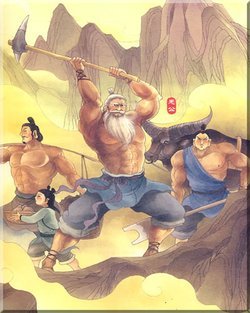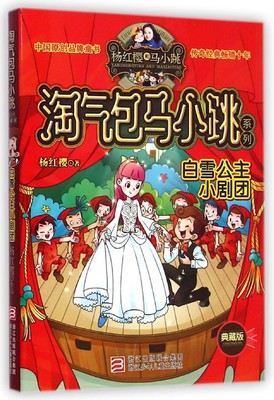六十八. 見小曰明
【原文】
昔者,纣为象箸①,而箕子怖②。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③,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盛菽藿④,则必旄象豹胎⑤;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⑥
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⑦,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見小曰明。”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喻老》)
【注释】
①象箸(zhù):亦作“象櫡”。“象笋”。象牙制作的筷子。②箕子,名胥余。是纣王的叔父,官居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曾劝谏纣王,但纣王不听,反而把他囚禁了。周武王灭商后,命召公释放箕子。武王向箕子询治国之道,记载于《尚书·洪范》。传说箕子晚年前往朝鲜居住,死后追谥為大圣王。③加于:放到。土铏:铏(xíng)古代盛羹的鼎,两耳三足,有盖,常用于祭祀。《儿女英雄传》第三六回:“一件像个黄沙大碗,説是帝舜当日盛羹用的,名曰‘土鉶’。”④菽藜(shūhuò):豆和豆叶。泛指粗劣的杂粮。菽,豆子。藿,豆叶。旄象豹胎:未生出的牦牛、大象和豹的幼胎。旄(mào):旄牛(即牦牛)。⑥卒(zú):终了,结局。⑦肉圃:各种肉类装点的园子。炮烙:古代烤肉用的铜格子。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盖为铜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博雅》临,大也。
【译文】
从前,商紂王因为使用象牙制作的筷子,紂王的叔父,官居太师的箕子,对此感到恐惧不安。他以敏锐的眼光由此联想到,一旦用上象牙筷子,必然不愿放到陶土大碗里面去随便拈取食物,必定发展到使用犀角美玉制成的高档奢侈杯具,才能与之相配。使用象牙筷子和高档的奢侈杯具,必定不愿用来装粗劣的杂粮饭和菜叶汤,必定发展到要吃未生出的牦牛、大象和豹的幼胎。吃牦牛、大象、豹胎,必定不会再穿粗布短衣、食住在茅屋之下,必定要穿重重色采精美华丽的衣服,住高大宽敞的楼阁亭台。用物质来满足贪婪者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见一叶落,当知天下秋。我害怕将来产生如此危险的结局,所以现在非常恐惧这样的开始。
居位五年,穷奢极欲的暴君商紂王,果然大量搜刮天下民脂民膏,建造了用各种肉类装点的园子;设置了大量的铜格子专门用来烤肉;酿酒之多,酒糟堆成高丘,美酒注满大池。终于导致纣的灭亡。
箕子见到紂王使用象牙筷子,就能预见天下的祸患。所以說:“能见端以知末、见微而知著,就叫作英明圣哲。”
六十九.莫辨楮叶
【原文】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①,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別也②。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③,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④,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⑤;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惡也⑥。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世。⑦”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喻老》)
【注释】
①象:指象牙。楮叶:落叶乔木构树的叶子。构树,古名楮(chǔ)。树叶去污力强,而且其树皮加工成的楮纸,白度、平滑度、紧密度及吸墨性都不错,于是人们砍枝剥皮,用作造纸原料。②丰杀:肥瘦。茎柯:茎,长条形的器物。柯,柄也。——《广雅》。毫芒:叶上绒毛。繁泽:多而富有光泽。乱:混杂。③乘:凭借,利用。载:放置,依托。身:身手。借指本领,武艺。④道理之数:事物的必然规律。⑤后稷:传说古代周族的始祖,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尧舜时代农官,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羡:有余,余剩。以羡补不足。——《孟子·滕文公下》。⑥大禾:泛指庄稼。臧获(zānghuò):古代对奴婢的贱称。范文澜《中国通史》:“墨家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惡:粗劣。这里指恶食(粗劣的食物)。⑦恃:依赖,依靠。为世:办事;成事。
【译文】
春秋战国时代,象牙雕刻工艺技高工巧,当时有个宋国人,用象牙为宋王设计制作了一件极为精致的楮叶工艺品,足足花了三年功夫才完成。长条形的叶柄肥瘦逼真,叶面上繁多的绒毛清晰可見而富有滋润的光泽。将它混杂在楮树的叶子中,难以分辨真假。这个人就靠奇巧的技艺在宋国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道家人物列子听说了这件事,感叹道:“假如天地之间任何一种植物,三年才能生长出一片叶,那自然界植物的叶子就太少了啊!”
由此说明,不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的各种资源条件,而片面依托个人的本领;不顺应事物的必然规律,而去学步于个人的智巧。这同三年制成一片楮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违背农时在冬季耕作种植庄稼,即便是以善于种植农作物著称的後稷,也不能保证粮食足够而有余;丰收年景各种庄稼生长茁壮,就连奴隶也不会一味吃粗劣的食物。靠个人的力量,後稷也生产不出足夠的粮食;顺应自然,奴隶也会衣食有余。
所以說:“必须依靠万物的自然规律,不敢任意行事啊!”
七十.自胜者强
【原文】
子夏见曾子①。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兩者战於胸中,未知胜负,故臞②。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③,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喻老》)
【注释】
①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亦称“卜子夏”,春秋末晋国人,“孔门十哲”之一。②臞(qú):瘦。③是以:所以,因此。
【译文】
孔子的著名弟子子夏遇见曾子。曾子问子夏:“你为什么身体长胖了呢?”子夏回答说:“战胜了自我,所以胖了!”曾子说:“什么意思呢?”子夏说:“我的思想斗争反复激烈啊!当我深入了解先王的道义时,深感显耀崇高而为之敬仰;可是眼前一再出现荣华富贵,又感到欣喜与羡慕。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复激烈未分胜负,当然就瘦了。现在,先王的道义终于在我的心中取得胜利,我的身体自然就胖了。”
因此,树立远大志向和高尚节操之难,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说:“能克己修身,战胜自我的人,才堪称为强者。”
七十一.买椟还珠
【原文】
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 为木兰之椟①, 薰以桂椒, 缀以珠玉, 饰以玫瑰, 辑以翡翠②。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 此可谓善卖椟矣, 未可谓善鬻珠也③。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④。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木兰:一种有香气的落叶乔木。椟(dú):小匣子,珠宝盒。②薰:以香料涂身。桂椒:肉桂及山椒。泛指高级香料。珠玉:小粒圆形的玉石。辑:集合,联结。③鬻(yù):卖。④览:观赏,采纳。忘:舍弃。
【译文】
楚国有个珠宝商,到郑国去做珠宝生意。他对珠宝的包装费尽了心思。首先用有香气的木兰做成华丽的盒子;再用高级香料肉桂及山椒涂抹薰烤;边缘还镶嵌小粒圆形的玉石刻意装饰、用翡翠集合在一起加以衬托。极力向人们炫耀他的珠宝是何等贵重,以便待价而沽。
可是,人各有异,取舍不同。有个郑国人,只留意外表流光溢彩,不在乎它的内在价值,买走了这个漂亮的盒子,却把里面具有真正价值的珠宝退还给了他。可以说这个珠宝商只是长于制售精美的包装盒罢了!不能说是善于经营珠宝生意啊!
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言论,都是华丽巧辩之谈,正是因为君王舍本逐末,只欣赏采纳那些华美的言辞,而舍弃那些真正有用的东西。
七十二.窃金不止
【原文】
荆南之地,丽水生金①,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②。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③。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注释】
①荆南:楚国荆山之南。西周初年,楚国先君熊绎被封在荆山一带(今湖北西部),国号为荆,直到春秋初才改为楚国。丽:依附;附着,依托。如“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易·离》。丽水:附着于水中。生金:亦称天然金、荒金、原金。是从矿山或河流冲积层开采出,没有经过熔化提炼的黄金。②得:抓获。辄(zhé):立即,就。辜磔(gūzhé):肢解躯体的一种酷刑。壅离:阻塞。③不必得:不一定都被抓获。
【译文】
在楚国荆山东南,谷地宽广,富含金矿。顺着水流泥沙俱下,附着于水流泥沙之中,有贵重的天然金砂。所以,大量的淘金者从四面八方涌来,偷偷地采金。
尽管官府的采金禁令非常严厉,抓到了偷采金砂者,立即在市街分尸示众。禁令下达后被处以极刑的人不计其数,尸体抛弃于水中,水为之阻塞不流。可是,违法采金还是不能禁止。
当时,最惨重的酷刑,没有比‘市街分尸示众’更残忍的了,但偷偷采金的行为还是不能禁止。那是因为,不一定每个偷偷采金的人,都会被官府抓获,这样就会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所以,现在若有人在这里说:“给你天下所有财富再杀死你,你愿意接受吗?”即便是见识短浅没有作为的人,也不会作出这种愚蠢的选择。占有天下,多么大的利益诱惑呀!还不愿意,那是因为他已知道必死无疑。
所以,刑罚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漏洞存在,那么虽然有‘市街分尸示众’的酷刑,也会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偷偷采金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知道犯法必死无疑,那么把天下的财富全都给他,也没人愿意去干违法乱纪的事了。
七十三. 富贾买璞
【原文】
宋之富贾有监正子者①,与人争买百金之璞②,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③,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④。事有举之而有败⑤,而贤其毋举之者⑥,负之时也⑦。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下》)
【注释】
①贾(gǔ):商人(古时‘贾’指坐商,‘商’指行商)。②百金:形容钱多。亦指昂贵的价值。《公羊传·隐公五年》:“百金之鱼公张之。”何休 注:“百金,犹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璞:未经雕琢的玉坯。③佯(yáng):假装。负:通“赔”(péi)。赔偿,补偿。④理:《说文》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毁瑕:毁损造成的缺陷。④溢:溢价。⑤举:施行;办理。⑥贤:胜过,超过。⑦负:放弃。时:时机;机会。
【译文】
宋国有个名叫监正子的富商,在市场上与别人争买一块叫价百金的玉坯。监止子认出这块未经雕琢的玉坯,的确质量上乘,他立即想了个歪主意,假装失手,把璞玉掉到地上碰坏了。这时,其他人都怕担干系而纷纷散去。卖玉的人要求监止子赔偿,他二话不讲,掏出一百金承担赔偿责任,可是玉坯就这样轻易到手了。
监正子把略有损坏的玉坯拿回家,找最好的工匠进行加工雕琢,修复毁损造成的缺陷,成了一块价值昂贵的美玉,居然溢价千倍啊!
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竭尽全力去做,却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即使失败了,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完全放弃,就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七十四.后息为胜
【原文】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①,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②,以后息者为胜耳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争年:比年长,争年龄大。②讼:争论。讼,争也。…以手曰争,以言曰讼。—《说文》。③息:停止。
【译文】
有两个郑国人,在那里瞎争论谁的年龄大。其中一个说:“我和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领袖,唐尧大帝同年而生。”另一个则说:“我与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哥哥同岁。”
两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争论不休。
这种不受检验与约束、毫无意义而且永远得不出结果的争论,大概只能以谁能一直说到最后,再没人胡说八道“接招”了,谁就算胜利了吧!
七十五.卜妻为裤
【原文】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①,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像吾故裤。②” 妻因毁新令如故裤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为裤:为,做;制作。②故裤:故,旧也。——《广韵》。③因:依据。令:使,让。
【译文】
郑县人卜子的裤子破了,便叫他的妻子给他做一条裤子。妻子问:“这次您的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呢?”卜子说:“像我那旧裤一样。”
卜妻只知墨守成规而呆板地模仿做事,只讲形式与教条,将做成的新裤毁坏,跟那旧裤一模一样破烂不堪。
七十六. 宋人治书
【原文】
《书》曰①:“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②。人曰:“是何也?” 对曰:“书言之,固然。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书》:中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尚书》又称《书》、《书经》。“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传本有些篇章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②绅(shēn):“绅,大带也。”—《说文》。大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衣裳所以必有绅带者,示敬谨自约整也—《白虎通》。绅束:用带子束腰,比喻约束的意思。治:研究。因:就也。重(chóng):重叠。一层又一层。③固然:当然,理应如此。
【译文】
中国上古历史文件汇编《尚书》中说:“绅之束之。” 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像用大带束腰一样,随时严格约束自己。
可笑的是,宋国有个研究《尚书》的书呆子,他只知道死抠字眼中狭隘的知识,不懂得从平凡简单的现象中推导出深刻的道理来。这个书呆子照字面的意思,用衣带一层一层厚厚地把自己的腰紧束起来。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非常严肃地说:“《书》中就是这样说的,我当然应该这么做啦!”
七十七.秦伯嫁女
【原文】
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①,为之饰装②,从衣文之媵七十人③。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④。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秦伯嫁女:指秦穆公将女儿怀嬴,最初嫁给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太子子圉(yǔ),子圉只身从秦国逃跑,回国即位,称怀公。后来秦穆公出于政治目的,又将已嫁晋怀公的怀赢(子圉故妻)嫁给流亡到秦国的晋国公子重耳(重耳既是怀赢的母舅,又是怀公的伯父),改名辰嬴。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即位称晋文公。②饰装:装饰打扮。③衣;这里作动词讲,意为“穿着”。文;通“纹”,华丽的花纹。媵(yìng):指随嫁,陪送出嫁,亦指随嫁的人。周代贵族女子出嫁,需要同族姐妹或姑侄陪嫁,称为媵,媵会成为侧室。后世媵和妾渐渐不分。④妾:“妾”在先秦和秦汉时是指女奴。
【译文】
从前,秦穆公出于政治目的,最初把他的女儿怀嬴嫁给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太子子圉,后来又将怀嬴嫁给晋国公子重耳,怀嬴身为秦国公主,迫于父母之命,再嫁给她的母舅又是前夫晋怀公的伯父。
秦穆公为了显示其霸主的地位,特地为他的女儿装饰打扮,随嫁的“侍女”都穿着华丽的衣服,且多达七十人。
可是,怀赢随晋公子回到晋国后,晋国人非常喜欢那些姿色靓丽的陪嫁“侍女”,却轻视秦穆公的女儿。
秦穆公本末倒置反而弄巧成拙。这可以叫做善于嫁“侍女”的高手,而不能说善于嫁女儿啊!
七十八.画鬼最易
【原文】
客有为齐王画者①,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客曰:“犬、马最难。”齐王曰:“孰易者?”客曰:“鬼魅最易。”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②,不可类也 ③,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客:指外来的画师。②罄(qìng):显现。 ③类:通“颣(lèi)”。缺点,毛病。《集韵》音垒。偏也。
【译文】
有个外来的画师给齐王画画,齐王问他:“画什么东西最难?”画师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画狗画马最难啊!”齐王又问:“画什么最容易呢?”画师回答说:“画鬼怪最容易呀!”齐王迷惑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原因呢?”画师说:“狗和马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动物,从早到晚在人们面前显露无余,是不能马马乎乎随意虚构的,只要有一点点毛病,人们立刻就会分辨清楚。所以要想真正有出神入化之笔,那是最困难的,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功夫才行。妖魔鬼怪就不同了,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它们的具体形象,可以胡编乱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受客观实际的检验,所以画起来是最容易的,而且谁也挑不了毛病。”
七十九.子产息讼
【原文】
有相与讼者①,子产离之②,而毋得使通辞③,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④。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讼:讼,争也。…以手曰争,以言曰讼。—《说文》。②子产:字子产,子美,郑穆公之孙,公子发子国之子,故称公孙侨。春秋时期郑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任郑国卿后曾铸刑鼎,是第一个将刑法公布于众的人,是法家的先驱者。③通辞:互相知道对方谈话的内容。通:了解。④到:通“倒”。颠倒。至:《玉篇》达也,由此达彼也。
【译文】
有两个人争吵不休,子产为他们评理。子产把他们分开两处,不让他们互相知道对方谈话的内容。然后把他们两人的话,颠三倒四地告诉对方,然后根据双方的谈话,发现漏洞,再仔细核对分析,谁是谁非很快就弄明白了。
八十.老马识途
【原文】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①,春往冬反,迷惑失道②。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③。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④,蚁壤一寸而仞有水。⑤”乃掘之,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与老马、老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⑤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曾任齐国相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隰(xí)朋:齊庄公的曾孫,春秋时期著名的齐国大夫,任“大行”之职,是齐国重要的外交大臣。孤竹: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一帶,诞生于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今冀东地区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中原霸主齐桓公,齐桓公北伐救燕,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②失道:迷路。③得道:寻找到归途。④山之阳:山的南面。山之阴:山的北面。⑤蚁壤:蚁穴周围防雨水的浮土。仞:古代计量单位:周尺八尺为一仞。周尺一尺约合二十三厘米。⑤不难:难,难堪的意思。师:效法;学习。
【译文】
公元前663年春,齐国相国管仲和大夫隰朋随从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援燕攻打入侵的山戎国。山戎首领密卢逃到孤竹国,与孤竹首领密谋,令城中兵民隐匿山谷。
为了实现北方地区的长治久安,齐军乘胜追击直捣孤竹。孤竹国王答里呵,派大将黄花率兵跟密卢一道前去迎战齐军,一触即溃,黄花于是杀了密卢,到齐军中献上密卢首级而诈降,称愿为齐军引路,前去追击答里呵。齐桓公信以为真,率领大队人马跟着黄花向北追击。进入迁安市南部与滦县北部接壤的区域,在一个叫“旱海”又称“迷谷”的村庄。由于已近冬日,只见茫茫无垠的沙碛之地,这时天色已晚,分不清东西南北,黄花也乘机溜掉了,情况非常危急。
管仲猛然想起老马能认识自己走过的道路。便对齐桓公说:“我们缴获了山戎与孤竹国大量的战马,现在老马的本领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派人挑选了几匹身强力壮的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在最前面带路,这些老马毫不犹豫地朝孤竹国方向走去,引导大军走出困境,打败了孤竹国,斩孤竹君侯之首,黄花也被乱兵杀死,孤竹国就此灭亡了。
在山中行军的时候,没有水喝。隰朋说:“冬天蚂蚁住在山的南面,夏天住在山的北面。蚁穴周围防雨水的浮土高一寸,地下八尺就会有地下水。”于是派人在山的南面打井,果然找到了水源。
凭借管仲的圣明和隰朋的智慧,遇到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也不把向老马和蚂蚁学习看作难堪的事。现在的人不知道用自己敦厚愚诚的心,学习和吸收圣人的智慧,这不是很大的错误吗?
八十一. 箕郑示信
【原文】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①”曰:“信名,信事,信义②。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③,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救饿:出自《韩非子》难势第四十:“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安:疑问代词。什么,怎么。②名:《玉篇》号也。号令也。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又称说,说出。事:引申为职守;政事。政府施政的事务。义:仪制,法度。③逾(yú):过分。超越法度。怠(dài):疲塌,荒废。
【译文】
晋文公向箕郑询问治乱的方法,说:“治乱如救饿。那怎样才能如紧急迫切地‘救饿’一样,迅速治理国家的混乱局面呢?”
箕郑回答说:“诚实守信!”
文公说:“怎么才叫诚实守信呢?”
箕郑说:“国家的号令、政事、法度都要诚实守信。国家的号令诚实守信,群臣就会忠于职守,评论好坏、褒贬功过就不超越法度,不会怠慢荒废各种事业;国家的政事诚实守信,就不会违背自然规律,百姓专心一意从事生产,不错过有利的天时季节;国家的仪制法度诚实守信,关系亲近的人就会互相劝导勉励,做到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关系疏远的人也会受到教化真心归服了!”
八十二.昭侯藏裤
【原文】
韩昭侯使人藏弊裤①,侍者曰:“君亦不仁矣②,弊裤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③。今夫裤,岂特嚬笑哉④!裤之与嚬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⑤。”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注释】
①弊:通“敝”。破旧,破损。②不仁:无仁厚之德。引申为不体面。③爱:爱惜,珍惜,舍不得。一嚬一笑:不高兴或喜悦的表情。嚬(pín),即颦,皱眉。③有为:有目的,有意图。④岂特:难道只是,何止,岂止。⑤予:与,赐也,通作“与”。—《正字通》。
【译文】
韩昭侯叫人把他的破旧裤子收藏起来,随侍左右的仆役说:“君王也太不体面了吧!连破旧的裤子都舍不得送给左右随从,还要收藏起来。”韩昭侯却态度和蔼地对仆役说:“其中的道理你们就不懂了,我听说真正的圣主明君,非常重视自己的情感,决不随意表现出不高兴或喜悦的神情。颦有颦的目的,笑有笑的意图。眼下我那些裤子,岂能是皱眉微笑可以相比的呢!两者相差太远了。我一定要等到对国家有大功的人,再亲自加赏给他们。由于还未发现赏赐的对象,所以现在要把那些破旧裤子收藏起来,没有轻易给予其他什么人啊!”
八十三. 曲成于欲
【原文】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道子西之钓名也?①”子贡曰:“赐也能。②”乃导之,不复疑也③。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④!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难⑤,子西死焉。故曰:“直于行者曲于欲。⑥”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道:说,劝阻,说服。引导,疏导。子西:芈(mǐ)姓,名申,又名宜申,字子西。楚平王之庶子,楚昭王兄长。春秋末楚国令尹。掌管楚国军政大权。误召回流亡在吴的白公胜,前479年,被白公胜所杀。②赐:即端木赐,字子贡,(前520—前456)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办事通达。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曾任鲁、卫两国之相。③不复疑:不复,不再。疑:迷惑,不明白。④被(pī):古同“披”,靠近;依傍。⑤白公之难:楚国太子建的儿子叫白公胜。太子建遭到诬陷时避难郑国,又与晋国人密谋袭击郑国,败露后被郑国人所杀。掌管楚国军政大权的子西,不听劝告,误召回流亡在吴的白公胜,像卵翼护着他长大,把他安排到靠近吴国边境上去保卫边疆。白公胜数请伐郑,子西勉强同意了。还没有出兵,晋国人就去攻打郑国。楚国却去救郑,并和郑国结盟。胜大怒,趁机叛乱,在朝廷上杀了子西,子西用衣袖遮着脸死去。⑥曲:曲意。违背自己的本意。
【译文】
孔子告诉弟子们说:“谁有办法能劝阻楚国令尹子西,不再沽名钓誉呢?”子贡说:“我端木赐尽心竭力去说服他,还是可能的。”于是前去开导子西,子西果真不再迷惑了。所以,楚平王死后,令尹子常欲立他为楚王,子西坚决不受,而拥立年幼的太子珍为楚昭王。昭王死后,他又拥立昭王之子熊章为楚惠王。
孔子说:“心胸真是宽广啊!不为权利所诱惑;德行高洁啊!可是人的本性是难以彻底改变的呀!曲的就是曲的,直的就是直的。”所以,孔子又说:“子西还是不能免于灾祸啊!”
后来子西不听忠告,还是为了名声,错误召回为人狡诈流亡在吴的白公胜,而且在其卵翼之下,把他安排到靠近吴国边境上去保卫边疆。终因养虎为患,后来白公胜发动政变,在朝廷上杀死了子西。所以说:“心地善良、行为正直的人,也会违背自己的本意而不知不觉地成就别人的欲望啊!”
八十四.庆封走越
【原文】
庆封为乱于齐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②”庆封曰:“越远,利以避难。”族人曰:“变是心也,居晋而可;不变是心也,虽远越,其可以安乎?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庆封:字子家,春秋时齐国大夫。为乱: 就是作乱。走越:逃到越国去。②族人:同宗的人;同一家族的人。之晋:到晋国去。③是心: 是,代词,此,这的意思。
【译文】
庆封和崔杼都是齐国的大夫。两人联合杀死齐庄公,共立齐灵公的幼子杵臼为齐景公。崔杼做了右相,庆封做了左相。后来庆封趁崔氏家族内乱,灭掉了崔氏集团,把持了国家政权。次年遭到栾、高、陈、鲍四族合攻,庆封逃离齐国打算到越国去。与庆封一起出逃的同族人感到奇怪,对庆封说:“晋国离我们近一些,为什么不到晋国去呢?” 庆封说:“逃到远离齐国的越国,有利于避免罹难之祸。”
庆封的族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改变你这种专揽朝政、荒浮骄纵的贪妄之心,借住在晋国就可以了;不改变你这种贪妄之心,虽然超过越国到更远的地方去,难道就可以安宁了吗?”
八十五. 醉寐亡裘
【原文】 绍绩昧醉寐而亡其裘①。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对曰:“桀以醉亡天下②,而《康诰》曰:毋彝酒③。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④。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寐(mèi): 进入睡眠状态。亡:丢失。裘,皮衣也。—《说文》。②以: 因为,由于。③《康诰》:是周公封康叔于殷地时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及纣王的儿子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便封周武王同母少弟康叔于殷地。为了使年幼的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作为法则送给康叔。这里的《康诰》应为《酒诰》。《酒诰》是康叔在卫国宣布的戒酒令。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周公担心这种恶习会造成大乱,所以让康叔在卫国宣布不许酗酒,规定了禁酒的法令。毋彝酒:不要经常饮酒。④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身:指人的生命或地位身分。 【译文】 绍绩昧喝醉了酒在席间酣睡,因而丢失了身上珍贵的皮袄。宋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感到奇怪,就问绍绩昧:“醉酒真的能够把自己身上的皮袄都弄丢吗?”绍绩昧回答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 荒淫无度的桀,因醉酒把天下都断送了。所以,后来康叔在卫国宣布的戒酒令《酒诰》之中,就专门规定了‘毋彝酒'。毋彝酒,就是不要经常饮酒。经常饮酒,如果是天子,就会失去天下;如果是平民百姓,就容易带来生命危险。”
八十六. 阳虎树人
【原文】
阳虎去齐走赵①,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②,及虎抵罪于鲁③,皆搜索于虎也④;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⑤,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⑥,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俯而笑曰:“夫树柤梨桔柚者⑦,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注释】
①阳虎: 姬姓,阳氏,名虎,一名货。春秋后期鲁国人。他以季孙氏家臣之身,跻身鲁国卿大夫行列,从而指挥三桓,执政鲁国,开鲁国“陪臣执国政”的先河。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治国之奇才、丧国之诡才。去齐:去,即逃离,离开。走赵:走,即前往,奔向某地。走赵,即投奔时任晋国中军佐的赵简子赵鞅。年轻的赵鞅看透了晋国国家政出私门,积极准备着六卿之间的争斗,并且注意收罗人才和建立根据地。赵鞅敢于打破士农工商的等级局限,大胆重用阳虎、尹铎、董安于等志士贤臣以为左膀右臂。②居:治理。居官,担任官职;做官。令尹:官名。③及:趁着,乘。抵罪:获罪,犯罪。抵:触犯。④搜索:搜查。⑤候吏:即候人。古代掌管整治道路、稽查奸盗、迎送宾客的官员。⑥迎:面对着,冲着。执缚(zhí fù): 逮捕;捆绑。⑦柤(zhā): 古同“楂”,山楂。《山海经》洞庭之山,其木多柤。《广韵》同?。似梨而酸。枳棘(zhǐ jí):枳,又叫“枸桔”。棘,酸枣。因其多刺而称恶木。常用以比喻恶人或小人。
【译文】
阳虎从鲁国逃亡至齐国,后来在齐国又遭到齐景公的排斥,不得不绕道宋国,辗转前往晋国,投奔时任晋国中军佐的赵简子赵鞅。年轻的赵鞅看透了晋国国家政权出于私门,积极准备着六卿之间的争斗,并且注意收罗人才建立根据地。赵鞅敢于打破等级局限,大胆重用阳虎,委任这位奸雄为赵氏首辅。
有一次赵简子问阳虎:“我听说你善于培养人才。你在执政鲁国及得到齐景公重用的时候,提拔了一些不得志或身份卑微的名流贤士、寒门子弟来辅佐自己。”阳虎说:“我在治理鲁国的时候,栽培过三个人,都做了‘身处上位,以率下民’的令尹。后来趁着我在鲁国获罪之机,都来搜查我;我在齐国做官时,举荐了三个人,一个能接近国君,一个当县令,一个做掌管整治道路、稽查奸盗、迎送宾客的候吏。后来我获了罪,接近国君的那个人不接见我,当县令的冲着我前来捉拿捆绑我。做候吏的追捕我直到边境,没有追上才罢休。我不善于栽培人啊!”
赵简子低头笑着说:“凡栽种山楂梨子、柑桔柚子,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种植带刺的枸桔和酸枣,长大以后反而刺人。所以,仁人君子培养人才一定要谨慎从事,切不可养虎为患啊!”
八十七. 鲁患不救
【原文】
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①,或宦于荆②。犁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虽善游,子必不生矣③。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今晋与荆虽强,而齐近,鲁患其不救乎!”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鲁穆公:战国初鲁国国君,即姬显,是鲁国第二十九任君主。鲁元公之子,在位33年。注重礼贤下士,曾隆重礼拜孔伋(子思),咨以国事;容许墨翟在鲁授徒传道、组织学派,使鲁国一度出现安定局面。公子:《仪礼.丧服》:“诸侯之子称公子。” 宦:学习官吏的事务。“宦,仕也。…犹今试用学习之官也。”—《说文》。② 荆: 春秋时楚国别称。③犁鉏(jū):一作犁且,鲁国上大夫,曾在齐为官。假,借也。—《广雅》。凭借,借用。于:可译为“从”“由”“自”等。
【译文】
战国初期,中原一带的齐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兵马强壮;楚国居长江中下游流域,沃野千里,兵车千乘,甲兵数十万,堪称南方一霸,时时窥视中原。鲁国虽然地处中原,却是个弱小国家,经常受到邻国的侵袭,使得鲁国君臣寝食难安。
鲁穆公为了跟晋国和楚国搞好关系,所以让他的众多儿子背井离乡,有的到晋国、有的到楚国去学习做官,认为鲁国一旦受到别国的进犯,就可以请他们来帮忙。然而上大夫犁鉏却认为,这是一种十分荒唐的作法,并拐弯抹角地对鲁穆公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人落水了,却要借助越国人来救起淹没在水中的孩子,越国人虽然善于游泳,但孩子必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假如发生了火灾而到大海里去取水来救火,海水虽多,但大火必定一烧到底扑不灭了,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
当前,晋国和楚国虽然强大,但齐国离鲁国近,若是齐国攻打鲁国,恐怕鲁国来不及得到晋国和楚国的帮助,早已经灭亡了啊!”
八十八. 在所与谋
【原文】
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①:“季孙养孔子之徒②,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而遇贼③,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④,而与周、召断事⑤,是能成其欲于天下。
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⑥。
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注释】
①南宫敬子:复姓南宫名敬子。颜涿聚:齊国大夫。②季孙:季孙氏,春秋战国时,鲁国的卿家贵族。作为三桓之首,凌驾于公室之上,掌握鲁国实权。③所:处所。朝服:古时君臣朝会、举行隆重典礼时所穿的礼服。同时,春秋时期贵族私家普遍设置家朝,在宅第会见家臣和处理家政事务。家朝亦称为私朝、内朝。十数:十个等级。数,等差。贼:祸害,特指杀害。④优:滑稽杂耍艺人。身材异常矮小的乐师。⑤周、召: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称。⑥是以:连词。因此;所以。
【译文】
南宫敬子问齊国大夫颜涿聚:“鲁国大夫季孙氏喜欢读书人,家里养着孔子的信徒,作为季孙家族的家臣与门客。在居住的处所每次私朝时,总是穿着上朝穿的礼服,正襟危坐会见他们。和他坐在一起的人,按其作用不同分为十个等级。可是季孙氏还是遭到杀害,这是为什么呢?”
颜涿聚说:“从前,周朝第二代君王周成王,交往滑稽杂耍艺人及身材异常矮小的乐师,是为了娱耳目乐心意,而他与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一起决断国家大事,因此能够在天下实现他的愿望。
现在,季孙氏家里养着孔子的信徒, 在居住的处所家朝时,穿着上朝穿的礼服会见他们,和他坐在一起的人,按其作用不同分为十个等级。可是他却去和优伶侏儒一起决断大事,家臣与门客以为是讨厌自己而心生怨恨,便串通起来杀害了季孙氏。
所以说:不在于跟什么人相处,而在于同什么人一起谋划大事。”
八十九. 车席泰美
【原文】
赵简子谓左右曰:“车席泰美①。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屦虽贵,足必履之②。今车席如此大美,吾将何以履之③?夫美下而耗上,妨义之本也。④”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注释】
①车席:马车上供坐卧而铺垫的用具。泰:过分。美:装饰,华美。②贱:简单粗陋,不值钱。屦(jù):泛指鞋。履:踩踏。③大美:豪华美丽。④夫:文言指示代词,相当于“这”或“那”。而:连词,有“往”、“到”的意思。妨:损害。义:仪制,法度。
【译文】
赵简子告诉身边办事的人说:“马车上供坐卧而铺垫的用具,过分美化装饰,实在太豪华奢侈了。帽子即便简单粗陋不值钱,也是用来戴在头上的;鞋子即使再精致昂贵,必定受到脚的踩踏。现在,马车上的车席,如此豪华美丽,我怎么忍心踩踏上去呢?从美化踩在脚下的车席,进而到不加珍惜地在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帽子,随随便便地消耗资财,更为破费,完全违背了仪制法度的具体规定和本来的愿望啊!”
九十. 文侯守信
【原文】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①,明日,会天疾风②,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魏文侯: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②虞人:又单称虞、山虞,古代官名。掌管山泽草木鸟兽牧猎的职官, 早在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便有关于虞人掌管山林草木鸟兽的记述。期:约定。明日:第二天,次日。会:恰巧,正好。③犯:顶着;冒着。罢:取消。
【译文】
魏文侯与掌管山林鸟兽的官员,预先约定了打猎的时间。第二天恰巧刮起了大风,身边的侍臣都劝阻魏文侯不要去打猎了。文侯不听。说:“不行。因为风大的缘故,就失信于人,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于是文侯自己驾着马车,冒着大风,赶去告诉掌管山林鸟兽的官员,取消这次打猎活动。
九十一. 击鼓戏民
【原文】
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①。饮酒醉,过而击之也②,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③。居数月④,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⑤。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楚厉王:原名熊眴,即楚鼢冒,熊霄敖长子,东周初期的楚国君主,警: 报警信号。为:将。与:表偕同的意思。跟别人一起。②过:错误。③罢:归,返回。④居:当, 在。⑤更令明号:重新申明号令。
【译文】
东周初期楚国君主楚厉王,规定了紧急情况的报警信号,如果遇到了敌情,就将击鼓以集合百姓前来守卫都城。
有一天,楚厉王喝醉了酒,糊里糊涂地拿起鼓槌猛敲一通。鼓声惊动全城,老百姓都纷纷跑来集结待命。楚厉王急忙派人阻止,说:“我喝醉了酒,跟身边的人游戏消遣,这通鼓打错了。”军民百姓都各自回家了。
几个月后,敌人真的来了,厉王击鼓发出紧急警报。但百姓以为厉王又是在闹着玩儿的,没有一个前来救援。楚厉王只好重新申明号令,老百姓才相信了。
九十二. 子皋逃卫
【原文】
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门①。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②。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③。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子之足④,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⑤,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法令⑥,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⑦,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⑧”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⑨;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⑩”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注释】
①狱吏:旧时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刖(yuè):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脚砍掉。异体字跀。②执:拘捕, 捉拿。③从,随行也。—《说文》。跀危(yuè wēi):指古代受刖刑的人。门下室:《说文》下,底也。④亏:违背。⑤固:本来。⑥方:相当于“在”、“当”,正当。狱:罪案。治:审理。也:表示停顿一下,舒缓语气。倾侧:随顺;依从。⑦臣以言:以,为。为我说话。憱(cù)然:《字汇心部》:“憱,戚也。”忧愁;悲伤。⑧天性仁心:先天具有的仁爱之心。固然:本来就是这样。德:感激。⑨概:量米粟时,放在斗升等量具上的木板,用以刮平量具内的米粟。平量:公平计量。⑩平法:谓执法平正。《书·立政》“准人” 孔传:“准人平法,谓士官。” 孔颖达疏:“平法之人,谓狱官也。”《汉书·宣帝纪》:“吏务平法。”平,正也。—《广韵》。
【译文】
孔子在卫国当相国的时候,他的弟子子皋做了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他砍掉了一个犯人的脚,然后让这人去守门。
有人在卫君面前恶语中伤孔子,说:“孔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不得不逃走躲避起来,弟子们都迅速跟着逃跑。子皋跟随着跑出大门,那个被他砍掉脚的守门人,指引他逃到大门下面的地下室中,卫君的差役们追拿不到子皋。
半夜时分,子皋问那个被他掉砍脚的守门人:“我不能违背君主的法令,亲自砍掉你的脚,这时正是你报仇的时候,你为什么竟然肯帮助我逃命呢?我凭什么能从你这里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呢?”受刑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不可改变的事,没什么好说的,我甘心承受。然而当您根据罪案审理我的案情时,您依从法令,陆续为我说话,很想为我免罪,这些我都是知道的。
等到罪案已定,您满怀伤感很不高兴,这种神情表现在脸上,我清楚地看在眼里。您并不是背公向私偏袒我才这样做的啊!而是您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之所以心悦诚服地感激您,并且帮助您逃避搜捕的原因啊!”
后来孔子说:“会做官的人,施行德政树立美德;不善于做官的人的人,树立的则是怨恨。概,是用来公平计量的;统治人民的大小官员,是用来公正执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平正义啊!”
九十三.昭侯握爪
【原文】
韩昭侯握爪①,而佯亡一爪②,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③。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注释】
①韩昭侯:战国时代韩国国君,战国七雄之一。握爪:握,同捂(wǔ)。遮盖。爪:指甲。②佯(yáng)亡:假装失去。效: 本义:献出。③不:同“否”
【译文】
韩昭侯手指弯曲成拳,故意将一个指头压在手心遮住指甲,假装失去了一个指甲,急切地希望寻找回来。左右的臣仆竟有人割下自己的手指甲,说:“这就是你丢失的指甲。”
韩昭侯用这种伎俩,立即分辨出身边的人诚实与否。
九十四. 越王式蛙
【原文】
越王虑伐吴①,欲人之轻死也②,出见怒蛙,乃为之式③。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④。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⑤。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上》)
【注释】
①越王: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勾践。虑:谋划。②欲:需要,希望。轻死:看轻死亡。不怕牺牲。怒蛙:肚腹凸起鼓动腮帮的蛙。晋葛洪《抱朴子·广譬》:“是以晋文回轮于勇虫而壮士云赴,勾践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轻死。” ③式:通“轼”。以手抚轼,为古人表示尊敬的礼节。轼(shì),古代车厢前面用做扶手的横木。④明年:古意,第二年。请:愿意。⑤杀,克也。—《尔雅·释诂》。战胜,顺服。又获也。
【译文】
春秋末期,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富民兴国政策,使国力大增。于是,越王时时不忘与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越王非常希望国人,为了灭吴雪耻而不怕牺牲。有一次外出,看见一只鼓腹凸腮的蛙。他就故作姿态地用手抚摸车前的横木,俯身低头表示敬意。随行的人大为不解,便问越王:“为什么要尊敬一只青蛙呢?”越王说:“因为那蛙的表现,有如此旺盛的气势,无所畏惧,多么像一位不凡的勇士啊!所以我要向它致敬。”
这件事很快在越国传开了。第二年,到越王那里,愿意为越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一年之中就有十余个。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赏誉厚而守信,它的作用足以顺服人,使人们愿意为你献身。
九十五. 齐桓巡民
【原文】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①,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及反②。”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③,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谕宫中有妇人而嫁之④。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⑤,妇人十五而嫁。”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注释】
①自养: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②无以妻之:无以,即没有(能力)。妻,用作动词,娶妻的意思。之,音节助词,无实义。腐弃之财:指腐败不用任其搁置的财物。③怨女:指已到婚龄而无合适配偶的成年女子。④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⑤丈夫:成年男子。室:娶妻;成家。
【译文】
齐桓公微服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巡视,只见家里有一位孤独老人,还需要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齐桓公问其原因,老人说:“我有三个儿子,由于家里贫穷,没有能力娶妻,完全依靠在外当雇工谋生,现在还没来得及回家。”
齐桓公回到宫中,把在民间的所见所闻告诉相国管仲。管仲说:“国库中畜积有腐败不用、任其搁置的财物,民间就会有饥饿的人;宫中有已到婚龄而无合适配偶的成年女子,民间就会有大龄男子无妻。”
齐桓公说:“你说得对。”于是颁布文告,宫中凡有成年女子一律出嫁。同时向民间下达命令说:“成年男子年满二十岁就要娶妻,成年女子年满十五岁就要出嫁。”
九十六. 鲁人救火
【原文】
鲁人烧积泽①。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②。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③。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④”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⑤”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注释】
①积,聚也。——《说文》。按,禾谷之聚曰积。倚:偏,这里指蔓延的意思。恐:这里表示估计,相当于“大概”、“也许”。国:国都。③将众:率领众人。趣,疾也。—《说文》。急,赶快。④请:请,告也。—《尔雅·释诂》。又《类篇》受言也。徒:只;仅仅。⑤降北:投降败逃。北为败北的意思,打了败仗往回逃跑。入禁:进入禁止的场所。
【译文】
鲁人收割的禾谷,堆放在湖泽岸边,突然着火燃烧起来。偏偏地面上刮起了北风,火势迅速向南蔓延,继续发展下去,也许会烧到国都曲阜。鲁哀公非常担心,打算立即率领众人前去救火。但是身边无人,大家都去追捕野兽,不愿救火。
哀公叫来孔子,询问对策。孔子说:“追捕野兽正合人们的心意,又不会受到责罚;救火不但辛苦,又没有奖赏。这就是没有人愿意奋力救火的原因啊!”
哀公说:“有理。”
孔子接着说:“救火的事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如何行赏。假如参与救火的人都给赏,那么国库里的钱,不足以赏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今之计,只好通告国人,只对不救火的人和继续追捕野兽的人进行惩罚。”哀公说:“好吧!”
于是孔子下令说:“凡是不参加救火的人,比照降敌逃跑论罪;继续追捕野兽的人,比照擅入禁区论罪。”命令还未传遍城乡,这场大火就已经扑灭了。
九十七. 欢以失日
【原文】
纣为长夜之饮①,欢以失日②,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③。箕子谓其徒曰④:“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⑤。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 辞以醉而不知。⑥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上》)
【注释】
①长夜:整夜。②失日:忘记时间。③箕子:名胥余。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箕子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当纣王闻知箕子情况,遂囚禁在“箕子台”。④徒:随从人员。弟子。⑤为,治也。—《小尔雅》。天下主:指国家的君王。其:在句中表示揣测语气,相当于“恐怕”、“或许”、“大概”、“可能”、“一定”。⑥辞:推托,借口。以:通“已”,已经。
【译文】
商朝的末代君主纣,不理朝政,整天整夜地喝酒,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寻欢作乐以至于忘记了时日。问他身边的人,也尽数不知。于是叫人去问独自隐居在箕山的箕子。
箕子告诉他的随从说:“一国之君与一国之臣都忘记了时日,国家一定危险了;一国之君与一国之臣都不知道的事,如果唯独我知道,那么我恐怕有危险了。”因而借口已经醉了,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九十八.造父御马
【原文】
造父方耨①,时有子父乘车过者②,马惊而不行,其子下车牵马,父推车,请造父:“助我推车。”
造父因收器,辍而寄载之,援其子之乘③,乃始检辔持策④,未之用也,而马咸骛矣⑤。
使造父而不能御⑥,虽尽力劳身助之推车,马犹不肯行也。今身使佚⑦,且寄载,有德于人者,有术而御之也⑧。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注释】
①.造父:西周著名御车者,受幸于周缪王,王使造父御良马八匹,西狩至昆仑,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后闻徐偃王反,王使造父御车日驰千里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今山西洪洞县),由此为赵氏,是为赵国之始祖。耨(nòu):本义:锄草,耕作。②时:当时,这时。者:这里。③因:古语“因”与“就”相通,《说文》:因,就也。连词于是,就的意思。辍(chuò):停止耕作。寄载:乘别人的交通工具。援:拉,拽。之:到,往。乘:《集韵》音剩。车也。④检辔持策:检,收拾,整理。策辔(pèi):马鞭与马缰。⑤咸:《易·雜卦》咸,速也。骛 (wù):《广韵·遇韵》:“骛,驰也,奔也,驱也。”疾驰之意。⑥使:假如。⑦佚(yi):通“逸”。《广雅》:“佚,乐也。”安闲之意。⑧德:恩德。术:策略,办法。
【译文】
造父正在田间耕作,当时有父子二人乘车经过这里。由于拉车的马受到惊吓,无论如何不肯前进。父子二人只好下车,儿子牵马父亲推车,还请求造父:“帮助我们推推车吧!”
造父因此收拾工具,停止耕作,轻身一跃坐上马车,随手将那年轻人拽到车上。刚刚整理好缰绳、拿起马鞭,还没有开始使用,那马就引起相应的反应,迅速奔跑起来。假若造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驾驭车马,虽然竭尽全力身受劳累帮助推车,那马还是不肯前行。如今身体得到安闲,而且能搭乘别人的马车,又给予他人的好处,这是因为他有本领驾驭车马的缘故。
所以,国家是君王的马车;权力是君王拉车的马匹。如果君王没有控制和使用臣下的策略和手段,身体虽然劳累,国家还是免不了出现混乱的局面;有驾御臣下的本领,自己就会处在悠闲安乐的境地,又能求得帝王的功业啊!
九十九. 申子辟舍
【原文】
韩昭侯谓申子曰①:“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②。”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③。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④,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⑤。
【注释】
①韩昭侯:战国时代韩国国君。前358-前333年在位。战国七雄之中,以韩国最为弱小。韩昭侯在位期间任申不害主持国政,使韩国致治,诸侯不敢侵韩。申子:申不害。法家代表人物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②以来:犹言以后。行法:按法行事。奚(xī):文言疑问代词,相当于“何”、“怎样”。③仕:审察,仔细考察。又‘仕,学也。’—《说文》。段玉裁注:“古义宦训仕,仕训学。” 朱曰:“犹今言试用也。”从兄: 古人之从兄,具体分二种:同曾祖父,不同祖父,年长于己者,称为从祖兄;同祖父,不同父亲,年长于己者,称为从父兄,即今日所说的堂兄。二者统称从兄。④谒(yè):请求。
⑤辟:古同“避”,躲,躲避之意。辟又作“擗(pǐ)”,拊胸也。即捶胸。
【译文】
韩国国君韩昭侯告诉丞相申不害说:“国家的法律制度很不容易执行啊!”申不害回答说:“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见到功劳才给予奖赏;依据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您设立了法律制度,又听从左右人的请求,所以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并无权威地位,这就是法律制度很不容易执行的原因啊!”韩昭侯说:“我从今以后,以及怎样依法行事了,我也知道应该怎样听取意见了。”
后来有一天,申不害请求韩昭侯仔细考察一下他的堂兄,让他学习政事,见习试用做做官。韩昭侯提醒申不害说:“这可不是从你那儿学来的‘依法行事’的作法呀!我今天要是听从了你的请求,那岂不是破坏了你所主张的治国原则吗?还是不满足你走后门、通关节的要求为好啊!”
申不害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于是躲进屋里深刻反省,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并请求韩昭侯给予处罚。
一00. 襄公之仁
【原文】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①。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②。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②。”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③。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陈而后鼓士进之。④”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⑤”公曰:“不反列,且行法。⑥”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⑦,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⑧。
(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注释】
①宋襄公:宋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涿(zhuō)谷:涿河边的河谷地带。②既:已经。济:渡河。使:让,令,叫,命令。③重伤:重复伤害受伤的人。二毛:头发花白的人。常用以指老年人。迫人:逼迫人。阨(è):狭窄。不鼓:不击鼓(进攻)名词作动词。鼓,击鼓也。—《说文》。④成陈:陈与“阵”通。列成战阵。鼓士:激励将士。腹心:比喻极亲近的人;心腹。这里当指宋楚之战,宋襄公亲自葬送了视为心腹的亲军卫队。完:保全,坚固,完整。特为:不过是,只为了。耳:表示限制,相当于“而已”、“罢了”。⑥行法:按法行事。⑦撰:常规,法则也。《易·系辞》以体天地之撰。⑧自亲:躬亲。亲身奉行。
【译文】
宋襄公与楚国人在涿河边上的河谷地带作战。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式,并在军中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仁义”两个大字,试图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这时,楚国人还没有来得及渡过涿河。宋国执掌军事作战指挥、统帅管理军队的右司马购强,觉得有机可乘,快步走到宋襄公身边,迫不及待地提出建议,说:“这一仗敌众我寡,由于楚军轻敌,给了我们机会,请主公命令我们以逸待劳的军队,在楚国人只有半数渡河,还没排成战斗队列时,就发起猛烈攻击,楚军肯定会方寸大乱必败无疑。”
宋襄公说:“我听品德高尚的仁人君子说过:‘不重复伤害受伤的人,不捕捉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把别人推入危险的境地,不把他人逼上狭窄的绝路,不击鼓进攻不成队列的敌军。我们是仁义之师,在楚国军队还没有完全过河的时候,就去攻打他们,是有伤义理的。告诉将士们,让楚国军队全部过河、列成战阵后,再激励将士攻击他们。”右司马说:“君王不爱惜宋国军民的性命,不保全视为心腹的亲军卫队,只不过为了个人的‘仁义’虚名罢了。”
宋襄公怒目切齿地说:“你再不回到队列中去,将按军法行事。”右司马只好返回队列。此时,楚国人已经排好作战的常规队列,宋襄公才命令击鼓进攻。
由于楚军人多势众,实力强大,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的亲军卫队全部被歼,大将公子荡战死,宋襄公虽然逃出重围,但股骨受伤。三天后,这位满脑子仁义的国君,就一命呜呼了。这就是宋襄公从仰慕到亲身奉行仁义带来的祸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