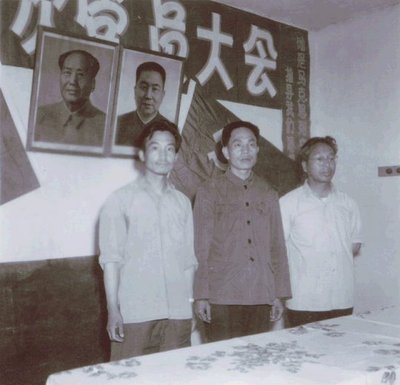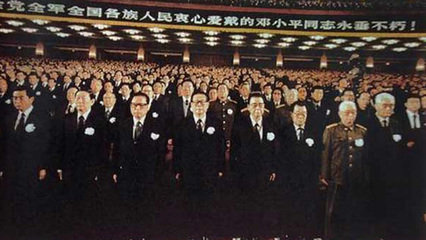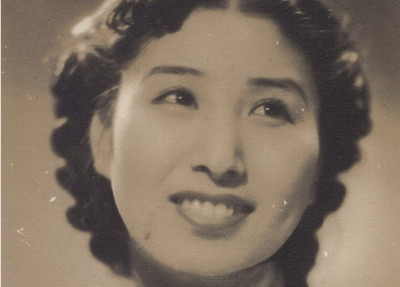
胡耀邦辞职风波始末——ZZY自述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
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
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 安排的七人小组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
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