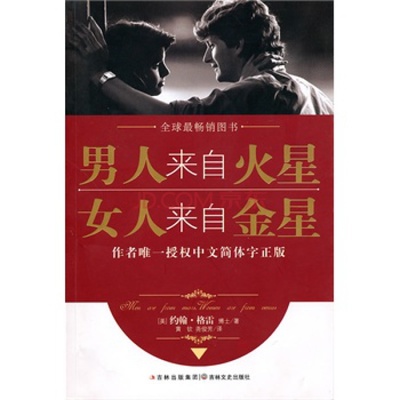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1
武汉的四季中我最喜欢秋天。记忆里,武汉的春天太短,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唯有秋天脚步缓慢,经常到了十二月还不见冬意。漫长的秋天一点点从浓烈转向开阔,风雨明晦的日子,站在珞珈山顶远眺,湖岸弯曲,远山迷漫,亭台掩映在树梢,像极了南唐董叔达的淡墨山水。
哲学院的贺念给我打电话时,我还在网上浏览刘晓波的一篇文章。他在电话中问我几点去VOX酒吧,唔,我居然忘记了,今天约了几个朋友去听民谣音乐专场。匆忙从家中出来,沿着东湖去关山,2008年秋天的武汉,暮色霭郁,云层低垂,秋风不停从江北吹来,正萧瑟。
上周也是这个时间,贺念约我去地质大学附近的VOX,他说周云蓬晚上在那里有场演出。VOX酒吧,很早以前去那里喝过一次酒,门脸不大,二楼,100多平米的空间挤满了来听音乐的年轻人,贺念说,这里现在是武汉地下音乐的集散地。地下音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二十年,我喜欢的音乐都带着旧报纸的气息,那些打口带、老吉他、翻抄的乐谱、吹不响的定音器,恍如隔世。咳咳,喝汽水的年代已经远去了。
不过周云蓬,我还是知道。不久前在网上听他演绎过一首《九月》,当然还有他的那首《中国孩子》。《九月》是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周云蓬唱起来凄婉动人又遥远高亢,简单的吉他配上暗哑的嗓音,一听就让人怀旧。有一个晚上我曾经坐在书房里反复播放它,音量开到小,音符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像用一根丝线勾连着什么,却又并不真切。仔细倾听换弦时手指滑过琴枕的声音,平静中的颤抖,轻薄如草原上的白云,又如微风吹动山岗。很有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味道。
为这首诗谱曲的人叫张慧生。和海子一样,张慧生也是自/杀身亡的,他去世后,这个曲子也就再没有人唱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居然周云蓬把这个作品保留并传唱下来。人生总有太多难以确定的事情,谁能说的清,就好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散场后,周云蓬带着宽厚的墨镜坐在我身边,VOX酒吧下的烧烤摊上,散落着空空的啤酒瓶。“我觉得海子对我来说是一道炽烈的光,很刺目。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愿意让他经常出现。他的诗是好诗,但是我会不安。”周云蓬扶着琴箱对我说。
我沉默,不知道说什么好。
“生命之饼”的主唱吴维过来干杯。很多年前,在地球村音乐吧我们有过一次交往。当年他还是个带着金属手链,纯钢戒指,穿件背心在舞台上玩砸琴、玩旱地拔葱的武汉朋克。这次一见,沉稳,收敛,一如他现在的音乐,乐队配上了风笛、长笛和大提琴,重复的段落表达、大量的回声营造出寂寥神秘的效果,曲风竟有爱尔兰凯尔特风味。吴维告诉我,下周赵老大,吴吞和冬子要来武汉演出,“到时候你也来听一下吧”,喝了一杯酒他坐回去,似乎还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夜已深,他的黑色鸭舌帽在昏暗的灯下光影分明,像年轻时的CharlieLandsborough。
2
没有了舌头乐队的吴吞孤独地坐在聚光灯下。
我有时候很怀疑中国摇滚乐的这种聚散。在中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几乎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但谁也没有办法说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摇滚乐队,没有一支能够长时间的聚合在一起。是因为趣味的改变,还是因为外力的倾轧?又或者,是因为本来的不成熟还是别的什么?
1997年,舌头在新疆成立,甫一出现,就以其生猛热烈的重型节奏震动了中国摇滚乐坛。同一年,更加另类的盘古也在南昌的黑暗中发出愤怒的呐喊:“你不让我摇滚,我迟早让你知道我的狠!”,那是我学会的最后一首和地下摇滚有关的歌曲。97年的武汉之春来的晚,我躲在学校旁的黄家大湾,在租来的房间里看闲书,琴已经弹的很少很少。
2月19日上午,十二寸的黑白电视中传来哀乐,中央电视台说,邓小平去世了。我打开窗户,侧耳听,外面没什么动静。收拾好东西步行走回学校,校园里静悄悄的,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和车辆,安静异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天多云转阴,气温很低,春寒料峭。
吴吞的《时候到了》,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为数不多让我迷恋的歌曲之一。口琴悠扬,吉他伤感,唿哨清丽,加上吴吞懒散的呓语,不动声色,内敛洒脱,音乐的轻松和诗一般的歌词,有点动漫,有点皮影,有点木偶剧的意思。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趣味狭隘,对某些音乐类型的过分偏爱。但这有什么不好?坐在台下喝啤酒,我看见舞台上一束灯光静静照着吴吞的肩膀,走动的人群在黑暗中晃动,带着鬼魅般的身影,让人觉得既真实,又虚幻。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第二天午饭时把这首歌放给六岁的儿子听,问他,你喜欢吗?儿子说,谁唱的,我说,是一个叫吴吞的叔叔。儿子嘴巴里含着饭菜,哼哼的跟着音乐唱,我敲着饭碗为他伴奏,他的童声咿咿呀呀,恰似这首歌曲的另一个伴奏版本。
之后的几天,儿子的嘴里经常蹦出一句:“太阳落山的时候下雨了,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只要一出门,他就望着楼道顶上的燕子窝这么唱,然后对我说:“爸爸,我也要一个宠物机器……”。
但我哪里去给他找吴吞歌曲中的宠物和机器?只有搪塞。很多天后,我正在电脑前工作,儿子在地板上玩他的宠物机器。我轻轻哼着《时候到了》,刚刚唱到“不管明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儿子就大声接着唱:“小燕子们都要从窝里飞出去,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我扭头看着他微笑,儿子敲打着奥特曼的脑袋接着唱:“吴吞,吴吞,给我一个印第安人!”
我哈哈大笑。
3
冬子上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从湖北云梦走出去的小伙子,抱着一把箱琴,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他安静地说,赵老大病了,在睡觉。我为大家唱一首《十方》吧。
十方?听到这个名字,我在心中默念了一遍。十方,十方,他说的是佛经中的“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还是说的上天、下地、东、南、西、北、生门、死位、过去、未来?我低下头,准备迎接冬子带给我的第一串音符。
第一串声音是从黑暗深处传来的。低沉,复杂,轮指滚动,越来越响,沧桑,温暖,难以言说。然后是寂静,三秒的寂静,那是十万佛塔的寂静之声,是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寂静之声。然后呢?然后是一串流水般的泛音在琴弦上跳跃,犹如晨曦初上,照耀金顶。《无量寿经》下卷中有这样一段话:“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一如冬子的嗓音,浑厚,低沉,一出口,上师低眉,菩萨垂手,空气在微微颤抖,全场肃然。
这是一首需要闭气聆听的神秘之歌。灰暗的调性,酸楚的低音,迟疑忧伤的喃喃自语纠缠在旋律中,听起来欲罢不能,欲言又止。吴吞端着酒杯,敲了一下桌子,他悄悄对我说:“冬子是中国未来的民谣大师!”。
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走到了西藏江孜的白居寺。那是一座十五世纪初由热布旦贡桑帕和班禅一世克珠杰·格勒巴桑始建的伟大寺庙,寺中萨迦派、噶当派、格鲁派3大教派共存。黄昏时,去寺中散步,望见巨大的圆形佛殿中部 还有一层小佛殿,四面的门楣上,各画了一双三米长的巨眼。寺中的喇嘛告诉我,这是印度湿婆神的慧眼,可以识善恶,辨是非。眼睛的画工极其精湛,波浪般的眼角,波浪般的眉毛,慈悲中略带威严,正是冬子十方专辑封面上的造型。我远远望着巨大的眼睛,那双眼在暮色中散发熠熠的光芒,不论哪个方向看都像是对我在注视,仿佛能看透人心,让天地间的一切无所遁形。
我坐在寺里一棵柳树下发呆,觉得人世中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夕阳辉煌,照耀西藏,突然想起冬子的《十方》,闭上眼,似乎真的有音乐在天际回响,一串轮指,然后寂静,然后泛音袅袅,然后山川沉默,河水倒流。
4
赵已然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他说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反正是越搬越远,已经搬到跟北京没什么关系的地方了。
他经常没有钱,有一次住在白庙,他都四天没有一分钱了,正好碰见万圣节。平常这种时候,赵已然很会享受这种孤独。练鼓,看书,要不就在午后,把衣服脱光了躺在院子里晒两个小时的太阳。但那天是个节日,他很想出去玩一下,很想去和其他人一道狂欢一晚,喝一点威士忌,或者,去飞两片叶子。
但是他从九月份开始,就没有挣到过一分钱。不是他不能去靠打鼓挣钱,而是他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贫穷就去冒充朋克,或者去迎合可以换钱的媚俗的音乐。
那一年,他四十岁。
中国的音乐市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他像一匹年老的孤狼,爪牙已经不再锋利,他误入了一个自己根本应付不了的禁区,在熟悉又陌生、认识又不认识的山林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终于被伤着了,喘着气缩在了一个角落里。
许多时候,他靠一包方便面度过一天,或者,是一块玉米面发糕和一些瓜果。他靠着这些东西在房间里疯狂地打鼓,弹琴,却没有人去仔细倾听。他是中国最好的布鲁斯音乐的吉他手,精湛,纯熟的技巧在业内无人不知,但他却只能在黄昏狠心把朋友送他的一把刀,压给村口小商店的老板换取两瓶啤酒。
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连借钱的技法和技术都不会,他只会在深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在空空的院落中,为墙头的荒草弹奏中国最好的音乐。
2004年4月11日,赵已然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信。
尊敬的爸爸:
我此一生,悲也好,喜也好,成也好,败也好,我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事。并非有意或无意而为。正像20多年前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样,乃已然者也之事。
名利二字,并非我所不齿、不屑。相反,我很尊重。只不过我所求者,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和利。
两年多来,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像我一样生活着的朋友,一样的道德观念,一样的生命态度,而他们比我更彻底、更纯粹。他们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们的支撑和宠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他们让我痛苦、迷茫、屈辱地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坦然、踏实了。我知道,我有同志了……
2009年秋天,赵已然路过武汉去香港。深夜,我在汉口的一个宵夜摊上接他吃饭。赵老大依旧是紧身的长裤,牛仔上衣,二十年前的装束和老做派,让人觉得温暖,和煦。他告诉我,最近终于重新开始唱歌了。有一家公司和他签约出版一张唱片,那将是他的第一张正式唱片。
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不喝酒了,对我说:“我要去深圳和香港做两个专场。顺便,去买一把自己的琴。”,我喝了一杯酒,望着他,“我把唱片的版权费拿出来,我去不了欧洲,机票太贵了,香港应该可以买到一把琴!”。
那天的武汉街头,正是初秋,有附近住家的女人穿着睡衣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真希望那天是1988年,赵已然年轻了二十岁,他在黯淡的路灯下畅谈音乐,依旧壮怀激烈,傲视群雄。
5
很多年前写过一首诗《西北偏北》。从滕州去北京的刘东明把它谱了曲,传唱开去,他把演唱会的视频发给我看了,音乐做的很好,粗砺硬爽,我喜欢的不得了。东明和赵已然、吴吞、冬子都是朋友,和我非常喜欢的野孩子乐队也很熟悉。野孩子乐队的几个人我没有见过,他们的音乐,像是高山上的杜鹃,黄河中的流水,朴素、浪漫,让我神往已久。
野孩子的主唱名叫小索,他2004年去世了。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一个三度叠置的和弦,小引,小索,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只是,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唱/唱着我的黄河谣……小索一直在孤独地歌唱。
我很怀念他。
拉萨的王啸给我寄来一张碟,名字叫“黑马河的儿子”。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收到他的信。打开一看,那是一张没有封面设计,甚至碟片上连名字都没有印刷的地下DEMO。王啸用签名笔在正面写着专辑的名字,黑马河,然后分行写,的儿子。
字体和他的音乐一样,龙飞凤舞,狂放不羁。
坐在学校的操场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音乐已经收到。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拉萨?我刚从那曲的比如回来,那里有面骷髅墙。
晚上在家独自欣赏他的音乐,扎念琴的节奏依旧孤单,急促,手鼓声隐约从远处传来,低声部像一阵闷雷从空气中滚过,王啸的呼麦浩荡登场,“那大雁飞过的地方啊,是母亲生我的地方;那鲜花开满的地方啊,是父亲死去的地方……”
武汉的秋夜,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静。
2009/9/17
周云蓬
赵已然
冬子
周云蓬
赵已然
周云蓬
赵已然
雪山音乐节
冬子《十方》
吴维
生命之饼

生命之饼
刘2
刘东明的宣传画
王啸
念餐吧
吴吞
野孩子赵已然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他说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反正是越搬越远,已经搬到跟北京没什么关系的地方了。他经常没有钱,有一次住在白庙,他都四天没有一分钱了,正好碰见万圣节。平常这种时候,赵已然很会享受这种孤独。练鼓,看书,要不就在午后,把衣服脱光了躺在院子里晒两个小时的太阳。但那天是个节日,他很想出去玩一下,很想去和其他人一道狂欢一晚,喝一点威士忌,或者,去飞两片叶子。
但是他从九月份开始,就没有挣到过一分钱。不是他不能去靠打鼓挣钱,而是他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贫穷就去冒充朋克,或者去迎合可以换钱的媚俗的音乐。
那一年,他四十岁。
中国的音乐市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他像一匹年老的孤狼,爪牙已经不再锋利,他误入了一个自己根本应付不了的禁区,在熟悉又陌生、认识又不认识的山林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终于被伤着了,喘着气缩在了一个角落里。
许多时候,他靠一包方便面度过一天,或者,是一块玉米面发糕和一些瓜果。他靠着这些东西在房间里疯狂地打鼓,弹琴,却没有人去仔细倾听。他是中国最好的布鲁斯音乐的吉他手,精湛,纯熟的技巧在业内无人不知,但他却只能在黄昏狠心把朋友送他的一把刀,压给村口小商店的老板换取两瓶啤酒。
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连借钱的技法和技术都不会,他只会在深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在空空的院落中,为墙头的荒草弹奏中国最好的音乐。
2004年4月11日,赵已然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信。
尊敬的爸爸:
我此一生,悲也好,喜也好,成也好,败也好,我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事。并非有意或无意而为。正像20多年前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样,乃已然者也之事。
名利二字,并非我所不齿、不屑。相反,我很尊重。只不过我所求者,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和利。
两年多来,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像我一样生活着的朋友,一样的道德观念,一样的生命态度,而他们比我更彻底、更纯粹。他们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们的支撑和宠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他们让我痛苦、迷茫、屈辱地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坦然、踏实了。我知道,我有同志了……
2009年秋天,赵已然路过武汉去香港。深夜,我在汉口的一个宵夜摊上接他吃饭。赵老大依旧是紧身的长裤,牛仔上衣,二十年前的装束和老做派,让人觉得温暖,和煦。他告诉我,最近终于重新开始唱歌了。有一家公司和他签约出版一张唱片,那将是他的第一张正式唱片。
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不喝酒了,对我说:“我要去深圳和香港做两个专场。顺便,去买一把自己的琴。”,我喝了一杯酒,望着他,“我把唱片的版权费拿出来,我去不了欧洲,机票太贵了,香港应该可以买到一把琴!”。
那天的武汉街头,正是初秋,有附近住家的女人穿着睡衣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真希望那天是1988年,赵已然年轻了二十岁,他在黯淡的路灯下畅谈音乐,依旧壮怀激烈,傲视群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