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女孩送到家 自始至终没细看
已是农历十月,草木枯黄,这正是准备过冬柴禾的时候。因为正处在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人们腹中饥饿,热力不足,如果没有树兜子之类的烤火“大柴”,就更加难以抵御严寒而度过漫长的冬天。我家廊檐东头,有一个用土坯垒的“鸡畴子”(鸡舍),上面已堆起不少新打回的“大柴”。
这大概是1959年或1960年入冬后的一天上午,我又上山打“大柴”了。挑柴用的竹箢子是自己做的,下面用核桃粗的牛筋树以火苗烧软,弯成“U”字形,用竹篾将其编出簸箕状的竹箢;再将一棵青竹由根部往上,劈到与成人腰部同高,也在火苗上把需要弯转之处烤软,在中部分岔处拧成提手,两端弯折成钩状,成三角“人”字形绑定在箢子上,成为“箢系”。我将两只竹箢子横竖着套在一起,用扁担挑于背后,前面的扁担头上挂把大挖锄,一手捉着锄把,经过下董堂的塘埂,前往上董堂(也许是上地鸡洼)山上打“大柴”。
几天之前,曾下过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雪后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的阳坡上雪已化尽,枯草在山风中摇摆起伏,窸簌作响,为低吼的松涛伴以浅唱。而阴坡、沟底和松林之内,仍有尚未融化完的片片积雪。有的积雪上面,断断续续地残留着小动物的脚印。
我在松树林里钻来钻去,寻找别人砍了树干的松树兜子。松树全靠种子繁殖,其兜子和根部不会萌长幼树,所以挖松树兜子是打柴人的光明正大行为,自己心安理得,也不怕被山主干预。
渐渐地,箢子里有了一些树兜,我挑起来转移到另一面山坡,继续寻找可以当柴挖的树兜。当太阳已经移到头顶偏南,我意识到时已过午。树兜柴也已装到箢系的半腰,这担柴已不轻了,当然我的肚子也早饿了,于是决定回家。
当我挑着柴慢慢爬上山顶,走下山梁和山冲,终于回到家的时候,母亲迎在大门口,笑眯眯地小声喊着我的乳名说:“享毛,你看家里来了哪个?”我把柴担挑进院子放下,发现廊檐下站着一个小姑娘,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儿!
“这女孩是哪儿来的?”我问。
“是来跟你做媳妇的。”妈小声地说。
我脑门猛地一热,说不清是害羞还是生气,或者二者皆有。
原来,这是一个被她家长送到我家的女孩。
在我家西面,从蒋家冲翻过大山,是一条“深山藏古寺”的峡谷。远在隋唐年间,峡谷中建起一座寺院,据说前往进香求愿者,大都能有求必应,百事皆灵,人们便把这座寺院称为“百灵寺”。全国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这座寺院未能幸免。寺院被毁后,山谷里的村子仍叫“百灵寺”。这里属于大悟县姚畈乡,大山这边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该村的一户陈姓人家,女儿嫁给了我们生产大队云蒙寺的刘子英。刘子英比我年长一点,曾是小学同学,与陈女成亲纯属早婚。
那几年,全国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人们都在过“粮食关”,日子是那么难熬。家乡到处都有饿死人的现象,相邻的河南信阳地区还发生了饿死百万之众的“信阳事件”。陈姓人家所住的百灵寺,是一个交通非常闭塞的山沟,田地少而贫瘠,农民交完公粮后,粮食奇缺,有的人也已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云蒙寺的刘家人以为,我父亲是生产大队的书记,我家又善于计划生活,非常节俭,家中不会断粮,就把想像中的主意告知了百灵寺的陈家。于是,陈家就把小女儿(刘子英的妻妹)送到我家,请求我家予以收留,给我做媳妇。
现在想来,陈家的做法,有点儿像旧社会出卖童养媳。人在饿极的时候,顾不得许多常理,会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其实,我家人多劳力少,是生产队有名的缺粮户;父亲虽是生产大队的书记,但那时当这样的干部纯属为大家办事、为国家尽义务,既无任何报酬,也不多分一粒粮食。父亲是个正派之人,从不占公家和群众一点便宜。我家能够维持着生活,基本不断粮,是因为父母每年从分到新粮开始,就严格实行计划用粮,有粮当做无粮过,尽量利用代食之物。
父母都是心软的人,明知道增加一口人吃饭意味着什么,在婉拒无效的情况下,把女孩收留了下来,并给了陈家两升(八斤左右)救命的大米。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也不是急于说媳妇的年龄。那时,饥饿的人们营养不良,生理失调,分泌紊乱,农村妇女怀不上孕,婴幼儿成活率低,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披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河南信阳地区有九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以上。自然,年轻人结婚更加不易,最大的问题是办喜事时管不起亲友吃饭。有的人在那几年办喜事,手拿几毛钱来赶礼的人很多,目的就是讨顿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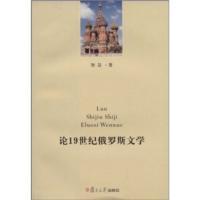
来我家的女孩大约有十二三岁,长的什么模样,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一眼。一是不好意思细看,二是没有兴趣细看。另外,我从来也没有单独跟她说过一句话。不像现在的少男少女,管你是亲不是亲,都没有太多的距离。现在想来,我有点儿过分,很对不住她。我朦胧地记得,她像其他农村女孩一样,十分乖巧懂事,也很勤快。她把我妈叫妈,主动地帮妈做家务。妈把她当自己女儿一样看待,每天“陈毛、陈毛”地叫着,晚上让她跟自己睡在一起。她完全就像我家一名成员,彼此相处很和谐。但是,她年龄太小,我年龄也不大且没有任何热情,父母也不愿意乘人之危。新社会了,家里养个小媳妇算什么?所以,女孩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以后,就通知其家人把她接回去了(也许是我父亲把她送到云蒙寺她姐姐家的)。临走,我家又给了一些大米给她家。母亲后来说,女孩来的时候面黄肌瘦,在我家住两个月后,长胖了,脸色也好看了。她后来的情况,我不得而知。
在这前后,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河南人,带着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孩来到我家,非要把女孩留下给我做媳妇。他说他那边的很多人都饿死了,自己家也没有饭吃。我看到,这个女孩由于长期饥饿,也是面黄肌瘦,但长得很灵巧,大大的眼睛。因是远道来人,不知底细,我家当然没有收留女孩,但留父女二人吃了顿饭,给了一点大米,让他们走了。
旧社会才有的现象,竟然出现在新社会。农民种出来的一点粮食,国家征收一空,然后无私地援助到并不诚实友好的国家,让人家吃不完扔掉,自己的人民却食不果腹。另外,国家粮库里也不是没有粮食,眼看饿死人仍然囤积在那里而不放粮救济。真不知那时的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1960年我辍学之后,姑父程学栈在他们丁桥那边给我介绍了个姓程的女孩。亲事说定,家人叫我礼节性地去女方家看看,我坚决不去,父母骂我,我也不去,那时自己对说媳妇之事极为反感。拖了数月,因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女孩的哥哥为了活命而偷杀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被上面抓去严刑拷打,可怜他坐牢而饿死。可怕的悲剧发生后,这一家人被迫搬走了,我非常逆反的亲事也顺理成章地结束。
在家乡农村,男女二十四五岁就算大龄,男孩十八九岁、女孩十七八岁完婚多的是。扬兵畈的章玉金成亲时,媳妇才13岁(生儿子章黑子时难产而逝)。不知为什么,我对别人给我提亲说媳妇的事十分反感和抵触。唯一的一个例外是,1963年春,我去姚畈公社丁桥大队桐子冲(此村1978年修建水库时被拆),到我三姑家有事。三姑做了很多菜,姑父程学栈陪我正吃饭,突然来了一个姑娘。姑父介绍说,这是他本家程木匠的女儿。我早就听说过,有个外地来的木匠,到这个村落户后,跟我姑父认了本家。他有个独生女儿,年龄比我大一岁。
这女孩在门口站了一小会,跟我三姑说说话就走了。也许是三姑有意叫她来的,让我见一下。只见她高挑个儿,乌黑的辫子,人长得非常漂亮。按当时的眼光,是我从未见过的美女。我虽然刚刚吃了几口饭,就再也吃不下了,推辞着说自己不饿、已吃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女孩产生如此爱慕,第一次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但在那时,无论是对女孩,还是对三姑和姑父,我都没有任何表达的经验和勇气,没有任何大方而得当的语言,只是努力地掩饰自己。
也许,我三姑和姑父曾跟程木匠提到过我,甚至没少夸奖我。在我们当地及四周,提起我父亲,德高望重,口碑甚好;说到他的儿子我,人们也知道是个不错的后生,这是我们的优势之处。但是,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家里比较贫穷,我下面还有两个痴呆聋哑的残疾弟弟。虽然我后来进城工作而改变了命运,哥哥娶到了漂亮能干的嫂子,可在当地,我们这种家境也尽人皆知,构成了提媒说亲的绝对劣势。
后来,姑父没有捎来喜讯,我曾一度怀疑他办事不力。程木匠的心理是,吐了怕是一块肉,吞了怕是一块骨头。我十分自卑,但也很理解。
我从部队退伍之后,曾听姑父提起,这女孩嫁给了姚畈镇供销社布店的一个营业员,后来又随夫搬到了大悟县芳畈镇南面的小河。
岁月悠悠,带走了多少酸甜与悲欢!生活就像打柴,要想打满柴担并挑回家,总要翻山越岭,出大力流大汗。也只有不乱砍乱挖,才能维护生态,确保青山不老。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郑州,晴)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