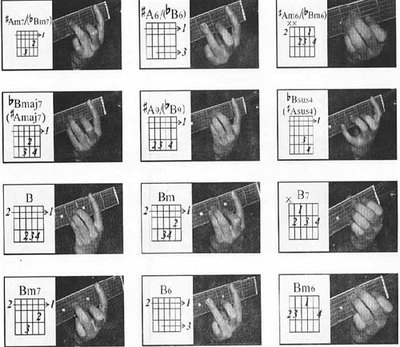去年春天

美好的事物中总包含着险恶。那险恶并非来自美好本身,而是隐藏在命运里。但对于命运,没有人能够参透。
去年春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很多年都没在家里过阴历生日了,今年回来过吧。自从我再次结婚并有了孩子,母亲似乎终于能够原谅我了,原谅我辜负别人,原谅我放纵自己。虽然她不会明白在我生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知道我过得不易,她曾经偷偷给我算命,并暗暗期待我那糟糕的生活终究有所改变。这改变出现了,她也在晚年有了最想要的孙女。她捧着那个婴儿,笑得那么开心。
每次回家前,我照例会失眠,所以,我总是以极度疲倦的样子回到家里。但一切都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欣喜。我回到土地,回到熟悉的气息,回到燕子与和风之中。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的阴历生日,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饭。一大帮子人从县城赶了回来,我们喝了很多酒,我几乎有些神智不清,但奇迹般的没有大醉。姐夫、堂兄和弟弟在院子里玩了一会扑克,便坐同一辆车回漕河,我则倒头便睡。半梦半醒间,听到手机响,接起来听,是二姐惊惶的声音,她告诉我,拉着我家六口人的那辆车在刘河附近出了车祸。司机中午没有喝酒,但车祸很严重,弟弟从车里飞了出去、昏迷 了,大姐夫满头都是血。万幸的是,十多分钟后,二姐夫从后面赶到,飞快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回家过生日,这一切都会避免。如果我没有留下大姐夫的车,他可能不会受伤。但我不能明白的是,命运如此惩罚我的原因何在。而从这起噩梦般的事故开始,去年整整一年里,莫名其妙的坏事连番找上家门。有人查出了癌症,有人受时局的牵累而丢掉工作,有人摔断了胳膊,几乎每个人都轮上了坏运气。回到北京没多久,她生了一场奇怪的病,连续高烧十多天,在哪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我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让她舅妈照看,我则一边照顾病人一边工作。直到住进一家大医院的特需病房,她才慢慢有了人样,但体重一下子减掉了十多斤。我中途去看过女儿一次,她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很多天看不到爸爸妈妈,显然在她心里留下了伤痕。她趴在地上,倔强而烦乱地玩着几个空瓶子。我走之后,听说她哭得很厉害。我们把她接回家的时候,她看到妈妈,马上哭得震天动地。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生怕妈妈不见了。
去年整整一年里,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父亲。我一直不敢说出这个,生怕它会像一小段波函数一样坍塌,成为现实。秋天,母亲生日的时候,我又回去了一次,父亲状态尚好,只是体力差了很多。他还是闲不下来,但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早晨,露水还没干,他就跑到山坪挖红薯,我赶紧去帮忙。我们很少说话,但我不时想起小时候跟他一起干农活的情景。他对自己苛刻,对家人同样严厉,但在他那刀子般的锋利和雷霆般的威严之后,仍然有浓厚的慈爱流露出来。他从没有说过他爱我,也从没有说过他曾为我感到骄傲,但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那几天,我一有空就在阳光下劈柴,据说足足劈了几百斤。我也没有想到我还那么能干。我只知道的是,如果我不干,这些活最终会落在他头上。何况我喜欢做。在我少年时,我帮他拉锯、跟他学劈柴,在当了多年的诗人和评论员之后,竟然还没有忘记这些技巧。而在我内心深处,我是那么喜欢做一个农民。
那年春天,过完生日没几天就是清明。听父亲说,修家谱的时候,族人到处走访,竟然找到了一处元代的祖坟。蔡姓迁蕲的始祖,本来在元朝做官,但是看世道不好,开了小差。他在升职的途中,路过蕲春西河驿,看到山川秀丽,一条大河从莽莽苍苍的地方流淌下来,就带着一家人溯流而上,从此归隐在山林里。他娶了两个老婆,生了十三个孩子,留下一本手写的家谱,告诉后人,他们的老根在福建建阳麻沙镇,祖上有四世九儒的辉煌。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祖先竟然没有传下丝毫的家学,佶屈聱牙的理学失散了也罢,看风水的手艺却也丢掉了,于是子孙们从此只好土里扒饭吃。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意吧?
这次找到的祖坟,埋着他的第五个儿子,彦五公。清明那天,全村在家的男丁开着车,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去祭祖。坟边油菜花开得正旺,艳阳下,纸钱燃起的火苗几乎看不见。我虔诚地磕头,心里边默默念诵的,大概是要祖宗保佑我的家人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我如此之久没写新的文章,与我心里隐秘的、含混的恐惧有关。我知道命运是不真实的,我也知道把一切苦痛归咎于自己并无道理,但当我已经这么想了,我就被幽暗中的事物封住了嘴唇。我的心里仍然有浩大的歌声,可惜,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