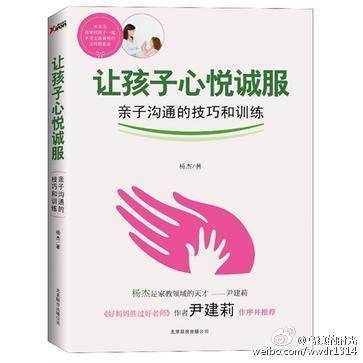曹少钦的长眉微微一拧,是厌烦的神情,群侪不知哪句话不中他意,便不敢再多语,老实提步随他继续前行。已走出几丈地,忽闻身后一个童稚的声音,接着他刚才的下文诵道:“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稚嫩如恋巢乳燕一般的音色,仍带着抛舍不去、不忍抛舍的闵音,或许是因为害怕,还在微微的颤抖。
曹少钦诧异回首,低贱的小内侍不知何时,已经在他的身后跪直了身子,敝旧青袍下的身量明显比寻常的七岁孩童更显瘦小,一张已可想见未来俊美五官的小脸上,黑白分明的清朗双目奋力掩饰下惊恐泪水,倔强而稍带挑衅地直视着眼前满身金玉的贵珰。
曹少钦注视着这个名叫雨济深的小宦,因为稍感惊讶而微微上扬的双眉已然低落,在众人一片不知所措的惊诧中,轻轻扬手,还未曾见动作,手中那本脊穿五孔,以数股丝线绞结串联的结实书册已经张张绽裂,经厂刻书特用的上等素白棉纸纷飞漫天,其中一页白纸黑字直冲向前,柔韧的纸张,携带着凌厉的掌风,啪的一声清响,如一记重重掌掴一样,小内侍清秀的右颊已经红肿了起来。
经厂掌司愕然望着曹少钦,呆了片刻才急转过头去呵斥泪流满面的雨济深:“大胆奴才,曹公已是分外手下留情了,还不快磕头谢恩!”
貂珰的凤目冷淡地掠过仍然倔强长跪的小宦,对手执藤条的督导内侍下令道:“笞他二十,就叫他跪在这里,晚上不许吃饭。”
重重的笞挞声随即在他的身后响起,难说出乎他所料,抑或如他所料,其间并没有夹杂哭泣和求饶。雅贵的貂珰没有再回头,直至颀长削直的身影为红墙掩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