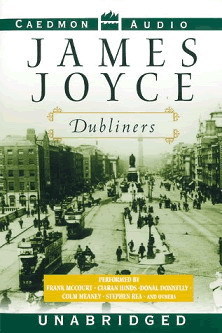(45)怀念我们的父亲吴德峰同志
——亲爱的爸爸诞辰一百周年祭
(一)
卅生 爱生 持生
一九九六年是我们的父亲吴德峰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也是逝世20周年。我们的父亲历经坎坷,在半个多世纪中,为国、为民、为革命的事业奔波奉献了一生。由于他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一些很老的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一九八一年他逝世五周年时王震、黄火青、肖克、郭述申、袁任远等五位老同志,曾以“怀念无名英雄吴德峰同志”为题著述文章,缅怀了他光辉、战斗、杰出的一生,称他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的刊物刊登了一篇题曰“中共内幕”的文章,称他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滑的吴德峰”,使他蒙上了神秘色彩,成为解放后某些作家笔下的传奇式人物。但他老人家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始终是受崇敬的严师、慈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执着、无私奉献精神;他对敌人、对艰难险阻和对突发事件,有随机应变、临危不惧、机智多谋、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毅力;他具有博闻强识、勤奋好学、思维敏捷和逻辑推理、分析预测、组织能力强的特点,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刚正不阿。他教育我们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德,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深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是我们永远学习教育子孙的榜样。
坚定的信念 无私的奉献
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我们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四品“通奉谏议大夫”,在云南等地做过官,辛亥革命前夕他当过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受“维新”“变法”的影响,先后送他两个儿子吴元泽(我们的二伯祖父)和吴元钧(我们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吴元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任新军战时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衔至中将;吴元钧在辛亥革命时曾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等职,衔至少将。吴家与黎元洪在历史上有通家友好关系,来往密切,黎元洪任大总统时曾邀请吴元泽、吴元钧到北京为幕僚。在吴家武昌、保康故居都曾挂有黎元洪为表彰吴氏兄弟功绩书题的《年高德绍》等字匾。
我们的父亲青少年时期已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也正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之际。父亲从小就受着家庭、社会和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转变的思潮影响和熏陶。辛亥革命前后他正值十三、四岁,随父亲吴元钧到武汉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念书,曾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父亲考入了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这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曾与毛泽东等同志有过书信往来,和肖楚女等同志建立深厚革命友情,共同研讨过中国之命运、前途;这期间,他参加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潮运动,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的教育厅长谈判,面斥教育界的黑暗腐朽,驱逐了反动校长,达到了革新教育的政治目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当时学潮的学生领袖人物之一,从而和当时在该校执教并任校监的董必武同志建立了革命的师生之情,与陈潭秋、徐全直等同志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友谊。
1921年陈潭秋同志推荐我们父亲任我党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由于他积极努力工作,该社成绩显著,在社会上影响广泛,很快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的宣传喉舌。该社越来越大的影响,引起了反动派、军阀的恐慌,于1922年夏被湖北督军肖耀南以“言论过激”为借口查封。经受了党的严格考查和斗争洗礼,在董必武、陈潭秋同志的坚持介绍下,党组织终於于1924年2月批准接纳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候补期几经缩短为一个月转正。同年七月,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员。揭开了他和我们的母亲戚元德同志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并蒂连理,共同奋斗的革命新篇章。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这样对我们子女说:“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多少革命者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你们必须更加努力继承实先烈遗志。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不少人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意志消沉,登报声明脱党、退党,甚至背叛革命。但我们的父亲,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坚信马列主义,革命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毅然绝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己取得的高官厚禄,抛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冒着被通辑、杀头的危险,顶着枪林弹雨,义无返顾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
在革命的初期,我党的活动经费来源缺乏,参加革命工作根本没有工资待遇,基本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并支持党的经费开支。父亲除靠教书、做公务员挣钱外,还经常从家里拿钱为党筹集用款,正如袁溥之阿姨回忆的那样,当时在武汉地区经常因工作哪个同志急需用钱一时筹集不到,总是要找吴德峰同志想办法,他从来都是千方百计解决,有求必应。一九二五年二月,根据党的要求,父亲出面开办了崇实中学,目的是团结、教育、培养革命青年志士和干部。这个学校的创办,没向党要一分钱,校舍是利用吴家在武昌黄土坡的一幢楼房,开办费是父亲动员我们的祖母龚敬勋女士变卖了她陪嫁的名贵首饰的款项,教员多是有名望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除少数职员拿微薄的工薪外几乎都是义务任教不拿一分钱。1928年江西省委被破坏波及九江,父母亲到上海找中央汇报以及安置其他同志的费用多是由祖母提供的。据母亲回忆,从1929年到他们进江西苏区以前。几乎我们祖母每月都要拿出一、二百块银元供父亲使用,绝大部分都用于革命活动和资助有困难的同志。记得刘伯承同志的岳母(即吴锦春同志的母亲)大年初一在上海去逝,刘伯承同志找到父亲,父亲当即从家里拿了钱为老人办理后事。就是解放后我们的父母亲还经常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钱出来资助有困难的同志和烈士的遗孤遗属。
我们的父亲党性、组织原则性很强,在五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时时、事事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需要、哪里危险他就到那里,从不讨价还价。大革命失败后,他刚从国民政府武汉公安局撤回,国民党当局还在四处通缉捉拿他,党因董必武同志生病决定改任他为湖北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中共鄂南特委书记、代中共湖北军委书记,立即去鄂南组织领导暴动(原定董必武同志去)。他二话没讲,连夜化装奔赴蒲圻地区。暴动开始取得一些胜利,缴获一些军需、弹药.但终因中央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动组织起义暴动,终因缺乏枪支弹药、寡不敌众导致这次暴动失败。失败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率部在芦苇荡与敌人周旋打了一天一夜,最后突围退到九宫山地区,由于在水中长时间浸泡,父亲双膝患了急性关节炎。回武汉后带病,一方面向中央、省委汇报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继续领导全省其他地区起义暴动工作。
1927年底,父亲调江西省委先后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领导该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发动工作。后
,
我们的父母生前50年相濡以沫,作为革命伴侣为同志们共识被赞誉为党
内“模范夫妻”。这套画共三册封面分别为红黄缘三色,是父母情爱的
鉴证遗物,上款书写“惇允吾妹爱存”下书写“铁哥赠于吉安一九二七、
十二、八、”(元德字号惇允。允妹、铁哥是他们夫妻间多年贯用的爱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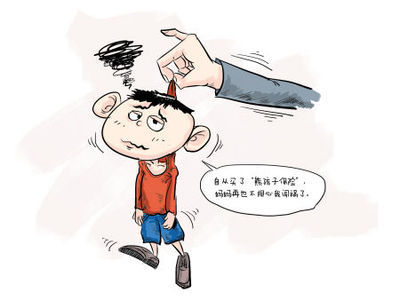
江西省委(在南昌)被敌人破坏,波及九江等地,他当即立断转移安顿机关和同志,携同我们快临产的母亲弃家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到上海后,又遇到河南省党组织被叛徒出卖,遭到全面破坏,国民党军、警、特、宪云集开封,大批同志遭到捕杀,中央又紧急决定,立即派我们父亲去河南任军委书记,消灭叛徒,重建组织。因工作需要母亲抱着未满月的爱生同行,双脚肿的只能穿很大一双男鞋。到开封通过其堂弟关系,站住脚,组织了特科及打狗队,消灭叛徒、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使党组织很快恢复。
1929年初,他在上海任中央交通局长期间,担负着传递党的各级组织和地区之间互相往来的秘密文件、情报、输送党的干部、物资、经费以及国内国际联系等重要、特殊任务的组织领导工作,顾顺章、向中发先后叛变,他又紧急投入应变,安排转移、营救同志,与叛徒特务做了坚决有效的斗争。
1932年他进苏区,先后任中央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分局局长、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江西省委委员、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湘赣省委委员等职,与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做过坚决斗争,坚决反对、抵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他先后以保卫分局局长名义发布了一系列通告、通令,制定了严格的保卫工作纪律,规定严禁逼供信、废除一切刑具,解救了张启龙一批好同志,上述通告在《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中有记载。
1934年春夏湘赣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进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长征途中他先后任六军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湘鄂川黔肃反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北局白区工作部部长等职,与张国焘反党分裂党中央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在《长征日记》中有记录。
1936年月11月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后,父亲应召随同周恩来同志赶赴西安处理事件,后因时局急剧变化,他由公开转为秘密,留在西安负责秘密情报领导工作,在战胜胡宗南的斗争中,我们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共同立下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周付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我们父母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给于极高的评价和明确的肯定,在文革中针对造反派要打倒宋任远同志的问题曾讲到过,“吴德峰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
1946年初,中央调他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因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改派李克农同志任职,父亲用中草药稍控制病情后,中央因工作需要仍决定父亲必须立即赶赴北平任执行部秘书兼武汉别顾问,负责武汉执行组工作,此期间我们父亲曾向张体学旅等部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为中原军区提供物资、经费及重要情报,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1946年7月父亲任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白军工作部部长,1947年春夏为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中央决定我们父亲兼任阜平县县委书记主持土改工作,此时他慢性盲肠炎复发,他仍坚持自用中药控制,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错误倾向。
1949年5月14日,他受命任中央直辖市武汉市市长。武汉刚解放时,城市千疮百孔,百业待兴,正常秩序尚未恢复,城市建设、粮食、防汛、灾民救济安置、特务的破坏暗杀等等问题一件件接踵而来,特务曾几次在新生花园等处预谋暗杀我们父亲均未得逞。我们父亲那段时间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到第二天凌晨,那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和我们母亲同在武汉市工作(当时我们母亲戚元德同志任武汉市妇联主任)仍过着战争年代星期六见面的家庭生活,有时一两个月见不到一次面。日理万机的工作使他累得患了高血压、心脏病(心电图T波严重倒置),他连看病住院的时间都没有,仍带着病日夜操劳、坚持忘我工作,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无不为他这种呕心沥血、无私无畏的革命工作精神所感动。
我们父母一生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展转南北。1954年前从未有过一个安定的家,妻子儿女很少团聚。父母共生我们兄妹九人。在战争年代除小妹持生一人跟随父母转战南北外,其他兄弟姐妹均因战争环境残酷不允许,从小送人或寄养在外。其中三人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养子、丫头。九个孩子在解放后只剩下五个,有两人在解放前因病得不到治疗夭折,还有两个在苏区和长征途中送给人当童养媳、养子至今生死下落不明。父亲为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他一生和所有一切,包括他的家庭、财产、名誉、地位以及儿女亲情。正如王震同志回忆时讲的,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是逼上梁山的,而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奉者,是一个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坚贞不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足智多谋 坚韧不跋
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百折不挠、坚韧不跋也是我们父亲为人做事的品德和风格。
一九二五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父亲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经国民党左派邓寅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公安局局长。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叛变,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组织通知父亲立即撤退,父亲根据他手里掌握的情况分析,认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国民党内部清党一时还清不到他头上来,请求组织同意他继续坚守在岗位上,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为我们的党员发放护照、通行证(当时的军警外出均持护照证明身份),使得许多党员得以及时安全转移和潜伏下来。直到国民党开始清理内部排斥左派时,军阀唐生智派员接收公安局局长职务并预谋将父亲解职后秘密捕杀。父亲得知这一情报后,一方面向中央请示汇报准备撤退,一方面利用还有的权力,布置组织召开规模盛大的“迎新送旧”大会,并特意通知郊区几个县大队持枪荷弹进城参加会议,新任局长一看这阵势未敢轻举妄动。会后父亲在欢送“吴局长荣升”的锣鼓、炮竹声中,在大队人马护送下安然归宅,在家人招待烟茶分发赏钱时,父亲从后门到友谊津(吴家另宅)化妆来到江边,与等候在那里的我们母亲戚元德同志会合,等敌人封江通缉父亲时,他已安全抵达汉口胡文裕姨妈家(我们母亲的同窗好友,革命的忠实同情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我们父母从开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贾身份租房住机关,房东太太见父母人口简单、绅士派,非常欢迎,谁知家具一到马上翻脸,说什么也不让进门,要住房必须得找三家铺保,一问才知道,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样,前面的房客没住几天就被以共产党罪名抓走,家具现在还堆在一间客房中,父亲一听毫不动声色的解释,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随便临时购买的一套家具,并答应立即找三个铺保,房东太太这才答应住下,事后父亲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并下发通知,今后住机关购买家具、用品必须注意避免千篇一律买便宜货,防止暴露身份。
一九三六年长征途中,二、四方面军汇合后,父亲由二方面军调中共西北局任白军工作部部长,由于他坚持原则,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遭到张国焘的忌恨、排斥,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除掉不可。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借口扩张武装,收编地方武装(土匪)建立新根据地为由,派我们父亲、母亲带着十多个人去收编李中土匪的部队并任政委,妄图借刀杀人把父亲甩掉。因为当时长征途中土匪部队很多,不堪一击,一打就投降,收编后补充枪支弹药,红军大部队一走,不少又哗变与红军为敌,李中的土匪部队也正是这种类型的。父亲留下,大部队走了,当晚李中就摆了“鸿门宴”,妄图把我们父母亲及同去的战友一网打尽,父亲识破了他们这一阴谋诡计,将人马一分为二,由我们母亲负责带几个人留守在土围子内等待接应,父亲仅带了几个特务员(当时对警卫员称呼)持枪荷弹去赴宴,李中一看父亲有所准备,下不成手,只好放父亲回去。天黑后8点多钟,李忠拖着枪支弹药带着他的部队跑了,并杀了我们三个下连队未能及时返回住地的指导员。父亲带着人追击未追上,只好返回赶大部队。回到西北局后,张国焘果真借口父亲“丢了部队”要军法处置杀我们父亲的头。父亲拍案大骂,揭穿了他的阴谋,这时己与一方面军汇合,在任弼时、朱老总等同志制止下,张国焘的阴谋才未得逞。
一九三八年父亲留在西安做情报工作,他沉着勇敢、足智多谋地领导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天父亲同罗表叔(罗青长同志是革命工作关系的表叔)出外办事,在表叔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抄把子关卡(即搜查行人的关卡)父亲暗示罗表叔,一同很自然地走进了路边的书店。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父亲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表叔提着箱子先行走,他落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他时,很自然的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远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象突然想起手中的书,慢回转身原地不动的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正在搜查第二个人就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一九四六年夏,父亲在军事调处武汉执行小组当顾问时,截获蒋介石调兵遣将围歼中原军区(即第五师)的重要情报,使中原军区最后得以从国民党合围的口袋中突围出来。中原军区突围后,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在敌人对他下毒手前,周恩来同志命父亲经南京先期撤回张家口。
撤回张家口后聂荣臻同志向中央请求,留我们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由于晋察冀边区是联系各解放区的枢纽,战略位置重要,中央就同意了聂荣臻同志的意见,父亲留下来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白军工作部部长)重点抓敌军工作,在他和康健生同志领导下成功的策反了傅作义的骑兵团起义。团长海弗龙是蒙古族人,后送到内蒙云泽同志(即乌兰夫同志)处。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军主动从张家口战略撤退,父亲因工作需要,与康建生等同志坚持到最后。当他们离开时,傅作义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的水母宫一带,几乎同敌人擦肩而过。几昼夜的辛苦劳累,使他在赴阜平县途中,从马背上晕倒摔下来,人事不省。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极为坎坷不平,但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坚持党的路线原则,曾与王明、刘士杰、张国焘、江青、谢富治等错误路线和危害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做过长期不懈、坚忍不拔的斗争。但他对同志对战友则关心爱护备至。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途中,他曾因工作组织解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王震、廖承志、黄火青、王首道、张启龙、周兴、李先念、陈绍敏、陈宗瑛、马庭士、王铮、赖传夫、肖佛先等等同志之危难或性命。解放后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自己因营养不良浮肿,却让持生陪他到北京台基厂附近商店买蛋黄粉,寄给一个当时政法系统公派去苏联攻读法律生病的学生,鼓励、嘱咐他早日恢复健康坚持完成学业。
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先后在某些别有用心、心怀鬼胎人的策划、指使下我们父亲就被陆续戴上“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官僚军阀”、“地主恶霸”、“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帽子,被专政揪斗、隔离审查,但他仍不顾又被扣上“叛徒头子”、“特务头子”等罪名帽子,始终如一坚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本着对党、对同志认真负责态度,实事求是地去为一些老战友和曾在他领导下做过秘密情报、机要交通和党政工作的同事以及经我党策反、统战从国民党反动阵营起义投诚、转过来的有功人员做历史外调问题的证明,证明王震等同志在二、四方军会合后是坚决反对张国焘通电一方军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的分裂主义行径,不是“三反分子”;证明周惠年、肖贵昌、安子文等同志在他手下做秘密情报、交通工作时是有功劳贡献的,没有“叛变自首”等违犯组织原则问题,“不是叛徒”、“特务”、“内奸”;证明王方明、肖德、霍建台、江子麟、戴中溶、陈建晨、杨小初和李步青夫妇、候林斌等等同志,是为完成党的特殊任务,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员和支持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功劳、贡献和支持者,不是“敌特”、“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对王铮、刘文华夫妇等起义、投诚人员则证明肯定他们弃暗投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是正确、有功的,为我党在军事、政治上打败、瓦解国民党反动派阵营开了先例是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刘文华是国民党反动派最早向我党投诚的高级军政人员之一,王铮为我党、我军破译敌电台密码,建设电台立有卓越功绩);他还为周惠年、肖贵昌、刘文华等同志的问题,专门向周总理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同志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常向来访外调人员或要我们子女去询问了解李克农同志遗属及孔原等老战友情况,当得知徐明阿姨被迫害至死后他和我们母亲难过的流下热泪;得知李英儒(父亲在晋察冀联络部时的秘书)、阮波(父亲在武汉市的秘书)、彭炎等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在狱中患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等疾病,病重吐血时,他就亲自配中药、营养药粉装成胶囊和衣物叫家属设法带到狱中为他们治病、保暖,并嘱咐家属转告他们坚持原则活着出来就是胜利!后又得知这些同志的家属、孩子也被牵连受迫害,他和我们母亲怕当时环境下孩子们年纪小无人管,流离失所生活没有着落或被坏人引入歧途,就在父亲工资停发、只靠母亲一人工资看病维持生活艰难情况下,仍组织发动中生、琛燕、持生、国良和仲平(父亲长征勤务员肖佛先同志的儿子)等孩子拿着钱、粮票、衣物四处打探寻找孔东、孔--丹、彭小蒙姐弟等一些爹娘不能照管的孩子,找到彭炎同志的孩子悄悄绐他们送去钱、粮票,要彭小蒙赶快到他父母过去打游击的老根据地去,告诉她那里的群众最了解他们父母,会关心安排她的,给彭小维准备衣物、被褥行装送她去建设兵团,又买好火车票又托人把年幼的彭小佳送往上海他大哥大嫂家抚养;
追悼会(左起)持生小蒙小薇小玲追悼会上(左起)持生 陶涛(李泛五夫人)
当时我们父母经常让我们去看望张淑文(李英儒的夫人当时没有工作靠织网兜养家糊口)、周惠年(当时仃发工资仅靠微薄一点生活费维持家用)等同志带钱、带物、补贴家用;一次持生回家讲,解放军总后勤学院李泛山同志(原红四方面的)被关押全家仅靠其夫人陶涛同志工资过生活,月初刚发工资一下子被小偷全拿走,又赶上孩子上山下乡去边远地区要置办行装急得病了全家一愁莫展,我们父母听了二话没讲,就将当时手中仅有的二百元钱全部取出,让持生立即送绐陶涛同志解急度难之用(陶涛文革后找到持生非还这笔款和参加两位老人追悼会时,仍感动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父母经常语重心长的对我们兄弟姐妹们说,他们都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他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和你们一样都是革命的后代、是党和国家的希望,你们兄妹也都是在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和叔叔阿姨们的关心照料下长大成人的,现在都自立啦,而这些弟弟妹妹们还小正在成长,需要人去关心、培养、教育,如果我们看到问题不管不问不负责任,听任这些孩子们流离失所,一旦他们发生不测或误入歧途,我们做为一个老党员如何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今后如何面对孩子的父母、我们的战友和同志,又如何向党、国家和人民群众交待。1975年我们父亲己年近八十岁还多次关心曾在他手下搞过秘密情报、交通工作同志的近况,我们从清理他的遗物中还看到他主动与李佩群等同志联络往来信件,信中仍向李佩群同志询问原在秘密交通系统工作过的曾波浪、颜伟良、熊明心等同志的现况和一些当时牺牲的交通员情况。就在他去世前病重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向看望他的罗青长等同志询问肖德等同志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还嘱咐罗要继续关心过问、向上反映没介决问题同志情况。父亲对自己身边周围群众的生活疾苦也很关心体贴,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时,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平房。他把儿孙们都叫回来同住,家里挤得满满的,但听到持生讲,她机关有一个女同志双腿瘫痪不能行走,一个女同志刚生孩子住在四面透风、不能遮雨的棚中时,就叫持生马上把他们都接到家里居住,每天还亲自过问关心他们吃喝生活等情况,一直住到数月后地震结束后才离开我们家。
一九五二年,因武汉市市立第二医院发生的一起“盗款未遂案”,在某些人的操纵下错误给父亲撤销在武汉市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和降级处分。所谓“纪案”提法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原本由武汉市公安局例行公事侦破一起仅壹仟二佰元(当时旧币为壹仟式佰万元)左右的“盗款未遂”抓小偷案,人为地与“市二医院付院长陈处枢打保姆(随军女战士)撤职处分”、“卫生部转来陈颉(化名)上告卫生局长宋瑛匿名信处理问题”、“公安局先后拘审‘盗案’嫌疑人及特嫌问题(由香港特务来信及纪凯夫曾任中统的职业据点中央药房的副经理引起,其兄纪憨就是特务)的纪凯夫”等几件事连在一起,演变成为“整个武汉市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体纠合包庇、纵容、阴谋、陷害市二医院一个普通文书纪凯夫”震惊中外、举世闻明的大案、要案,“中南局决定”改组了这个棣属中央直辖市的市委、市政府,处分处理了整个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干部,株连一大批老同志人人过关检查、捡讨、降级、党内处分,并将付市长周季方、卫生局长宋瑛、二医院监委王清、公安局办案侦察科长彭其光以及中南联合检查组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刘子胜等同志做为主谋、同案犯,分别予以逮捕、法办、判刑、开除党籍。对于这宗错综复杂的案中案在此我们不做更多的评述,但要讲明两点:一、对于处理“陈处舒打保姆”和“卫生部转来匿名信”两问题我们父亲从始至终都是坚持党性,按组织原则、程序及中央通知精神交有关部门逐级讨论研究确定的处分,处理是正确无误的,处理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抱着实事求是、治病救人、严励批评、帮助教育的态度,不存在辜息养奸、徇私枉法、结党营私、打击报复、包庇坏人等问题,父亲的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光明磊落的品格,长期在党内外、在武汉市市政府和市委都是有公论,受到大家赞许、认同是有档、有据、有材料可查证的;二、市二医院发生的“盗款未遂案”及“公安局拘审纪凯夫‘盗案’嫌疑人、特嫌问题”是由市委主持交市公安局办的案,根本不属任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某些人心怀鬼胎故意将此职篡改成“文教党组书记”)的吴德峰主管、分工负责。对我们父亲的处分决定事先未按党的组织原则基层逐级讨论通过上报中央批准(吴德峰做为中央直辖市市长是由毛泽东主席直接任免的),更未与父亲本人见面谈话,甚至开大会前都未通知会上要宣布处分他的决定,对他搞突然袭击(做为党员的权利父亲在撤职第二天曾找过邓子恢同志,就上述问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提出要看中央对他处分决定通知、批示文件或电话记录,邓子恢同志回答中央没有决定、批示文件,电话也没有记录)。因事发突然,大会一宣布,会场一片凝滞、谔然,很多同志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紧接着会议主持者点名要父亲表态,父亲当时心情很沉重,武汉的工作刚刚走入正轨,情况仍然很复杂,突如其来的变故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更大的乱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有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只有无条件的服从表态,“自己受党教育多年,犯了错误很感痛心,服从组织决定”。台下一片寂静不少党员、民主人士流下热泪,有人在抽泣、有人哭出咽音……,父亲的心情更加沉重,觉得肩负的压力更大了。散会后,警卫员和司机按常规在门口等他,他通知他们,他已被撤职,要他们马上回机关报到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他步行往回走,车子和警卫员、很多同志,仍跟在他的后面迟迟不肯离去。第二天上班,他又步行去机关,车子、警卫员加上秘书,办公厅主任都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甚至一个三轮车夫蹬着车跟上来说:“吴市长,您不坐市长小车,请坐我的车.我愿意天天接送你家(您的意思)上班、下班,不收一分钱。”父亲谢谢了他的好意,把他劝走,并停下来等后面的人跟上来。父亲问办公室主任:“你们跟在我后面干什么?!”办公室主任说:“保卫您的安全。”父亲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国民党特务要杀我,要把我赶下台,因我是市长,我现在被撤职已经不是市长了,他们的目的己达到还杀我干什么?!谢谢你们的关心,但这样做对党、对政府影响不好”。我们父亲被撤职后时时处处想的仍不是个人恩怨、得失,而更多的是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记得一次在汉口灯光球场进行了一场蓝球友谊比赛(父亲闲暇时很喜欢体育运动看比赛),开赛前父亲刚一进球场被看台上的观众发现,很多观众站起来向他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示敬意问候……,父母顾忌影响没等球赛开始就离席退场,并郑重其事的对我们母亲说,今天看台上观众突如其来向我热烈鼓掌示意问候关怀、实感受之有愧、受之不安,不管怎么说我是受撤职处分的市长,这样欢迎的场面、这样的热烈气氛不妥,搞得不好绐组织和新领导班子增加了付面压力,影响党、政府、群众协调一致及党群、干群和协关系和我党、政府威信、声誉,看耒这种场合今后我不宜再出现、出席,“受处分”的人就要有个“受处分”的样子,应该珍惜难得的闲空时间去埋头学习、努力充实提高自己,的确从此以后我们父亲基本深居简出,除工作外、专心攻读马列政策政法等类学习资料和书籍,很少再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父亲撤职后一段时间有很多同志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在父亲面前流露想不通,要去找中南局、党中央反映情况,父亲都耐心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有什么问题该向上反映的,他自己到时侯会按组织原则主动向上反映的。同样“纪案”也牵连到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母亲,也没有找我们母亲谈话,也没经过任何组织讨论,即没有处分决定,更没有宣布、通知本人,就稀里糊涂无缘无故地将上级中央正式下通知任命的中南局妇委书记、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政府委员、武汉市妇联主任等职务都罢免了,行政级别由八级降至拾级,她也同样与父亲一样在当时顾全大局正确对待的。父亲撤职降级后,开始没分配工作,他主动要求去“三反”办公室帮助搞了一段清理甄别工作,后调中南政法委员会工作。父亲时年57岁,毫不气馁地仍一如继往、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工作,这期间他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钻研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和专业知识。“宪法”颁布后,他又为配合宣传宪法,主持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闰宪法讲话》一书再版数次畅销全国。一九五四年中南局转发中央“撤消”对父亲的处分通知,恢复原级别待遇。张执一同志代表组织向他传达他们的问题搞错了,中央精神只在小范内冷处理解决(下面的干部由所在地方亦按中央精神解决处理好),表明工作可仍调回武汉市委或市政府恢复原职亦可留中南局政法委任主任的意图,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李先念同志干的很有成效,频繁的换人对武汉市工作不利,自己年纪大了愿意回中央工作,如果中央暂时不好安排就先留在中南政法委员会协助工作,干什么都行(张执一同志赞同父亲的看法不再回武汉市,并讲中南局某些人的意见亦不同意你再回武汉市工作,即便你要回武汉市工作最好也只担任市委专职第一付书记抓党务工作,不要再担任市政府市长)。不久父亲就调回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任付主任,恢复级别待遇。母亲也经中央组织部乔明甫、李步新同志谈话,查明了未经任何一级组织批准撤职、降级处分过她,恢复了级别待遇,因考虑国家经费困难,征得我们母亲同意象征性补发数月工资并重新分配工作,原订调司法部任付部长,母亲第一次向组织提出要求迥避不愿再和父亲在同一系统工作,经织同意后调全国总工会作为党组成员(享受付部级待遇)先后任组织部、干部部、女工部部长。到北京后,一次持生陪我们父亲去北京饭店理发碰到曾希圣叔叔,曾叔叔问到说:“吴老听说你的问题搞错了,换个别人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在什么地方、范围内处分的,就必须在什么地方、范围内恢复纠正……”。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后,罗瑞卿同志当着总理面对父亲讲,你的问题搞错了,我到武汉时你怎么没有讲……。处分撤消前父亲从不随便在党外谈“处分”问题,处分撤消后遇到有人鸣不平时他总是讲:“母亲错打了孩子,已经认为不对纠正了,难道孩子还能不依不饶吗?……,作为共产党员只能维护党的形象、威信不受损失,还有什么个人问题可计较”。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谢富治等人欺上瞒下,以莫须有罪名蒙骗群众,妄图再次把他至于死地,父亲这时已七十岁高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气管炎、白内障(眼睛开刀后不让休息,引起黄斑出血)等重疾,但从不气馁,意志信念仍是坚定不移,坚信终有一天真相大白。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出过去对付敌人的手段去对付整他的人?父亲说:整我的人不是都是敌人,对敌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同志怎能采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去对付呢?!父亲一生不管何时、何地,一言一行总是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威信为重,即便工作中受了天大的挫折、委屈也不会牢骚满腹、意志消沉、躺倒不干或一厥不振,他经常告诫我们,共产党人要以党性、革命利益为重,决不能拿别人的不公正和错误来惩罚自己,也就是不能放弃原则以歪就歪,以牙还牙,以错误的思想和方法去对待、对付别人,错上加错,对党、对自己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走向消极反面,甚致走上犯罪的道路。这都充分表现了父亲作为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负贵任的高风亮节品德和崇高的思想素质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