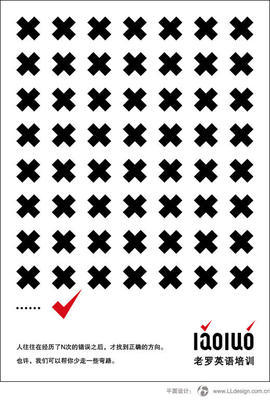乌仁娜.察哈图姬(UrnaChahar-Tugchi)蒙古族女歌手,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13.51,-0.13,-0.95%)草原,现定居德国。幼年即从祖母及双亲身上学会上百首传统蒙古民歌,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主修扬琴,并且以蒙古文创作诗词。自1994年起开始巡回世界演出,与各地乐人进行许多有趣的世界音乐实验。并且经常现身世界各地重要音乐节,在欧洲出版多张专辑。乌仁娜除了拥有刚柔并济、上下能跨四个八度的惊人广阔音域,对音乐的态度同样广阔无限,在东方与西方、创新与传统之间,乌仁娜已经寻找出既跨越地域又别具一格的奇妙音乐空间。
一位俄罗斯的乐评人将她和图瓦的珊蔻(Sainkho)并列为两位“亚洲歌后”(Two Asian Divas);捷克的乐评人PetrDoruzka曾这样形容她的歌声:“就像是在沙漠里观赏即将绽放的花朵,或是发现一个别人还没发现的美女,或是在原野中看到瞪羚纵身一跃,却不知它将落在多远的地方。”2003年夏,乌仁娜因为对欧洲世界音乐的贡献被德国授予RUTH最佳国际艺术家大奖
登上舞台的乌仁娜没有穿蒙古袍子,对于一个歌者来说,她的身躯真是瘦小。她的乐手也没有怀抱马头琴,舞台左手边是来自匈牙利的提琴手ZoltanLantos,右手边是来自法国的伊朗裔鼓手Chemirani父子,他们的手指舞动,敲击出陌生的节奏;弦子跳跃,提琴开始唱歌,乌仁娜随即吟诵蒙语的诗,然后,她开始唱了,干净的声音像是草原上的飞鸟,时而在野花上歇脚,时而在天空上飞翔,飞到目力不及的最高远处,又贴近地面带着疾风。很少有歌手,能在温柔处如此温柔,在暴烈处如此暴烈,就像是草原上的黄鹂和骏马
这场演出的名字叫做《生命:Amilal》
美丽的原声
对于这个出生在鄂尔多斯,在草原、沙丘和羊群之间学会歌唱的蒙古族女子来说,她的歌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生命”,她只出版过四张专辑,分别是《TalNutag》(1995,意为蒙古草原之歌),《H?d??d》(1999,中译《蓝色草原)》,《Jamar》(2000,中译《在路上》),《Amilal》(2005,中译《生命》)。四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创作歌曲,无一不以草原作为母题
从发声方法上,乌仁娜与我们习惯的美声化的蒙古族民歌很不同。她更尖利,也更不驯服。但如果与上世纪60年代民族音乐学者在田野采集的蒙古族民歌录音做对比,会发现她的发声方法与这些原始录音非常相似。事实上乌仁娜所有歌唱学习都来自外祖母和父母亲。她常常说“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我们学会说话就学会唱歌”,“在蒙古,唱歌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学来的。人们总先聚着喝茶,过会儿再喝点酒,就开始唱起来了。当我到欧洲时感觉非常怪异,我所能看到的都是讲话的人”。她说自己从不练歌,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因为歌唱就是生活本身
乌仁娜对于传统文化有一种高度自觉,这大概得益于19年的草原生活,也与她在异文化中感受的强烈冲击无不相关。她离开草原的契机源于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扬琴的教授,在跟随他习艺之后,乌仁娜在几乎完全不会说汉语的情况下登上去上海的火车,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与对于“说”的羞赧相比,她对于“听”有一种迷恋,她说:“我去听提琴的考试,去听钢琴的考试,去看篮球比赛,我什么都听,朋友们都说,乌仁娜,你是个疯子。”从“听”中,她学会了很多,甚至从“不好”的音乐中比从“好”的音乐中学习更容易

正是在上海,她发现了许多具有“纯真嗓音”的同学们,在程式化的学院派训练之下,都用同样的方法歌唱,只是语言不同而已,“这真是一种羞耻啊。”
毕业后她曾在内蒙管弦乐团担任扬琴手,不久辞职来到北京,与德国巴伐利亚筝的演奏者RobertZollitsch组成“高山流水”乐团,在一些酒吧演奏。就是在流浪的巡演生涯里,乌仁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歌唱了,原本她神奇的嗓音是局限在好友范围内的机密。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人又那么安静,谁会想到她能在歌唱时的震撼呢?
独特的演绎
在1994年移居德国之后,她差不多每年都会回一次鄂尔多斯。1997年她曾在那里进行过一次传统民歌的搜集工作,这工作现在看来是具有标志性的,此后掌握传统民歌的老歌者纷纷凋零,“歌的海洋”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所有的创作都植根于传统民歌,乌仁娜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传统艺术传承者”,从一开始,她的歌唱就是更自由与现代的,她所有的专辑都是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家合作,赋予了蒙古歌谣一种超出想象的可能性
她先后合作过的乐手除了Robert Zollitsch,还包括现在欧洲声誉极高的笙演奏家吴巍,来自印度的打击乐手RameshShotham,马头琴演奏家张全胜等。在乌仁娜的前三张专辑中,改编传统音乐的歌曲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即便是那些传统民歌,譬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这首广泛流传于蒙古的著名长调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在乌仁娜的版本里(收入《Jamar》),同样使用了马头琴,但她的演唱仍然是独特的,内向而轻柔,音句末梢处像消失的云朵,有一种冥想的性质。我总认为她是把声音作为一种多变的乐器—是的,她的音域跨越四个八度,允许她与伴奏者促膝低语或者热烈交谈,有一种高度的和谐与即兴,甚至器乐并不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们有时会走向前台成为主角
自由的歌唱
在第四张专辑《Amilal》里,乌仁娜组成现在的乐队:ZoltanLantos在布达佩斯获得提琴演奏的学位之后,曾有9年的时间在印度学习传统音乐的经历;DjamchidChemirani被称作“伊朗鼓王”,这位现年67岁的宗师出生于德黑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移居法国。他与两个儿子组成的Chemirani三人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法国当代音乐的面貌。单从履历表上看这个组合都是富有想象力的
不无巧合,他们与乌仁娜一样都有着跨越不同文化的背景,音乐的即兴程度很高,都将传统的音乐推向超越传统范式的层面。在这张专辑中,仅有两首传统改编的歌曲,乌仁娜的演唱与创作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更有智慧”了;或者是,她的歌声更为自由
整张专辑听上去并不那么“蒙古”,因为鄂尔多斯歌谣传统上较少使用诺古拉(颤音),乌仁娜少量使用的诺古拉并不算精彩,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倒是她的呼吸。在《生命》演唱会上,她用一首《献礼》为我们示范了一个神奇的节奏,11拍、11拍、12拍、4拍……这个既不整齐也不规律的节拍是乌仁娜歌声的众多秘密之一。“有很多音乐家总是数不好我的节拍,我有时候会说没关系你走你的节拍,我走我的,我可能会绕一下路,但我还会回来的。”她用手比划着,就像是为了看风景故意多走了一程路,她说自己并不特别在意节奏,她的节奏来源于“脉搏”
相信这些秘密和乌仁娜所有智慧一样,就来源于蒙古音乐的传统。就像蒙语本身的吐字发音赋予音节神奇的蜷曲与起伏;蒙族音乐强烈的旋律感让乌仁娜的歌曲从来都不缺乏优美。在海外“游牧”多年,她依旧保留着从大自然和朴实生活习来的特质,她说父母从小就教她“我的孩子,你不要怕与别人分享”。她说蒙古人不会教小孩子做什么,小孩子从小伏在父母背上,看父母做事,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她说姥姥曾跟她说,要想很大声地唱歌,必须学会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唱歌……但从没有一个蒙古人,在被传统充分滋养之后,在音乐的旅途上依然能走得那么远,为她的听众开辟出一个那么广阔的听觉世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