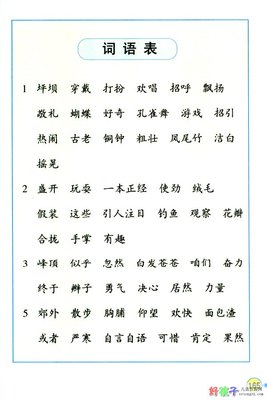这个字读(niang),我们老家都这样叫,该是“婶婶”的意思,泛指。
上次我回老家给苹果撕纸袋子的时候,嬢嬢正在我家地里忙活,她在打短工,按天计费。
很多年没有和乡亲这么近距离接触了,我多少还是有些拘谨,她手把手教我如何利索地撕掉纸袋而不碰落苹果。但我仍然碰落了很多果子,她便说:“随便碰呗,反正是生产队的,瞎帐!”就这一句,我立刻明白她还是将我看做自家丫头,她还是我的嬢嬢。
这个嬢嬢她从小在山间长大,喝山泉水,那里的山泉并没有将她滋润得像山花一样烂漫,而给她的是氟骨病,这也是我猜测的,因为在老家这个问题是忌讳谈论的。一瘸一拐的嬢嬢嫁给了村里同样喝山泉长大,一瘸一拐的远方堂叔乃鱼。小时候我很害怕这个嬢嬢,因为她的笑容和她的身材一样看起来总有些扭曲,但她总是很喜欢我的,每当看到我总是面带扭曲的笑容叫我的小名。
听母亲讲,当年她是新娘子,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挖玉米杆。结果她站在地理把包谷杆当甘蔗嚼。队长发现了,批评她:“乃鱼家的,你怎么站在地理嚼玉米杆呢?”她笑嘻嘻地回答:“你要是嫌我站着嚼那我就坐下嚼吧。”就这一句名声大振。
嬢嬢的大女儿好像和我同岁,叫“娟娟”,悲哀的是娟娟遗传了父母的矮小和扭曲,她总是一脸谦卑的笑容,她的残疾是大家取笑的资本,无良是一种病,它能传染。我们那一拨的孩子好像都欺侮过她,当然也包括我。成人后我很惊讶我 竟然做过那种可耻的事,内心常感内疚自责,看到娟娟便主动示好,她便也很喜欢我。
嬢嬢的二女儿将父母身上所有的潜能都展示了出来,如杨柳般婀娜高挑,聪慧能干。二十岁上出落得像出水芙蓉,突然得了脑瘤,亲戚朋友倾尽所有财力将她送到省里最好的医院,可是她连手术台都没有下来。
紧接着正值壮年像牛一样结实的乃鱼叔突然脑溢血一头栽到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年春节前我回老家,大年三十大雪纷飞,街道上到处是热热闹闹的节日气象,我看到人群里嬢嬢的小儿子建峰正在埋头给大家写春联,好像一副五毛钱。我很惊讶这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孩子竟然写这么好的一手毛笔字,写春联的有几处,但是建峰的生意最好,也许人们因为同情,因为敬佩。他一直埋头在写,我看见那握笔的手又红又肿,有冻疮。他的鼻涕拉得很长,马上要落到春联上时,他便跐溜吸一鼻子。这个孩子也最终辍学,小小年纪就出门打工了。
我们村我这一拨的十几个孩子中,辍学的有好几个,其中包括考上大学最终放弃的。考学出来却因各种意外,事故死去的也有三四个。所以我这么衣着光鲜地活着是一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情,回老家我总是操小道,也不喜欢出门上街,怕叔叔嬢嬢们看到我触动内心的伤痛。如今在自家地里和嬢嬢这么搭伴干活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便小心地找话题:“娟娟还好吧?”
嬢嬢倒是坦然:“唉,可怜着呢,你知道娟娟人老实,嫁出去也没生个一男半女,这么多年了,婆家人看不起,女婿没给买过一件衣服,像叫花子一样。”
“没有看过病吗?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人家婆家不让看,就说怪娟娟。”
“建峰呢?”
——“在南方打工呢,媳妇和娃在家,我给帮忙看着。”
......
很久沉默后,嬢嬢问我:“你婆婆家老家是什么地方?”
我说:“山西”
她感叹:“你妈也是的,怎么把你嫁那么远呢?想看你一趟多艰难啊!”
我不想同她解释什么是祖籍,便也随着她感叹:“是啊,是太远了。”每个牵挂女儿的母亲都该有痛楚吧。
嬢嬢干活认真卖力,因为她按天计费,大概下午五点母亲便催她回家,她还是坚持干了一会儿才走。看着她的背影,我很伤感,那一天正好是中秋节,我对母亲讲:“我去拿一盒月饼给嬢嬢顺便让她拿回家吧。”
“不可!”母亲立刻制止我:“你嬢嬢是个硬气的人,你这样让她捎回家她绝对不会接的,你要有心,等咱们干完了,你自己正式给她送过去。”
嬢嬢的身影在我眼里一瘸一拐地走远了,写下这些时,她好像又一瘸一拐向我走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