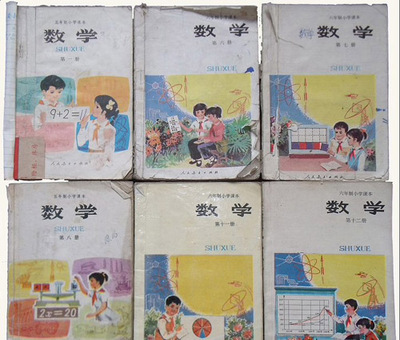谭心休
谭心休,字介人,号毅君,宝庆府城(今邵阳市)人。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弱冠入庠,旋食廪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举人。二十九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习法政。三十一年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冬归至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后至长沙,主持邵阳驻省中学堂校务,并为上海中国公学筹款。三十二年夏,与禹之谟、陈家鼎等率领学生万馀人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于岳麓山。同年秋,禹之谟系狱靖州,他也被宝庆府署派兵缉捕,乘间得脱,走广西,转赴上海,编辑《竞业旬报》和维持中国公学。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前夕,谭心休密返长沙,与焦达峰、陈作新联络。长沙光复后,被继任都督谭延闿简派为宝靖招抚使,率省标兵1营前往宝庆。途经湘乡青树坪时,在贺金声就义处凭吊立碑。及抵宝庆,又招募新兵和改编防营,合计有兵力5营,接收地方政权,清除匪患。还在邵阳西门外仙人井,为烈士刘大鹏建立纪念碑。
民国元年(1912)5月,谭心休卸职赴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4年(1915)冬,以上海国民党代表身份,经越南河内秘密抵昆明,与蔡锷共商讨袁事宜。5年(1916),自沪返长沙,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当选为参议院议员。6年(1917),适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即图南下,未及行,而中风病发,逝于长沙。
( 转自 http://www.changshalib.cn/was5/web/detail?channelid=239062&record=283)
蔡锷:“二次革命”时的选择
作者:李继锋文章来源:民国春秋网
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这里本来远离政争的漩涡。
1913年6月,云南都督蔡锷在五华山都督府内,会晤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国民党信使谭心休。这次会晤让他必须面临重大的抉择。
奉国民党领袖黄兴之命,谭心休的此行的任务是约请蔡锷在西南起兵,和国民党人联合讨伐日趋独裁的袁世凯。他给蔡锷带来了黄兴亲笔书写的《为蔡锷书联》:“松坡我兄正之: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民国二年夏六月,黄兴书于申江”。对这位既非国民党员、又非北洋派的老朋友蔡锷,黄兴想用两人之间深厚的情感来打动他。
蔡锷与黄兴的相识于1902年。因为是同乡,来往比较多。蔡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黄兴在上海被捕的时候,他还救援过他。对蔡锷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学界一直有争论。辛亥革命前,黄兴曾经对在广西活动的同盟会员林虎说,蔡锷是我们的同志,但没有说他是同盟会员。蔡锷的老部下朱德明确说蔡锷不是同盟会员。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经组织统一共和党,后来合并到国民党里面。当时云南国民党人要推他为云南国民党支部长,但蔡锷说自己已经提倡不党主义,没有参加。云南国民党由李根源为支部长。除了在云南国民党支部成立的时候,题了“大狮子吼”几个字之外,完全不参与国民党的活动。对党争,那时他不仅看不惯,还很厌恶。
蔡锷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之间的争斗中左右为难。他在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影响力使得他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蔡锷是个职业军人,他是主张国家至上以,加强中央权力、以便于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对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对党派的政治斗争,他都没有什么兴趣。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
对黄兴来说,更不利的是蔡锷特别尊敬的老师梁启超站在袁世凯一边,作为进步党的领袖,对抗国民党。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篇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愕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到长沙岳麓山下,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愕深得老师的喜爱。
梁启超只教了蔡锷两个多月,因为在长沙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从而结束了在时务学堂的教学生活。但对蔡锷的影响却是终生的,他从此开始用新思维学问来思考。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师徒流亡日本。蔡锷等未能进两湖学堂,执意要踏上漫漫长路去寻找梁启超。这让梁启超深受感动。他自己亡命日本,处境因难,不名一钱,但还是想办法请唐才常资助了一点旅费,让蔡锷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一起东渡到了日本。到康、梁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师生们在患难中重新相聚。
流亡日本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后来,梁肩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中回忆说:“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唾,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大隈重信的帮助下,让蔡锷进人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六年,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蔡锷对自己的老师推崇备至,从湖南时务学堂到自立军起义,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一直到护国反袁,蔡愕都是梁启超的忠实门生,当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时依然执弟子礼甚恭。
1912年6月6日,已经当上云南都督的他专门致电袁世凯等,详细列举了梁启超的贡献(在办报、办学、组织社团,宣传爱国、平等、自由、民权等诸方面的巨大贡献,评价道:“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他请求袁世凯邀请梁启超回国,并给予优待。10月在梁启超回国后,他致电袁世凯一方面欢迎老师,一方面“以谢大总统为国求贤之盛怀”。还致电各省都督请他们都致电欢迎,可见他对这位恩师 的热情。
而梁启超对蔡锷异常倚重,曾推荐蔡锷为国务总理候选人。1913年的6月中旬,梁启超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但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显得蔡锷并无争做国家最高政治领袖的勃勃野心。他当时感兴趣的是湖南都督或者京城的带兵官,可以为国家训练国防军。
在1913年国民党内激进派主张与袁世凯决裂之际,蔡锷并不为所动。就是好友黄兴的感情牌当时也不足以让蔡锷松口,
他对使者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
谭心休警告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冷笑说:“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心休大吃一惊,逼问蔡锷为什么这么说。蔡锷严肃的回答道:“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
谭心休听到这段话,知道蔡锷此时已经不会出手反袁,气得拂袖而去,将这不利的消息面报黄兴。
蔡锷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一贯立场,其中关键理念之一是坚持军人不党主义,保持军人在政治上的中立。在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蔡锷曾组织过统一共和党,他被推为总理,但不久见政党之间党争过于激热,而且诱发入党的军人干政,便提出军人不党主义。统一党合并为国民党之后,他就脱离了党。梁启超在北京好不容易把共和、统—、民主三党拢在一起,组成了—个进步党,利国民党对抗。但进步党内派系林立,很难团结一致,梁很想蔡到北京来帮自己一把。所以,他不顾蔡的不党主义,硬拉他在进步党当了个名誉理事。但他并没有多参加党务的活动。
一个月之后,曾经在云南任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宣告爆发,黄兴不久到南京举兵反袁。在国民党和北洋系双方彻底摊派的时候,蔡锷作出了什么样的举动?
蔡锷宣言反对国民党讨袁的举动,并筹划组织了黔蜀滇三省联军。
雷飙,蔡锷的同乡,自从1905年蔡锷任湖南武备、兵目两校教官起,一直跟在蔡锷身边,关系非同一般。他回忆“二次革命”时,称蔡锷组织三省联军是想占据武汉,伺机支持黄兴。当得知黄兴等很快战败,他不禁痛哭。还有记载说蔡锷“拟出师三镇,以为官军声援”。二次革命末期,他还派兵人川,镇压熊克武讨袁军。但大量的史料证明,“二次革命”蔡锷更同情袁世凯,认为不要对新生的袁世凯主政的中央政权过于苛刻,而不欣赏国民党当时的所作所为。但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双方的战争,而且因为他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传统情谊,选择时应该是很矛盾纠结的。
现在来看,“二次革命”不免操之过急,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反袁独立的省份很快失败了。
原文 http://img.mg1912.com/news/2011/10/13/5d670bb93259eaf40132faca8560016e.html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