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秋的傍晚,细雨蒙蒙,长街上只有几个撑着伞或冒着雨匆匆而过的路人,以及一个一手挎着竹篮,另一手捧着洁白花束的小丫头。 大概七八岁的年纪,梳一双喜庆的招财童子发髻,一袭春衫单薄,握着花束的手指在风雨中冻得苍白,越发显得孤弱伶仃,然而脸上却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倨傲表情。 竹篮里发出轻微的响动,她熟练地掩开一缕狭小的缝隙,伸出食指轻轻地碰了碰里面的东西,仿佛在安慰一只乖巧的宠物,脸上露出一抹宠溺的笑。这时,远处有嘚嘚的马蹄声渐渐近了,看样子是个富贵的人家,华丽的马车上坐着两个衣冠楚楚的车夫,就连马儿的颈圈上也裹着烫金压线的布绸,气势逼人。 马车驶得很快,车轮滚过积累了一夜的泥坑时都会飞溅起黑色的泥浆,染污了来不及躲避的路人的衣裳。旁人都避之不及,因此谁也没有注意那个瘦小的丫头究竟是何时出现在马车的前方,只有半步之遥的距离。 只听见鬃毛马儿猛地立起两只前蹄,发出一声惊吓的嘶鸣。两个车夫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有些苍白,稳定了心神,才定睛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不要命的野丫头。 “快滚,快滚,撞死你事小,弄脏了我们家小少爷回家的路,哼,事可就大了!”其中穿青衣墨衫的车夫满不耐烦地嘟嚷道。 “今天的花很新鲜,爷,买一束好吗?”声线细柔,充满了童稚。那丫头似乎对自己刚才所处的险境全然不知,也对此刻车夫的威胁丝毫不怯。 见这丫头竟不知趣,车夫懒得跟她啰嗦,扬起一鞭重重地抽打在马儿的背上,企图使它从女孩的身上践踏过去。正当周围的路人和闻声探出脑袋来看热闹的街坊都在心里紧紧捏了一把汗时,那挨了一鞭的马儿除了发出无奈的低吼,却根本没有往前移动一步。 “找死!”其中一个车夫终于按耐不住,握紧了手里的马鞭,侧身跳了下去。女孩也不躲闪,倨傲的脸上闪烁着一对晶莹透亮却深不见底的眸子。 “住手!”声音是从马车里传来的,掀起帘子的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仅从手腕上的那只白玉镯子就能看出这小少年的身份显赫。 一张干净白皙的脸,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走出来的,他披着深色的兔毛披风,里面是红白相间烫金竹节的缎袍,嘴角浮起一丝愧疚的笑。他被车夫搀扶着下了马车,定睛看着眼前在细雨中纤细却执拗的女孩。 “没事吧。” 但事实上方才车夫的鞭子已经伤到了她,车夫来不及收回的力扫过她的嘴角和手中的两朵残花。少女的肌肤吹弹可破,此刻已经溢出寸长的血痕,在雨中轻轻晕开。 少年掏出怀里的一方洁白的丝帕递给她,眼睛里都是愧意。“我让他们赔你花,好不好?” “哼,你赔得起吗?”女孩夺过手帕随意地擦拭了嘴角,依旧不甘示弱的样子。 其实就算他是涉世未深的大少爷,却也看得出女孩手中的花并不名贵,甚至普遍至极。但莫名地不忍心拆穿,他轻轻地笑道:“那你说,怎么办?” 仿佛就等着少年说这句话,女孩精灵古怪地眨眨眼睛:“除非,你借我一点东西。” 少年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她捏着手放进了那一只竹篮里。片刻间一种锥心的痛贯穿了少年的全身,他下意识地抽出手,只见一点细小的伤口,殷红的血珠霎时凝固。 那一年,他也不过九岁。 后来每当想起初见女孩时的情景,他都会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手指。虽然不知道竹篮里吸食人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他却格外庆幸自己回来的路上就嘱咐车夫们告诉祖母路上一切都顺利。否则作为堂堂南宫家的祖母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她宝贝孙子的人。 自从南宫家唯一的儿子半年前病死之后,祖母南宫颜氏就竭尽全力寻找唯一的遗腹子,也就是南宫家流落在外的小少爷南宫碧。 但其实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冷冰冰的名字,更不喜欢那个整天逼迫他读书练字作画的祖母。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对着南宫府后的莲花池发呆,想着那如莲花一般外表粉嫩内心却倨傲的小女孩。 尽管市井传言纷纷,说是她娘亲已经疯癫成狂,无药可医。但他猜想她的娘亲一定是个用情至深的女子,如此才会给自己的女儿取名思君。 思君。 暮暮与朝朝。
除却跟祖母一起被众人簇拥着去山上的寺庙里焚香,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出门。 拥有着庞大家世背景家规森严的南宫府,请的厨子和教书先生都可谓是人中龙凤。但每当他为先生的才学所折服的时候,祖母总会用那双阅尽人事的眸子不屑地扫过他那张惊喜的脸,冷冷地笑道:“这些人算什么,都比不过你父亲当年的万分之一。” 其实这两年他也从下人的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他那未曾谋面的父亲的事,比如他自小就被祖母宠溺着长大,天资聪颖,极具慧根,七岁便已将诗词歌赋玩弄于指尖,十一岁时精通琴棋书画,以才学出众而扬名天下。 然而之后的事情,众人却只用一句天妒英才轻描淡写地带过。 也许是天性敏感,他从进入南宫府的第一天就已经感觉到,祖母用那双因哭泣而变得格外清明的眼睛看着他时,喜悦之外还流露出一丝嫌隙。 他自知不如父亲,无论是品貌还是天资。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的身份。若不是父亲早故,除他之外再无子嗣,祖母是断然不会派人从千里之外的一名青楼女子手中将他带回来,一夕之间,便如鲤鱼跃上龙门。 如果说当初别人看着父亲的眼睛都是充满敬畏和崇拜的欣赏,那么如今他从别人眼里读到更多的却是歆羡和妒忌——无非是命好罢了。 莫名地,他总能从眼前对自己毕恭毕敬的下人们的眼神里读出这样的意味。 像是跟自己较劲似的,他拼命地读书练琴作画,但就算先生赞赏有加,祖母亦会冷冷地皱起眉头:“比不过先父的千分之一。”他是见过父亲的手笔的,惊艳得能用绝世之作来形容。那些花鸟鱼虫就像活的一样跃然在纸上,栩栩如生。 “少爷,祖母请你去花厅见客。”贴身的侍婢叶倾拎着灯笼站在书房门口,橙亮的光芒照着她明艳的双眸。 从进入南宫府的第一天,祖母就为他准备了几个贴身的侍婢,每个都是明眸皓齿的美人。其中就属叶倾最为耀眼,尤其这两年,她宛如花瓣上的一滴露水,越发晶莹剔透。 起初他并不能理解,觉得整天被一群丫鬟们伺候着怪不舒服的。可是这两年他才渐渐懂得祖母的用心。 十个才子九个风流,祖母也许将父亲曾流连于烟花之地视作南宫家的耻辱,如今便教他从小识得美艳的女子,不至于一朝迷恋,步父亲的后尘。 这么想着,又对叶倾生出了几分嫌隙来,于是他冷淡地应了一声,就径自向花厅走去。
去到花厅时却只看见祖母笑意未褪的眼角以及红木茶桌上一张红绸缎面的请帖。 心里更加奇怪,是谁这么大的面子,不过是来送一张请帖罢了,还需祖母亲自来迎。 “碧儿,你过来。” 也是凑近了才看清楚,那缎面的红绸上只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金池砚”三个字格外耀眼。原来是与南宫府齐名的金府,其祖上是战功显赫的将军,如今亦是财雄势大,上达天庭。而金池砚也是金家唯一的少爷,地位如他在南宫,不容小觑。 “三日后,便是他的生辰。碧儿,你与我同去。”祖母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孙儿的脸,仿佛是在欣赏一件即将在世人面前展览的珍宝似的。 仿佛是老天都来给金家少爷贺寿,天空格外晴朗。 爆竹声,莺歌舞,宝马香车花满路。 演奏的乐师是京城第一琴圣,舞池中央的少女亦来自最红的歌舞坊,酒桌上觥筹交错,热闹至极,溢彩阑珊。 祖母今个的气色格外好,一身暗红色织锦绒袄,胸口用金丝线绣了一朵俏丽的牡丹,领子上别出心裁地缀了孔雀翎羽,富贵雍容。来的人身份亦是不凡。但每个人看见她,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是初次出席这种场面的少年眼神还是稍稍有些怯弱,好在叶倾一直跟在身后提醒他该注意的礼节。 宾客都入了席却迟迟不见主人,祖母脸上是淡定的浅笑。饭桌上尽是些谄媚的嘴脸,他实在耐不住,便偷偷起身,将这满园的灯火都扔在了身后。远了珠光宝气,他才终于能深深地吸一口气。 一股奇异的幽香就在这时趁机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格外沁人心脾。 循香望去,只见假山溪水后面是一大片花圃,香气氤氲,流光如云。一名藕粉色长裙的少女正在给花儿浇水,动作轻柔得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 仿佛是被一根刺温柔地扎进心脏,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她。 “思君!” 当年倨傲的少女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她认出他时,眸子里也闪烁同样的惊喜。 中间相隔的几年好像不过是弹指间,他们都从彼此的目光中寻到了当年的模样。万语千言,缕缕情丝,都在那一念之间。 “公子,祖母正寻你呢。” 叶倾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背后,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 “知道了。”他有些不舍地收回目光,转身入席。 其实说起来,思君于他不过是一个有过一面之缘还有些“过节”的陌生女子。可是当她那张熟悉的脸再次出现,却叫他有些心猿意马,意兴阑珊起来。 尤其得知思君如今是金府中的花奴,他就越发对那个正从珠帘幔纱后面走出的男子有些好奇了。 但当金池砚真正出现在众人眼中时,他却忍不住吃了一惊。 他能想象得到金家的少爷必是人中之龙,眉若剑飞眼若星芒,但他却万万没想到,他竟坐在一把红木雕花的轮椅上,一双清凉的眸子看似有如冰雪般透明,但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察觉,他眼里的光是溃散的,毫无生气。 堂堂金府的少爷,名闻天下的如玉公子,竟然会是一个半身瘫痪且双目失明的弱冠少年。 他有些失态地凝望着前来拜见祖母的金池砚,虽说金池砚双目失明,却掩不住盈盈气质。反倒是他,回过神来时,只见祖母扫过一束冷光。 那日的道贺并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走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花圃的方向看了一眼,却已不见芳踪。 施施然,竟有些失落。
“你看金家少爷如何?” 祖母拨弄着指上的一枚珊瑚玉貌似漫不经心地问道。 “嗯?”他有些不明白祖母话里的意思,思绪也似乎还停留在那个花中的少女身上。 “混账!” 他未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脆生生的一响,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分不清是麻木还是疼痛。 祖母的表情瞬息间就变了:“你连那花厅壁上的画都没有留意?”她恨铁不成钢地骂道,“没用的东西!” 其实他当然是留意到了,花厅的一面石壁上画满了千万朵盛开的花朵,栩栩如生,从远处看仿佛是被柔风拂过,格外动人。只不过他没想到那壁画竟是出自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手。 “一个月后,就是江南一年一度的书画赛,我要你赢了他。” 祖母的眼睛里闪着别样的光彩,手掌轻轻地摩挲着他的脸。 这是第一次他在祖母面前除了谦卑还有惊恐,他强忍着脸上的疼痛,惴惴地答:“是。” 夜里叶倾为他上药,烛影摇红,她的动作格外轻柔。 但他看着镜中的自己,不知为何却有落泪的冲动——祖母下手很重,长长的指甲在他脸上划出一条细细的血痕。他的心突然变得冰冷而绝望,于是狠狠地拍掉了叶倾的手:“滚!” 仿佛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叶倾后退一步,从容地放好药,说:“其实公子不该恨祖母的,若不是她,您现在恐怕已经在饥荒中饿死了!” 这句话让他狠狠地打了个激灵,是啊,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怎会舍得亲生母亲,一个人来到这冰冷的深宅大院呢。那年的塞北正经历着大旱,饿殍无数,几乎到了吃人的地步。当祖母出现说要用黄金万两跟母亲交换的时候,他几乎是惊喜着答应的。 况且自从上次金府一行,他开始渐渐适应和体会南宫家少爷的身份所带来的荣耀,以及享受着那些锦衣贵人歆羡且恭敬的眼神。 习惯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他摸着脸上的血痕,仿佛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目光定格在手指上那一条小小的疤痕。
“思君。” 当少女熟悉的身影在江风翠柳中闪现,他的心便安了。 微红的脸,欲言又止的唇,温柔的眉眼,少女身上独有的香气萦绕在他的鼻尖。他只觉得全身酥麻,思绪飞扬在江风里,险些忘记此行的目的。 “你当年究竟养的什么小东西,咬得我疼了许久。”他故作委屈地伸出那半截手指。 “那个……是娘亲留给我的,叫做螟蛉。”她的眼睛调皮地眨了眨,撅着嘴问道,“疼了你多久呢?这么记仇。” “疼了很多年。”他温柔地答,不失时机地握住了她的手。 思君只稍稍挣扎了一下,就安分地被他牢牢握在手中。再甜蜜的情话也比不上一个笃定的眼神。 不过数日,他便从思君的口中得知了金池砚作画所用的笔墨纸砚,甚至他作画的习惯以及最精妙之处。“公子也想得到那幅‘鸳鸯楼’吗?”彼时思君在他怀中漾着水一般的眉眼,一袭藕色的烟裙映衬着碧色湖光。 “你也知道……鸳鸯楼?”他有点吃惊,有种被人识破心机的尴尬。 鸳鸯楼是一幅画圣谢铭留下的稀世绝作。据说里面画了一座楼,共有七七四十九层,其中有两扇窗里分别画着谢铭以及他此生最爱的女子。 这几日他暗地打听了很久,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名女子只有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金家已亡故的老夫人,另一个则是南宫颜氏。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祖母从小就培养他作画,真可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不过是工具罢了,什么骨血亲情,什么认祖归宗,都是幌子,都是借口。 “碧郎,不如我们一起离开?”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旦动了真情,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受半点委屈。但他又岂是当年任她摆布,以血喂虫的少年呢。 |
胭脂红泪 文/晚安月 刘文天 晚安北京下载
更多阅读

《男生女生》别册-权倾天下 文/咖啡杯里的茶 医妃权倾天下txt下载
1 “话说那苏广门,当年身为卫国大将军镇守这平阳重城。皇恩如此浩荡,他家男子皆为将相,女子不是入后宫便是嫁得朝中重臣之子。原本指着他为幽朝江山尽点绵力,哪知那人竟然在关键时刻不发一兵一卒,白手把这平阳让给了沧州人。这下可好,

贾樟柯电影周 站台影评 回望浪漫的过去ZT 站台贾樟柯电影下载
贾樟柯的电影象诗又象散文,所以情节和结构最是被人说松散杂乱。贾的电影和王家卫的有一些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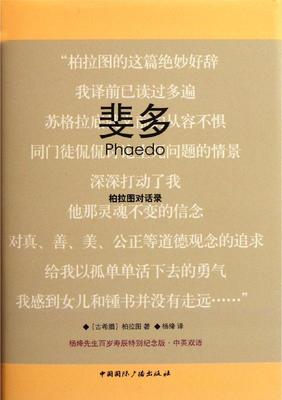
图穷对话录第9篇 “哈佛女孩”李菲雅 图穷对话录txt下载
案例提示: 李菲雅,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外语专业,毕业后被国家派往非洲从事石油贸易工作,两年多后回国,在一家著名的咨询公司从事贸易咨询工作。经过三年努力,1999年6月得到美国某大学半奖录龋她虔诚地捧着像救命符一样的录取通知,却
有机农业 成长的烦恼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4年07月14日 成长的烦恼英文版
很少有一个产业同时面对如此多的变化和问题。经过20余年发展,中国有机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该如何走向成熟? 王申福在北京密云县古北口镇北甸子村创办了乐活村农庄,以生产散养蛋鸡为主。据多年的经验,他认为市场上没有真正的有机鸡

视频 峰生水起精讀班 风水学29集 全 峰生水起精读班下载
48:01峰生水起精讀班面相篇29学习王28,16447:35峰生水起精讀班 风水学28学习王15,82747:1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