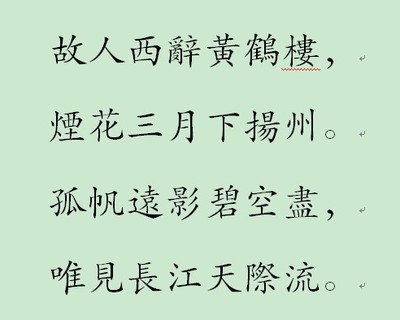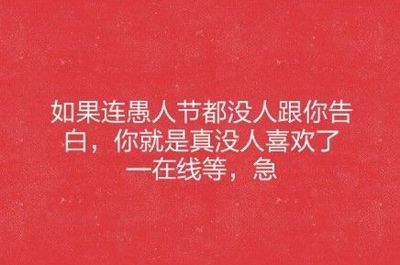只要被打碎,我就随风飞
——白连春
1、
二十年前,我在河南省寻找被人贩子拐走的妹妹三年,多次卖血。当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被告知卖血可以感染,我便生活在巨大不安中。我漂泊北京,经陈建功老师介绍,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生活稳定了,但是,我的内心,时常被这巨大的不安困扰,不敢和任何人交往过密,怕我万一,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再传染给别人,那会使我痛苦。
我很少参加活动,人多地方尽可能不去。领导关心我,要为我介绍女朋友,不得不,我向领导说谎。我说,我有了女朋友了。其实,我没有。
到底,我还是病了。千真万确,我感染了艾滋病毒,是艾滋病发病了。医生不让说,让我说我得了肺结核,严重点,肺癌。曾经两个人,一是某报记者,一是女诗人花语到医院,想弄清我究竟得了什么病,和医生吵闹,医生都没告诉。医生再三对我说,医院绝对会为你保密,至于你自己说出去了,后果自负。我无法预见我说出我得了艾滋病有什么后果。
现在,我病了快两年了。
我住院两个多月,我母亲来看我一次,她很忙,要侍候庄稼,要给我二弟带孩子,要给我二弟喂猪,十一头,我父亲一次也没来看我,他哮喘,天天坐茶馆。
全国各地的文友知道我病了,给我捐款,有十二万。世中人从北京来到四川,把钱送到我手里,我非常惶恐,我骗了大家,对于我得什么病,我没说实话。
2
我在河南省寻找的被人贩子拐走的妹妹,不是我亲妹妹。我没亲妹妹。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子,我是老大。
九岁那年,我在长江边半山坡高粱地里捡到一个女婴。这女婴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妹妹。我把她捡回家第三天,她就被我的邻居,当时的队长老婆卖了。我找了她半年,没找到。队长老婆给我说的是相反方向的一个地点。三十多年后,当我和这个妹妹重逢,才知道她被卖的细节:队长老婆得了二十块钱,并不是如她说的五块。
我生命中第二个妹妹是我认的。那年,我二十岁,我本当兵,所在的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汽车连全连解散,我回到家乡,开始农忙在家务农农闲外出打工。那时,打工这个词还没出现。我怎样认的这个妹妹,又怎样在河南省寻找她整整三年,终于把她找到,这些细节在我最近写的小说《河南省》里有仔细叙述。在这篇短文里,我不多说。在此,我只是说出:有一个河南省老大爷陪着我找我妹妹。这老大爷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父亲。他陪了我三年,直到我找到我妹妹。当然,也是在他带动下,我开始了卖血。
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生活稳定下来,一天,我收到一封河南省寄来的信。是以前,那个陪我找我妹妹的老大爷的老伴托人写的。看着信,我泪流满面。原来,老大爷得了艾滋病,要死了,想见我一面。我立刻赶去。我看到瘦得只剩下骨头并且浑身都烂了的老大爷。他努力向我伸来右手,没力,无法够着我。我赶紧捧住他右手。我俯下身抱住他,哭了。泪水,全部,滴落到他脸上。
我要死了。
不。
我担心你。
不。
我怕我害了你。
不。
除了说不,我不知该说什么。我抱着他,把脸贴到他脸上。我一直守在他身边。当天深夜,他死在我怀里。我把他埋了才回的北京。
我消失一个星期。领导对我非常不满,因为我没请假,手机也不开,领导有事找不到我。领导批评了我,然后问:是不是你女朋友出事了?
我赶紧说是。
3
我生命中第一个父亲是死人。在我生的那一刻,他死。那年,他六十五岁,没结婚,他是我家乡最著名的石匠,因为看电影被活生生踩死。活着时,晚上有月亮,他都在长江边和月亮一起喝酒。他不认识字,却专给死人打碑。
我出生于一九六五年正月初二,实际上,是初一晚上。这天晚上,长江岸边,山下工厂生活区的广场放电影。
我出生那一刻,我父亲不在家,他守在广场外等着看电影。那时娱乐很少,农民娱乐更少。全国各地都放露天电影。很多山上农民来到山下,像我父亲一样守在广场外,等着看电影。电影早就开始,已经放完一部。因为春节,大年初一,三部连放。电影是工人放的,放给工人看。农民只能守在广场外,等着有好心的工人把广场的门打开,让他们进去看一会儿。没好心的工人来打开广场的门,农民就一直守在外面,听电影,或,爬到围墙上看。能爬上工人修的围墙的农民没几个。所以大多数农民只能听电影。这天晚上,农民很幸运,有一个好心的工人把广场的门打开了。守在广场外的农民立刻一起朝广场里挤。就这样,和我父亲一起等着看电影的柳富云,被活生生踩死。同一时间,我在山上出生。
我出生第一个晚上,准确说,是我出生第一个早上,我父亲看完电影回家,看见我很惊讶,甚至可以形容成很惊恐。他担心我:是不是刚被踩死的柳富云投的胎?不等天亮,他就找了瞎子给我算命。瞎子先问了我父亲我的出生情况,然后,瞎子说我命重二两九钱,是柳富云投的胎,要克父,我一天天长大会把父亲一天天克死。
我父亲听了很害怕。他又找了第二个瞎子给我算命。第二个瞎子仍说我命重二两九钱,是柳富云投的胎,要克父,我一天天长大会一天天把父亲克死。
我父亲不信。其实,我父亲信。为了证实,他又找了第三个瞎子。那时瞎子真多。真要好好感谢瞎子,如果没瞎子,我就不会如此顺利成长为今天的白连春。那一天,我父亲一连找了五个瞎子,五个瞎子都说了大致相同的话。
我父亲害怕极了。柳富云被活生生踩死的情景,他亲眼所见。我父亲不能想象,无法想象,一点没办法不想象,那个他看见的活生生被踩死的人,投胎成了他儿子。我父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到了我出生第三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偷偷抱着我,把我扔在了长江岸边半山坡一块红苕地和一块白菜地中间的小路上的一窝草里。
我被祖母抱回家,父亲见祖母抱回我,当即和祖母分家,带着母亲搬到和我家隔着五座山的一座山上,重新修了房。
有记忆起,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六十五岁没结婚的石匠投的胎。从小,周围的人都叫我二两九,都知道我要克死我父亲。
晚上,我都躲在被窝里流泪。每天,差不多我都在被祖母惩罚和被别的大人孩子欺负中渡过。别的大人孩子欺负我,我可以接受,他们是外人。祖母惩罚我,我更可以接受,她是我唯一亲人。祖母惩罚我花样很多:打我;要我跪;不准我吃饭,而且要我跪在一边看着她吃,她甚至还要我头上顶着一块碎瓦;即使冬夜,她也把门插上,不准我进屋。她骂我更是家常便饭。她经常骂我:捡的娃儿任脚踢,你是我捡的娃儿,我想咋你就咋你,我打死你也没人管。
为什么我祖母这样对我?因为我祖父不爱她,我祖父在泸州城工作,一直住在泸州城,每月只回沙湾乡下一次,给她一点钱。还因为我父亲恨她,我祖母只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父亲,我父亲八岁那年,泸州城解放,一天,我祖母带着我父亲进泸州城去看望我祖父,由于人太多,结果,我亲爱的祖母把她唯一的孩子丢了。十二年后,我父亲二十岁,找了回来。他吃了很多苦,所以,恨他母亲,他坚持:她是故意丢的他。他对她的恨时刻表达出来。他哪里知道:当初,他丢了,他母亲差不多疯了。
我祖母基本是半疯的人。她把她对祖父和父亲的复杂感情:有时爱,有时恨,有时又爱又恨,更多时是不知该爱还是该恨,全部,发泄到我身上。小小的我,没任何抵抗能力的我,成了她可以抓到手的唯一出气筒。
在我上学前,坟地的坟,每座,我都熟悉了,因为每天我都在坟地割草,猪草背回家给祖母喂猪,牛草背到生产队挣工分。我只能在坟地割草,我不敢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孩子们要骂我,打我,抢我的草。我是一个在坟地长大的孩子。
每座坟都长满草,一年四季,绿油油的。还有不少开花的坟。开花的坟,我想,肯定是女的。有些坟有碑,更多的坟没。有碑的,碑上的字,差不多,我都会写了。开始,我不会写字,就拿手摸着字在碑上写。我就是这样练习写字的。我知道,中间三个字是死人的名字,更知道,那些死人的名字,都是投胎成我的柳富云打的。就是说,我知道,坟地的碑、碑上的字,都和我有密切联系。
七岁那年,用我在工厂生活区捡破烂卖的钱,我终于和其他孩子一样上了学。我学会了认字:汉字。我上学的学校不是正规小学,民办的,老师没教拼音,我至今不会拼音。
当我学会认字,我就开始在坟地大声读死人的名字。我读过无数死人的名字。我把他们牢牢记在了心里。
我记得最深刻最真切的一个死人的名字就是,只是,柳富云,因为在长江岸边这一带人人都传说是他投胎成为的我,于是,在我心灵最隐秘的角落,他是我,同时,他更是我父亲。在我还不会读字不会写字时,我就已经把他认做父亲。我认一个死人做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我的活人父亲不要我,怕我克死他,那么,一个死人父亲,应该不会怕我克死他,因为他已经是死人。不知从哪天开始,我直接喊坟里的死人柳富云爸爸了。迄今为止,除了死人柳富云,我没喊过任何人爸爸。
爸爸,婆又不准我吃饭了,她要我跪着,看她喝酒和吃饭。
爸爸,那些娃儿又打我了,我痛。
每次,我这样给他说。说着,我抱住他。我想他也抱住我。我抓住他坟上的两窝草,把他在怀里抱紧了。
4
八岁那年,某天下午,我到山下工厂生活区捡破烂,在垃圾堆中翻找到半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那时我不知道我捡到的是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后来,我的生命已经和诗歌融为一体,才知道。我好幸运,开始读书,开始认识字,就读到了全世界最好最美最温暖最永恒的文字。
白天,很多活要做,没时间读书,我就晚上读,等祖母睡着了。我捡到半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时,正是夏天。夏天不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呆很久。我不敢在家里读,更不敢点煤油灯,怕祖母醒来,发现我不睡觉,点煤油灯读书,不因为浪费而骂我,打我,才怪。
家里不能读书,白天不能读书,我就晚上等祖母睡着后偷偷跑到坟地读书。夏夜,长江边的半山坡。周围紧紧包裹着我是无边无际的草。
即使有月亮,又有星星,凭月光和星光,要照亮书上的字也困难。我捡破烂捡了很多罐头瓶。我在坟地抓萤火虫儿,我把抓到的萤火虫儿全放进罐头瓶。一个罐头瓶装满了,不够亮,我就装三个甚至五个。反正空罐头瓶我有的是,反正坟地萤火虫儿有的是。就这样,我开始我秘密的读书生涯。
我在坟地读书,从来都在死人柳富云坟前。在我心里,死人柳富云不仅是我更是我父亲。我在他的坟和他坟前的碑间读书。小小的我背靠着他的坟头枕着他的坟,脚可以伸到他的碑。他的坟和他的碑正好构成我的椅子。我读累了,不知不觉睡着了,他的坟和他的碑就正好构成我的床。一个天和一个地都是我温暖的怀抱。
天冷了,坟地没萤火虫儿了,我就把我捡破烂卖的钱买了手电筒,我还会用我捡到的工厂扔的擦机器的油糊糊的布条和棉纱做成简单的火把,再大些,我还会用我捡到的工厂扔的电石,做成简易的电汽灯。我做煤油灯更不在话下。我会做各种各样的灯。
为了有书读,每天一早一晚,有时,中午那点时间,我都跑着,都到工厂生活区捡破烂。在山下,长江岸边,沙湾居民街和工厂生活区间,正好有一个供销社,设了废品收购点。我捡到破烂,随时可以卖,得了钱,就在供销社买书。那时供销社买书。供销社的书非常有限,很快,我就把供销社的书读完了。
为了有更多书读,八岁那年开始,我多次游泳横渡长江进入泸州城。以我一个农村孩子的聪明,我知道我亲爱的祖父,他虽无视祖母和我存在,但他仍是我祖父,对我,他孙子,有无法逃避的责任。找到祖父,我给祖父说我肚子痛,我抱着肚子在街上打滚,引来无数围观的人,逼得祖父不得不给我钱。有了钱,我立刻从街上爬起,跑到新华书店买书。后来,这种骗祖父钱的把戏要玩很久,祖父才肯给我,因为,他早知道我在骗他。
公啊我肚皮痛得很啊。
我抱着肚子,在街边翻滚。我就快从街边翻滚到街中央了。围观我的人,开始两个,三个,五个,渐渐,就围成挤不动的人圈了。
哪个的娃儿啊肚皮痛成这样,没大人管?有人忍不住了,问。
白老师的孙孙。知道的人回答。我亲爱的祖父虽是文盲,只会读自己的名字不会写,然而他在当时泸州城最好的单位百货站管着工地,泸州城的人,几乎都认识他,都尊称他为老师。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文盲比读书人吃得开。最简单的证明:那时不签名,兴盖私章。我祖父腰上有两枚私章和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穿在一起。这两枚私章都刻着我祖父名字,他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有了这两枚私章,泸州城,没一个人敢怀疑我祖父一个字都不会写。
娃儿的肚皮不痛,装的。进一步,有人说。
啊,为啥呢?
要钱。
娃儿要钱,装肚皮痛,在街上打滚,都这样了,大人就多少给娃儿一点钱呗。
娃儿这样好多回了。
娃儿要钱干啥?

买书。
买书是好事啊。
白老师不让,白老师说在沙湾,人人都说娃儿疯了。
为啥?
他天天晚上到坟地给死人读书。
噢!
围观我,本来对我有兴趣的人,听到这里吓住了,立刻,散开一些。我在地上,赶紧翻身坐起。我必须说话了,再不说话,就要不到钱了。
白天我要干活,没时间。
那你为啥要到坟地给死人读书呢?
家里我婆不准我读。
家里不能读书,仍有很多地方可以读书啊,比如河边的岩石上,还有在桂圆树林里,为啥一定要到坟地读书呢?
别的地方,那些大娃儿要打我,还要抢我书。
看起来,你就只能在坟地给死人读书了?
死人不怕我。
死人不怕你?那个对我非常有兴趣的人,吓了一跳。
我老汉听瞎子算命,说我要克死他,他怕我,我生下来第三天就把我丢在了河边,是我婆把我抱回家的,从此,我就和我婆是一家,我老汉和我妈还有弟弟,他们是一家。
噢。那个对我非常有兴趣的人,听到这里,噙起了泪水。
咋个会这样啊?他问。
他蹲下,向我伸来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
多好的娃儿啊,爱读书,我娃儿就不爱读书。这么说了,他站起身,接着说,白老师给你孙孙一点钱,让他去买书吧,你要是没钱,我就给了。
我有。我祖父说。
我只是不想让他读书读疯了。我祖父说。
读书读不疯。
很多人都疯了。
不是因为读书。
是。
好了,我不和你争,你不愿意给娃儿钱,我给。
我孙孙,为啥要你给?
我亲爱的祖父就把钱给我了。拿到钱,我从地上起身,飞一样,朝新华书店跑。
我在长江岸边成长的无数夜晚,读了什么书,我不一一举出。没必要。但,我,一个八岁孩子,在夜晚,在长江岸边山坡上的坟地,读书给死人听的情景,现在想来,依然让我无法说清:对自己,究竟怀着一种怎样的感情。
5
我祖母曾离家出走很多天,说是去亲戚家借粮。具体多少天,我无法说清。我饿得不行,进泸州城找祖父。祖父不在,去了外地,他在泸州市百货站工作,负责工地管理,哪里有工地就去哪里,泸州市下辖五县三区,边远地区紧挨着云南贵州。饿得没办法,我只好吃柳富云坟头的草和土,最终饿晕在小学教室。校长宋久荣的一碗面条救了我的命。
我祖母曾把我赶出家,原因是一天晚上,我把喝醉了睡在坟地的我父亲背回了家,我父亲醒来,把我家的锅、碗、桌子、板凳全砸烂了。我在同学杨昭龙家住了半年,杨昭龙家也很穷,不得不,我偷偷住进学校。这时,我读中学了。我写的一篇作文,把班主任物理老师写得太真实,他不准我做他学生,我只要进教室,他就用扫帚打我,把我打出教室。分文理科时,我不读文科,得罪了文科语文老师,他读不懂我写的诗,就在学校讲我是神经病。管寝室老师不让我住寝室,我没交钱,他每天晚上守在男生寝室外堵我。实在走投无路,一天早上,我跳进了长江,傍晚,才被人救起。
这年,我十五岁,被救后,我当兵离开四川省到了黑龙江省。我当兵的唯一目的,只是离开家乡。本来,我是考不上兵的。我身体差,很瘦,年龄又小,得知我不能当兵,我当场蹲在地上,抱头大哭。
我的哭,感动了一位接兵的首长。
十五岁到四十三岁,我基本上都在外:当兵,流浪,打工。中间几年我在家乡,从祖母摔断右腿开始。真是奇,我祖母摔断右腿时,我在河南省孟县,她摔断右腿那一刻,我头开始痛,回到她身边,就不痛了。我祖父七十二岁,已经离开泸州城回到沙湾乡下,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祖父在泸州城百货站工作六十多年,把单位分的房借给一个无房结婚的朋友儿子,没法收回。他太老了,百货站又不要他继续住工地,不得不,回到沙湾乡下,像我,即使在北京生活十年,最终,也不得不回到泸州。
我守在祖父祖母身边,他们先后去世,我把他们都安葬后,才离开。
6
我回来,我出生地所在长江岸边,要修长江大桥,柳富云的坟所在那片山坡首当其冲,成了忙碌的工地。我祖父祖母的坟也面临立刻搬迁。我父亲母亲和我二弟都不管。他们对我说,是你的公婆。我刚出院,身体异常虚弱,走路都无力。我出院不是因为病好了,是因为医生给我说:你出院吧,医院外安全些,医院里病毒多容易反复感染。我必须四处找人,找工人和道士,还要联系安葬地,张罗给祖父祖母迁坟。当祖父祖母的坟挖开,我抱着祖父的骨灰盒和祖母的骨头,泪如泉涌,很自然,我想到自己。某天,我死了,谁埋我?碰上迁坟,谁捧我的骨灰盒?城市一天天扩大,农村一天天缩小,我死了,埋在哪一棵草的根下?哪一棵草收留我的灵魂?
正是夏天,身上穿不住衣服,蚊子咬一口,我的身体,被咬处就会留下一个大包,然后一点一点,烂。当时,我不知道是蚁子咬的,我以为是我长了热毒疮,痒,痛,白天,坐卧不安,夜里无法入睡。控制不住要抠。越抠,越痒,越痛,越烂。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我的腿和手臂,还有脖子,到处都是烂的。
费尽千辛万苦,我总算把祖父祖母安置好了,但是,当地人天天给我打电话,要求我给钱。原来,我先给的几千块钱,被那个帮我联系安葬地的人吃了。
祖父祖母的坟再次安葬好,我花了一万多块钱。
本来在农村,我有房,不管好坏,总是有的,后来,我到了北京,被我二弟拆了。他为了自己修新楼房,拆了我的旧房。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说我的房自己塌了。不是,是我二弟拆了。
现在,国家占地,我一直在外,在我的出生地农村,我失去了户口,失去了房,得不到任何补偿。我二弟除了买自己的返还房外,还要买我父亲母亲的。我父亲母亲也让我二弟买,不让我买。
这期间,我出院后,暂住在同学杨昭龙家,天天上山帮我母亲侍候庄稼。我爱侍候庄稼。没办法。眼看土地要被占了,我和我母亲一样着急,想尽可能多侍候一天庄稼。
时间长了,我不能一直暂住在同学家,再加上,我心里清楚我这样的病,所以,我租了房。为省钱,我找了最差最便宜的房,一个月房租一百块钱。
就这样,我在我家乡长江边住了下来,继续我的生活。
7
我得艾滋病,还是有几个人知道了。一是我家乡领导。一是我堂兄白联洲。白联洲是法官,他比医生先告诉我我得了艾滋病。真不知他如何得的消息?
我没病,还在北京,白联洲要送一套房给我。这事是通过我家乡领导说的。我不认识白联洲,不知道我竟然有当法官的堂兄。听到这消息:在家乡,有人要送我房,我高兴得快疯了。具体说,是白联洲替某开发商搞了很成功的策划,开发商要送他房,他转送我,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和开发商僵了,开发商没送他,他就不能送我了。送的房没得到,白联洲对我好,我记住了。我病了回家乡,白联洲知道我的实情,没乱说,仍对我很好,组织白氏家族给我捐款。我出院回沙湾乡下后用着的小灵通是他给的。本来,他还要给我笔记电脑,我没要。我有电脑,台式的。我完全把他当亲人,而且,是唯一的。《星星》诗刊给我发辉煌30年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的奖,我要他代我去。他很乐意。他到处宣传:白连春 是白氏家族唯一文人。在我家乡,四川泸州,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人都知道他对我好。
我出院半年,悄悄回到北京,把在北京贷款买的房,最快速度,最低价,卖了。一些朋友:浙江张敏华、北京海城和冯连才、山东孙殿英,借给我钱,先后还了,还有两个朋友借给我钱,我没还。这两个朋友,一个是浙江张连文,一个是黑龙江刘长军,他们都表示不用还。我还是要还,只想缓一段时间。我共欠他们六千块钱。就这样,我卖房的钱,加上朋友们给我捐的钱,有三十万。我打算在四川省泸州市我的出生地买房住下来。我爱这土地,我虽得了艾滋病,注定活不长,心中仍有爱。
白联洲决定帮我买房。很快,他为我选好一处房,一百三十多平米,对我来说,太大。我一个人住,浪费。房价超出我预期很多。见我不想买他推荐的房,白联洲说,这房很好,不买可惜,要不这样,你不买,可不可以先把钱借出来,让另一个姓白的人买。他说另一个姓白的人也是我堂兄。我至今没见过。白联洲说他儿子要上初中了,这房挨着六中(我家乡泸州市最著名的中学),方便上学。他还说孩子我见过,在我的朗诵会上朗诵过我的诗。经白联洲这样说,我想起:几次朗诵会,他都领来一个男孩,男孩都朗诵了我的诗。白联洲说,等今后,我找好房就还钱,按银行同期利息算,保证不担误我买房。
我把钱借了。我的钱三十万借出去三个多月,借我钱的人还没给我写借条。这天,忍不住了,我给白联洲打电话,问,是不是给我写张借条?白联洲回答可以。我堂兄没来,他妻子来了。她写借条,把我的名字写成白莲春。我说写错了,要她重写。她重写了。我要她写如何还钱。她写上:一年1——2万。而且,她写下借钱人名字是她儿子:白肇野。
我不同意,立刻,给白联洲打电话:要求还钱。白联洲连声说好。自从我打了要求还钱的电话。白联洲给我的小灵通开着,就没接到电话,我再用小灵通给别人打,打不出去。原来,他把小灵通号消了。
我买了手机,用手机和白联洲联系,要求还钱,白联洲满口同意,要我说一个还钱时间,我说九月。九月,从我的钱借出去算起,整整五个月了。白联洲同意。九月过了。没人还我钱。我又给对方——借我钱的那孩子母亲——联系,对方说钱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那就十月十号上午九点,借我钱的那家银行还钱吧。十月十号,我到银行拿了号,等很久,对方才来,说,还不了,无法还。
我给白联洲打电话,说,不还钱,我只好告了。
告吧,白联洲说,是你的权利。
我有病,身体不能……
不要给我说这些!
我找了律师,律师说,借条上署的是小孩的名,白联洲没担保,不能起诉白联洲。我找了公安局,公安局说经济案件归法院管。白联洲是法官,而且,律师说了不能起诉白联洲,我怎么找法院?我找了家乡领导,白联洲就是这领导介绍我认识的,领导说,白联洲是你堂兄,我不好介入。没办法,我向朋友倾诉,朋友说,白联洲对你很好,中秋节,还朗诵了你的诗,向我们宣传你的诗《我和你加在一起》,在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上朗诵后,音乐人小柯谱成歌,由祈福女孩李姗殷作为“祈福中国,爱传百城”的主打歌演唱,还有可能入选亚运会。听朋友这样说,我不明白:公开,白联洲还对我如此好,实际上,他把给我的小灵通取消了至少两个月了。
我怎么办?我三十万块钱,就这样被我堂兄——法官白联洲——领来的小孩白肇野借走,无人归还了吗?
世界很大,我,白连春,一个卖血得了艾滋病的农民诗人很小,何处能让我渡过短暂的余生?人生很幸福,我,白连春,一个卖血得了艾滋病的农民诗人从未享受,可不可以让我继续用短暂的余生热爱?
8
我身体越来越差,钱被借走,让我吃不下睡不着,更没免疫力。我头痛,不得不,时常听歌,以此减少痛感。刀郎的歌《德令哈一夜》,是近段时间最感动我的。这篇短文题目,就出自这首歌中的两句。我做了简单改动。我肚子胀,从长江边捡了无数鹅卵石回来,每天都用鹅卵石压肚子,或,趴在鹅卵石上摇晃肚子。
现在,我知道我身上的烂处,是蚊子咬的了。知道是知道了,但是,我没办法不让自己不被蚊子咬。蚊子让我防不胜防。全世界最让我害怕的动物就是蚊子了。蚊子咬一口,就会留下很大一个包,痒,痛,这个包,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烂。
我不想活生生烂死,在我亲爱的家乡。
我不想一个卖血得了艾滋病的农民诗人,被一个法官如此对待,在我亲爱的祖国。
我,白连春,一个卖血得了艾滋病的农民诗人,身边没一个亲人,又被堂兄法官白联洲借走所有钱不还,注定活不长了。
多年前,我祖父在泸州市百货站工作一辈子,分得的房被借走,无力讨回,七十二岁,不得不,回到沙湾乡下,最终,郁闷而死。
现在,我得了艾滋病,我的三十万块钱——这钱,有文友捐的,有我打工挣的,有我卖房剩的,还有我借朋友的——全部,被我的堂兄法官白联洲借走,和我祖父一样,我无力讨回,然而,我不想像我祖父一样郁闷而死,我写这篇短文,不想得到同情和原谅,想得到帮助,想大家帮助我,为我讨回我的钱。
这篇短文,题目虽有两句,意思却不完整,结束时,我表达完整。
只要被打碎,我就随风飞。
只要未被打碎,我就还在这里,迎接生活给我的一切打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