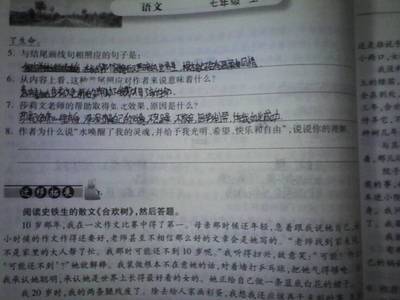蝈蝈的叫声

前几天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卖蝈蝈的,一个自行车上挂满了装满蝈蝈的笼子,蝈蝈的叫声此起彼伏,引来路人关注。蝈蝈给我的童年单调生活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问了一下,5块钱一个,连笼子一块,想也没想就买下了。
在法布尔的《昆虫世界》中,蝈蝈被称做“夜晚的艺术家”,意思是一到夜晚就是蝈蝈登场的时间。但在我的记忆中,蝈蝈的鸣叫是不分昼夜的。在法布尔的描写中,蝈蝈还被比喻为“蝉的屠夫”。但是,法布尔描述的蝈蝈和蝉大战,最终以蝈蝈的“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大胜为结局的情景我也没有见到过,这也与我记忆中的蝈蝈不相符合。在我的记忆中,蝈蝈是比较温顺的。当然,法布尔对蝈蝈叫声的描绘是生动而又贴切的“那像是滑轮的响声,很不引人注意,又像是干皱的薄膜隐隐约约的窸窣作响。在这喑哑而连续不断的低音中,时不时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急促、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毫无疑问,在城市,这些近乎完美的天籁之音无疑是绝响。
蝈蝈能不能吃呢?在我的记忆中,蚂蚱可以吃,但很少有人吃蝈蝈,尽管蝈蝈看上去比蚂蚱肥胖很多。毕竟,蝈蝈的叫声那么好听,吃蝈蝈无异于暴殄天物,不可想象。但在历史特定情境下也许是例外。我喜爱的老作家汪曾祺在《草木春秋》中写到当年他插队时的情景,就专门提到烧蝈蝈吃的情景:“草里有蝈蝈,烧蝈蝈吃!蝈蝈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一会儿就能捉半土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每逢看到这里,我都怀疑汪老吃的不是蝈蝈而是蚂蚱,尽管我知道博学多识的汪老不会弄错。
在我们豫东老家,蝈蝈的俗称叫油子,放暑假到豆田里逮油子是儿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小伙伴热衷于逮油子当然 是由于它独特的叫声。走在田野里,耳边传来“吱拉,吱拉”的悦耳声,没有人可以抵御这种声音的诱惑。用来装油子的油笼都是我们自己用高粱秆编的,准确点来说,不是编笼子,而是扎笼子,所用的材料是高粱秸秆。用小刀在秆的结合处切个小口,扣在一起,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和鲁班锁差不多,完全靠自身的结构去支撑,上面还可以做一个“提手”。笼子扎好后,不用一根钉子和绳子,而且结实好看。最后一道程序是把秸秆外面的皮去掉,这种有弹性和硬度的皮类似于织席子的篾片,很锋利。根据“房间”的大小,把秸秆皮裁成长短和宽窄不一的细条,横竖交织扎在秸秆上,一个外观漂亮、结实耐用的油笼就编成了。为了便于油子进出和饲喂,“房间”还有一个“门”。当然,也有简单和省事的,就如同我在大街买到的一样,就是用秸秆外面的皮编制的,圆形或者椭圆的,空间有点小,只能盛放一个油子。
油子买回家后,上幼儿园的儿子很喜欢,不时拿白菜叶、葱叶来喂它。油子看样子是饿坏了,吃得津津有味。但它对声音很吝啬,无论如何逗弄,就是不肯出声。过去油子不叫,我们常用的办法是拿来一个喜欢叫的油子和它放在一起,听到同伴卖力的歌唱,它当然也不甘寂寞。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把电脑打开,搜索出一段油子鸣叫的视频,把音箱放到最大。听着电脑音箱里传来“吱拉,吱拉”的叫声,我想它该开金口了吧。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这只油子很顽固,也许听出了这种电脑上的叫声是“赝品”,始终不肯“一展歌喉”。时间一长,儿子感觉没趣,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忙着玩游戏去了。
次日工作忙,我一大早就出去了,中午家里也没人,晚上回到家时才想起油子一整天没人饲喂,是不是要饿死了。当我拿着菜叶走到油笼边时,终于传来了久违的悦耳的“吱拉,吱拉”奏鸣曲。尽管单调不如和鸣,但毕竟聊胜于无。晚上,儿子从幼儿园回家时,听到“吱拉,吱拉”的叫声,没有表现出我期望中的惊喜,听了一会就走开了,让我的内心很失落。妻子上晚班,晚上回来时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油子的鸣叫,感到很意外,还以为是从窗外传来的。
我们家一墙之隔是一大片荒地,本来是从农民手里征用来搞房地产开发的,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就一直荒在那里。时间一长,院里的居民就你一小块、我一小块把荒地开成了菜地,一到夏天,推开窗户一看,黄瓜、番茄、青菜,绿油油一片,煞是养眼。妻子猜测油子的鸣叫从窗外传来也很自然。不过,时间一长,不光是妻子,连儿子也对“吱拉,吱拉”起了厌烦。特别是在午睡和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油子的鸣叫难免大煞风景。最后,妻子、儿子的抗议逐渐升级,我也抵抗不住了,最后的决定是把油子送人。满怀欢喜地迎进家门,最后落个如此结局,连我也无法想象,或许过去的已经真的过去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