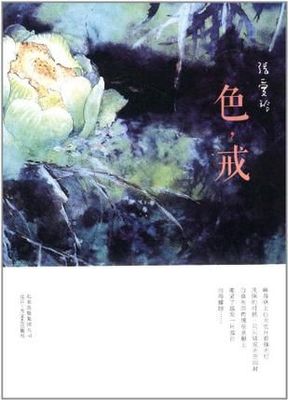《三戒》为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写。有人说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因为小序中说:“吾恒恶性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淡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于是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以为《三戒》的主旨是:警戒世人——如毫无自知之明而肆意逞志,必然自招祸患;或讽刺权贵——如官高位显、无才无德而仗势欺人,擅威作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就没有好下场。这样理解,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比喻本来是“多边”的,一个喻体同时兼指几个本体也未尚不可。
然而这种分析与概括毕竟过于笼统肤浅。
林纾曾说柳宗元的寓言后面,“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韩柳文研究法》)。这“最有力量,最透辟”的一句,在《临江之麋》中是“麋至死不悟”,在《黔之驴》中是“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国今若是焉,悲夫”,在《永某氏之鼠》中是“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每一句都点明了本则寓言的寓意,并且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分开来看,这三则故事都是各自独立的,然而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三则寓言的排列却不能随意换位。
麋即麋鹿,哺乳动物,比牛大,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俗称“四不像”,它是原产中国的珍稀动物。麋为什么“至死不悟”?因为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临江之人捉来豢养,与家犬生活在一起,备守呵护,犬不敢欺;久而久之,它就以为大凡是犬,都是它的朋友,于是出门与外犬嬉戏,终被外犬共杀而食,狼藉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教育杀人”。钱钟书在《读〈伊索寓言〉》中说:“我认为寓言(当然这里所指的寓言不包括柳宗元的《三戒》之类)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小麋鹿不就是被临江之人宠傻“洗脑”了,认为所有的犬都会和主人家里的犬一样怕它让它,结果一出门就被外犬所共杀的吗?由此可以看出,这则课文中的麋,暗喻幼稚、天真却被“洗脑”教育夺去了生命的人们。
当然,临江之麋还只是被无意识地“洗脑”洗去了它潜意识中对犬的警惕性,人类社会中还有很多有意识的“洗脑”的教育,如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的主人公,还在读中学就被送到战场成了法律西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再如我国建国初期的少年刘文学,因不愿放过偷辣椒的地主被地主杀死;稍后一些,又有优秀少年赖宁为扑灭山火丧生:如果不是“洗脑”教育,就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置于首位不可。
驴是善良、憨傻的动物,暗喻成年人中的老实人。这些老实人没有特别的技能,更不工于心计,往往憨得近傻,蠢得可怜。李世民的小小说《我的民工哥哥》中的主人公王小石,就是一个像驴一样憨傻的青年。王小石是个小工,当伙伴们吹牛自己力气大、家里种的冬瓜大、老婆怎么怎么样时,他都保持沉默,因为他没有吹的资本。但是当有人吹谁的亲戚官大、管得人多时,他着实忍不住了,就说自己有个弟弟叫王大牛,“就在这个城市里,当科长呢,他管的人呀,数不清”,并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作证明。后来,大家渐渐对王小石的话产生了怀疑,开始疏远他了,于是“平时连一块雪糕也舍不得买的王小石,居然买了一包又一包的礼物”,要带伙伴们去他弟弟家喝酒。谁知“惧内”的弟弟竟然借口媳妇在卫生局上班讲究卫生,不让进门。回来时,他又拿出自己的200元钱,说是弟弟请他们喝酒的,弟弟有公务,不能相陪。至此,王小石的诚实品质就像那头黔之驴一样,被“老虎”吃掉了。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驴以为自己“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王小石则以为自己毕竟是王大牛的哥哥,自己带了一大包礼物去换他一杯酒喝,总是不成问题的。黔之驴对虎之挑衅“不胜怒,蹄之”,终于被老虎吃掉了;王小石抵挡不住伙伴们的影响,抬出了当科长的弟弟给自己撑面子,终于“醉”了。
像黔之驴这样的人很多,憨傻却落得悲惨凄凉的下场,真是可悲呀!
当然,黔之驴也可以暗喻那些不学无术而居于高位的人,但却不能暗喻那些“无才无德而仗势欺人,擅威作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官高位显”的人,因黔之驴毕竟没有“仗势欺人,擅威作福”。
鼠当然只能喻指坏人,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社会政治清明,贪官污吏不敢为所欲为;社会政治黑暗,贪官污吏就横行无忌。然而“物极必反”,一旦失势失怙,贪官污吏就无可遁逃。不过凡是贪官污吏,他们都与永某氏之鼠一样,以为他们“饱食无祸”是可以永恒的。
以上分析,也还流于表面,并不深入。倘若深入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三戒》批判的“世之人”的共性是“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即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源,本性,本能,本质,却凭借自己拥有的外在的势力或外形的庞大好胜逞能——“依势以干非其类”的是麋,“出技以怒强”的是驴,“窃时以肆暴”的是鼠,但在麋、驴、鼠的背后,还有一个“乘物以逞”的“世之人”,一只违天逆理的罪恶之“手”——这个“世之人”就是仗恃权势胡作非为的当权者(如《临江之麋》中的“临江之人”,《黔无驴》中的“有好事者”,还有《永某氏之鼠》中的“某氏”),这只罪恶之“手”,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
麋本善类,因其年幼无知,被“世之人”“洗脑”,以致忘其本性,死于非命,多么可怜啊!“洗脑”教育之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教育者不可不戒。驴本长厚,斗非其长,屡被狎戏,“不胜怒,蹄之”乃不得已,其死也,非其过也。即使不怒不蹄,能无恙乎?鼠虽恶类,然若不为人庇护溺爱,则战战兢兢,岂敢如是公然肆虐?由此可见,麋之“依势以干非其类”,驴之“出技以怒强”,鼠之“窃时以肆暴”,“卒迨于祸”,自身虽不无过错,然皆有人祸之也。
毫无疑义,《三戒》中的三个故事都是悲剧,无论麋、驴、鼠,都是权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受害者。如果不是临江之人畜麋、宠麋,使麋忘其本性,麋就不可能丧身于众犬之口;如果不是“好事者”载驴入黔,驴也不可能成为黔之虎的美餐;如果不是永州某氏的荒诞迷信,使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盗暴尤甚”,鼠就不至于让“后人来居”,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何以至是乎哉?”不就是因为那些“世之人”(没有监督不受约束的掌权人)“乘物以逞”(滥用权利)吗?由此看来,《三戒》所控诉的,主要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恶,柳宗元所“恒恶”(永远讨厌)的,主要还是滥用权力的掌权人。柳宗元不就是被那些滥用权力的人贬谪到永州的吗?
《论语•季氏》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从上面的论述中可见,柳宗元的《三戒》与孔子说的君子“三戒”是不同的,柳宗元《三戒》的意思是三个值得警戒的故事,其警戒的内容有:一戒权力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二戒洗脑迷信,宠爱溺爱;三戒躁怒,骄傲自大。总之一句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推己之本”,不可“乘物以逞”,不可违背天理(客观规律)人情;否则,悲剧将不可避免。
附:
(一)三戒(并序)[唐]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9],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11],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15]。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选自中华书局校点本《柳宗元集》)
(二)要推己之本,勿乘物以逞
古往今来,皆倡导固木先固本,做事先做人。读柳宗元的《三戒》,当有新的教益。
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无能而仗势,假威且作福:或如临江麋,依势忘本,乘物以逞;请或如黔之驴,身无真技,外强中干;或如永州鼠,狐假虎威,有恃无恐。其共同特点是,不知推己之本,只是倚仗人势依凭外力,作威作福甚至欺弱霸市。人们厌恶这种人――在权势面前,他们既无灵魂,亦无人格,极尽阿谀奉承,奴颜卑膝;在权势之外,他们又仁心不在,诚意不留,极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人们又可怜这种人――既可怜他们在权势面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在拉关系、找门路时一脸乞求、一味巴结的奴才之相;又可怜他们对"靠山"是否稳固,"关系"是否变化而朝夕不能踏实、平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魂之态;更可怜他们一朝大树倾覆,猢狲猝散甚至厚颜攀新主的那种可[]气复可恨的无赖之状。
人们更鄙视这种人――乘物以逞之流,无真才可言,无实学可道,无品德可称,无人格可论,其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关系的寻找和人身的依附。这种人实际上已蜕变成行尸走肉,无骨、无魂、无神,虽耀武扬威有时,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步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之后尘而赤条条一身遁无影呢?
冷静想一想,临江麋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麋,黔之驴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驴,永州鼠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鼠,原本有着三条深层的原因:其一,有势可仗。麋、驴、鼠的悲剧,首先源于为"乘物以逞"之流提供可仗之势者。我们有些人,或出于自身的心理缺陷,或出于自信心的缺乏,或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或推崇,热衷于营造小圈子、小团体,一遇附势之流,则欣然接纳,在用人上,有意无意地"关系高于一切",甚至于纵容"乘物以逞"之流打旗号以谋私惠。可以说,是提供可仗之势者促成了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而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悲剧之元凶乃提供可仗之势者。其二,攀势以仗。导致"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乘物以逞"者自己应负不可推卸之责。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寻仕途不循正道,求功名不择手段,寄希望于走捷径,以至于弃人格廉耻于不顾而趋炎附势。殊不知,有无相生,高下相倾,炎攀势附之日,亦即祸生灾降之时,悲剧的制造者,原本是悲剧的主人。然而,正如柳公所言,这类人中,许多仍是"至死不悟"!其三,畏势纵仗。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酿成,有"有势者"的原因,有"攀势者"的责任,但是,与芸芸众生的"畏势"不无关系。如若这个世界十分地洁静,如若有势者不势,无势者不畏势,虽有"有势者"提供前提,"攀势者"极尽内因,也难得"以逞"。从这种意义讲,社会对"乘物"行为的沉默、认同、纵容,也为"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从柳宗元的《三戒》中,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要自知之明。要担当大事,成就大业,必须尽心在"明强"两字上,以明强为根本。人要有自知之明,既知己长,亦知己短;既善扬己长,又勤补己短,如果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看得不明不透,如果不自量力,一味蛮横逞强,定难自立于世。二要自强不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富强,必须要有实力;一个人要自立,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因此,有志者必须自强不息。不仅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知识财富,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文明成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自强、自坚、自立。三要自善其身。一个人要成为有用之材,必须时时注重修身养性。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为无涵养、无作为之辈。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如果我们把权力看得很轻,把名利看得很淡,把欲望看得很薄,才能做到淡泊无争,心无旁骛,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做一个真正的强者。(2005-11-04光明日报裘新实)
(三)《黔之驴》寓意多 认识自己才是为人处事之本
《黔之驴》是柳宗元最著名的寓言故事之一。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从多个角度均可解读出不同凡响的寓意。
比如从老虎的角度而言,就是不要被对手的气势吓倒,不要一见貌似勇猛、貌似强大的对手就不敢上阵、不敢对抗。事实证明,架子大、派头大的家伙往往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对手,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藐视它,但在行动中,在细节上则要十二万分地关注、观察对手的动向,只有认真研究清楚对手的所有情况,才能拥有正确的决心与行动。这只老虎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在树林里悄悄观察,驴子一叫,吓得要命;后来习惯了,就在驴子身前身后转悠,还是在观望;最后惹恼了驴子才探到它的底牌,于是果断出手,横扫而去。
还有驴子的角度。驴子的遭遇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就不要虚张声势、张牙舞爪。生活固然美好,也固然善良,但它有时候会很残酷,也会不留情面。总有一天,虚假的西洋镜会被无情的生活拆穿。面具再华美艳丽、威猛刚毅,也终究只是面具,不是自己的真实面孔。而面具一旦滑落,就会暴露出干瘪丑陋的本来面目,到那个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品尝苦果的到底是生活还是自己。
问题出在第三个角度,即柳宗元的角度。在这故事的结尾处,柳宗元感慨:驴子看上去身形高大似乎很有德行,声音洪亮似乎很有本领,但如果不显示它那可怜的本事,老虎虽然勇猛,因为心怀疑惧,终究还是不敢吃它。现在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悲哀!显然,这个角度不是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问题,而是埋怨驴子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也就是说,柳宗元认为驴子之所以被吃掉,主要不是因为没本事胡乱虚张声势,而是不善于伪装自己。在柳宗元看来,只要驴子凭着高大的形体,保持沉默的态度,不随随便便暴露自己的短处,装作一个深沉而有内涵的"巨无霸",就可以永远确保自己性命无虞。
这个结论或者角度多少有点儿奇怪,而且与作者创作的初衷也不大一致。在《三戒》小序中,柳宗元说他写《黔之驴》的主要原因是:"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出技以怒强……然卒迨于祸。"意思是说:世人往往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们总是借助外力逞强好胜,常常草率出手以致激怒强者,最终不免遭祸。对于遭贬永州的柳宗元来说,这样的人生慨叹当然意有所指,个人的感悟也自然蕴含其中。但将“生存之道乃在于善于隐藏缺点”作为《黔之驴》故事逻辑的必然结论,的确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浙江省东阳市第三高级中学(六石高中)许国申
(康 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 震 光明日报 2012-2-2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