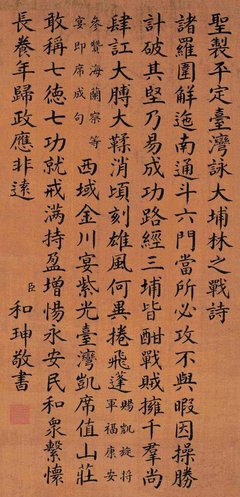芭比娃娃就躺在她的身边,被人细心地用小毯子盖着。唐果扑上去抱住洋娃娃,脸埋进被子里闷闷地笑起来。
独自玩了一会,唐果跳下床,赤着脚踩在木质地板上,感觉有点凉。
她抱着洋娃娃,小心翼翼出了房间,看到楼下有微弱的淡黄灯光,便轻手轻脚下了楼。
楼下可能是客厅,空间很大,却空空荡荡的,只摆了一张长沙发,旁边是不大的桌子,铺了一条地毯,更显得大而冷清。
唐果愕然发现,房间里有一整面竟都是落地玻璃窗,光滑洁净的大块玻璃,连成一整面透明墙壁,被黑色的窗框分割为数块,窗帘此刻卷上去,窗外寥落的星光便毫无遮拦地洒了进来。
这里想必是非常高,视线所及无甚阻拦,远远近近流光溢彩的都市浮华,星星点点,尽收眼底。
那个人正站在窗前,背对着她,看着脚下万千灯火。
暖气开得很足,他只穿了件松松垮垮的白色背心,和一条黑色的休闲短裤,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夹着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那样子多了几分倜傥不羁。
似乎感觉到什么,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楼梯口的唐果。他的脸隐藏在烟雾之后,神色模糊,然后他招招手,示意唐果过去。
唐果紧紧地抱着怀里的洋娃娃,慢慢走过去。木地板渗出丝丝的凉意,浸的脚底板冰冷,她却仿佛无知无觉,只仰起头,着迷地盯着他烟雾之后的脸。
韩穆伸出手,揉了揉唐果的脑袋,也不作声,继续默默地抽着烟,看着窗外。
黑暗的夜空还落着雪,唐果站在他身边,嗅到他身上刚洗浴完清爽的味道,有如夏夜雨后潮湿的的青草芳香,和着淡淡的烟草气味,贸贸然闯入她的鼻尖,又七拐八拐地钻进心里。
过了一会,韩穆低下头,看到唐果一张小脸泛着红,神色紧绷。他疑惑着问:“怎么了,小丫头?发烧了?”
说着伸手拭了拭她的额头,并没有热度,又见唐果光着脚,于是一手把她夹在腋下,走两步扔到了沙发上,自己也在旁边坐下,抖抖烟灰,纳闷地说:“怎么回事......睡一觉反而没精神了.......”
唐果也疑惑自己这是怎么了,这莫名其妙的紧张。她夸张地大声笑了笑,扑上去揽住韩穆的脖子:“刀疤脸,你怎么没睡啊?你不困吗?”
韩穆仰头靠在沙发上,吐了口烟:“这几年我已经睡够了。”烟雾在他脸前弥漫,这让他的脸显得神秘而有些悲伤。
唐果偎上前,凑到他脸前仔细端详着他。其实她已经很熟悉了这张脸,偏偏总也瞧不够。
眉毛是远山的青黑,长睫是蝶翅的颤动,鼻梁是山峰的俊秀,而线条美好的嘴唇,则是那朵最美丽的花朵的浅红。就连那道横亘而过的伤疤,都成了水墨国画里轻描淡写清清秀秀的一撇飞白。
韩穆突然睁开了眼睛,那里,汇聚了所有的星光和月色。
唐果离他那么近,近得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那双清亮的眼睛,和那双眼睛里的自己。
韩穆倒被吓了一跳,推开趴在他身上的唐果,拿了一瓶酒回来,又站在窗前看夜景。
“你还敢喝酒!”唐果叫起来。
韩穆叼着烟,手指夹着那一小瓶酒,另一手正拿开瓶器钻着软木塞,听了这话,似笑非笑地看向唐果,手上动作却是没停。
唐果讨了个没趣,便懒散地窝在沙发一头,就着昏黄的灯光研究旁边桌子上的相框。照片上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笑起来的样子仿佛夏天的阳光。
木头相框被摩挲的光滑无比,有些地方甚至模糊了纹路。唐果忽然有种酸酸涩涩的感觉,那味道从心里模糊地冒上来,像是青涩早熟的苹果味道。
唐果冲着韩穆的背影扬扬照片,大声问道:“刀疤脸,照片上这人是谁啊?”
韩穆的背影却似忽然僵住了,他一动不动的站着,肩背紧绷。漆黑的窗外雪花簌簌地落着,有风声呼啸而过,裹挟着飞舞的雪花,冷眼旁观人间的夜色浮华。
唐果有些害怕了,她开始后悔问这个问题。
房间里坟墓一般寂静,只有窗外风声肆虐,一阵阵抽打着玻璃窗。唐果希望他赶快开口说句话,随便什么都好。
也不知过了多久,韩穆总算低声开了口,声线压抑而嘶哑:“是我爱的人。”
唐果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虽然还有疑问,却也不敢再问了。她把相框放回桌上,端端正正地摆好,忍不住又看了一眼,那个女子笑容嫣然,明亮得似乎能够照亮黑夜。
韩穆手上仍然机械地动作着,拔下软木塞扔在一边,仰头喝了一口。冰凉苦涩的味道划入体内,渐渐浇灭了他眼睛里最后的那一点点光亮,窗外万千繁华灯火,却再也映入不了他的眼。
唐果怀里紧紧抱着洋娃娃,不知不觉躺在沙发上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自己身上盖了一条薄毯。
正是黎明时分,雪下了一夜,此刻已停了。清晨的天光浅淡,映着白的刺眼的积雪,世界似乎褪去了一层浮华,只剩下干净清新的白色。
韩穆这时端了两杯牛奶走进来,看到唐果醒了,微微一笑:“醒了?喝点东西吧。”说着把牛奶递给她,坐在桌子对面的地毯上。
他见唐果直愣愣地看着自己,又扬扬下巴:“这有饼干,将就着吃一点吧。”
唐果哦一声,端起牛奶喝了一口,又被烫的咋舌,她狼狈的小样逗得韩穆笑起来。
唐果偷偷瞟着对面,桌子对于坐在地上的他稍稍有点高,他姿态散漫地坐着,一条腿屈起,一手撑在身后,另一手拿了饼干浸到牛奶里,慢慢地吃。
他又恢复了平静,仿佛昨晚窗前那个落寞的背影并不是他,那脆弱得一触即碎的气氛也仿佛并没有存在过。要不是几个空酒瓶散落在窗前,唐果都要怀疑那只是自己的一个梦了。
吃完了早餐,韩穆去冲了个澡,唐果百无聊赖地躲在沙发上玩洋娃娃。
没多久,就见韩穆光着上身从浴室里走出来,头发还滴着水,边走边低头用毛巾擦着。他的身材高而瘦,四肢修长有力,脸上胡茬刮干净了,看起来清清爽爽。
让唐果心惊的是,他的身上横七竖八落了许多道疤痕,时日久了,颜色浅淡,却还是看得出来。
细长的鞭痕,烟头的烫伤,还有匕首恶意的划痕。手臂上,脊背上,胸前。似乎所有的酷刑都在他身上试了一遍,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块画布,涂满了伤痕。
可能是昨晚夜色深重,唐果并没有看出来。熹微晨光里,那伤痕一处处让她胆战心惊。
韩穆抬起头看到唐果缩在沙发里,眼睛里溢满了惊恐的泪水,他愣了一下,顿时醒悟过来。他拿了件睡袍披上,蹲到唐果身边,揉揉她乱糟糟的头发。
唐果下意识地向里缩了缩,满脸惊恐地望着他。
韩穆被她恐惧的眼神看得一愣,手不由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放下手,温和地低声说:“乖,别害怕。”
唐果仰头看着他,他的脸沐浴在晨光里,模糊不清。
然后他站起身,上了楼,没多久换了一身正装下来。
韩穆身材修长,穿上这身笔挺的黑色西装,更显挺拔。他的脸色苍白,刀疤鲜明,搭上这考究的西装,同时赋予了他一种奇异的邪气和贵族气质,二者奇妙的混合在了一起。
韩穆站在楼梯口,仰头整理着白色衬衫的领口,一边说着:“小丫头,我要出去一趟,程时会陪你玩,他马上到。”
唐果跳下沙发:“你要去哪里?我不要他陪我玩,他欺负人!”
“程时不会欺负你了。”韩穆耐心地说,他走到唐果跟前,轻声笑,“你也不要欺负他,我很快会回来。”
这时门铃响起来,韩穆走上前,从猫眼里向外看了看,开了门。
黄毛小子一下子窜进来,见了韩穆,愣了一下:“韩哥,你要去见谁?”
“秦叔。”
“我也去!”程时立刻说。
“不,你陪着小丫头。”他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
程时只好点点头,又问:“你们在哪里见面?”
“一家茶楼。我打听过,那里不是秦叔的地方。”
“那就好,”程时点点头,“这老狐狸,咱们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一直对你很提防,这几年也多疑了很多,还是小心为好。”
韩穆突然叹了口气:“他毕竟曾经待我很好,那时我心里是当他作父亲的......我只希望能够跟他把话说明白——我不愿意跟他争。”
程时旁观者清,心道只怕是不容易:“现在跟以前毕竟不一样了,以前你替他做事,他是大哥。可现在大家都心里明白,你这事是怎么回事,弟兄们服的是你,那老东西对你不地道,这几年也昏了头了,净做蠢事,弟兄们早就对他不满了。就算你不愿跟他争,他恐怕也拿你当眼中钉。”
韩穆抬头笑了一笑,眼神云淡风轻:“我明白,但我总得试一试。”
程时轻轻叹息了一声,沉默半晌,程时说道:“韩哥,那小猴子的地址找到了,你相信吗,她爸妈竟然还没发现女儿丢了。”
两人看向沙发那边,唐果正窝在角落里摆弄着洋娃娃,一个人玩得咯咯直乐,小小的脸上尽是满足喜悦。
韩穆渐渐听明白了,唐果现在的母亲是继母,她的亲生母亲在她三岁时就死了,终日郁郁,久病不得医。她死的时候披头散发,形容枯槁,不停诅咒着唐果的父亲。
无非是那些俗套的情爱、背叛和仇恨,唐果的生母至死都不愿离婚,宁愿所有的人都不快活,尽管她是最不快活的那个。她死了之后,这场旷日持久两败俱伤的战争立刻草草收场了,另外两个人结婚了,在她死去的一个月多后。
可想而知唐果的日子不会好过,因着她的生母,两个家长都不喜欢她。韩穆不知道唐果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可是那个小女孩选择在大年三十的寒夜里,在自己的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地离开了那个家,义无反顾。
那个看起来天真快乐的小女孩从来都说,她想要芭比娃娃,一定要芭比娃娃。伪装成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其实是在倔强地掩饰另外一种伤心。
韩穆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慢慢走到唐果身边,轻轻蹲下。唐果仰起小脸,迷茫地看着他。他的眼神很复杂,她看不懂,但是那双清澈的眼睛,亮晶晶的黑眼睛,就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好看。
那双好看的黑眼睛,温和地注视了她一会,然后那个人伸出手,拂开她额前柔软的栗色头发,轻轻地在上面亲吻了一下。
那个轻柔的亲吻,柔软,冰凉,像夏日的溪水,像清凉的薄荷糖。
唐果不知怎么的,眼泪突然涌出来。她慌的用手背拭去泪水,咧开嘴冲着韩穆笑了。
韩穆揉揉唐果的头发,温言道:“在家乖一点。”便起身离开了。
唐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眼泪忽然止不住地往下流,像是开了闸的水,拦都拦不住。朦胧的泪眼里,只看到程时一张受惊的脸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她却什么都不想管,藏了那么久的伤心委屈,全都和着眼泪流成了河。
如果唐果当时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定会哭的更加痛彻心扉,喊破喉咙也要留住那个人,她的刀疤脸。
可是那时候她只是忘我地哭着,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她越哭越委屈,越哭越伤心,哭的昏天暗地日月无光。泪如雨而下的时候,她还在模模糊糊地想着,刚才的那个吻,就像是她最爱的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唐果终于停止哭泣的时候,程时也累得散了架。他又是送水,又是递纸巾,忙前忙后地伺候这位主子,累得腰酸背痛。
见唐果安静下来,他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长叹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累死了。”
唐果呆呆的没有反应,只安静地蜷缩在沙发的一角,眼神茫然地看着窗外。
程时有意挑拨她:“怎么啦,小猴子哭傻啦?变成傻猴子啦?”
唐果没多少兴趣地看他一眼,又看向窗外:“刀疤脸说过要乖,我才不理你。”
程时哼了一声::“看不出你倒挺听韩哥的话,你能乖最好。”
过了一会,程时忍不住又开口逗她:“小猴子,你多大啦?”
“十岁。”唐果兴致寥寥地答。
“你想知道我多大吗?”
唐果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又面无表情地转回头。
这沉默的鄙视让程时恨得牙痒痒的,他又问:“那你想知道韩哥多大吗?”
唐果转过了头:“多大?”
“啊哈!不告诉你!”程时得意地大叫。
话一出口他自己也汗颜了,老大不小的人了居然在跟一个小女孩玩这个,更何况这个小女孩此刻的蔑视明明白白写了满脸。
“看你可怜就告诉你吧,韩哥二十七了。”
“啊,比我大了这么多......”唐果叹口气说。
“废话,谁不比你黄毛丫头大这么多。”
唐果不理他,把那个相框拿给他看,问他:“那你知道她是谁吗?”
程时一脸狐疑地望着她:“你问这个干吗?不能告诉你。”
“我想知道,快告诉我吧,我保证对谁都不说,刀疤脸也不说!”唐果摇着程时的手臂,像条谄媚的哈巴狗。
“不行不行,韩哥会不高兴。”程时连连摇头,开始后悔把她的兴致挑起来,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
“他又不会知道......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刀疤脸说你欺负我!”
程时一脸愤恨,气得换了个物种称呼她:“那也不行,小兔崽子。”
“你要是不说......我、我可就哭了啊!”
唐果作势便要抹眼泪,程时忙劝住了她:“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了行吗?”他心里暗骂,真是个难缠的小鬼。
唐果坐在他旁边,托着腮,一副专心听讲的模样。
“不许告诉韩哥啊。”程时又警告了一遍。
“一定一定。”
那个故事不长,程时却讲得字斟句酌,异常艰难。到底谁是谁非,当时年幼的唐果似懂非懂,很多年后她却也没有想明白。
故事的开头极像一部烂俗的言情故事。黑帮大哥年轻的的得力手下,这个故事里他叫做A。A暗恋着黑帮大哥漂亮单纯的女儿,可是她只把他当作体贴的兄长。女孩子18岁那年,在街头被一群小混混欺负,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男人救了他,爱情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女孩,她的世界里再容不下别人。
这个男人原本只是黑帮大哥手下一个普通的打手,却有着非凡的头脑和冷静的智慧,他是故事中的B。在他摆平了几次帮派火拼之后,黑帮大哥渐渐信任了他的能力。A和B一起,两个年轻男人成为黑帮大哥的左膀右臂。
这原本会是一个无趣的爱情故事,毫无曲折的两情相悦,幸好故事出现了转机。A陷入了日日夜夜的深深嫉妒之中,他不能容忍女孩的身边有着别人。他派人对女孩的英雄进行彻底的调查,并日夜监视他,终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那个男人在秘密地与警局里的人接头,他是卧底。
故事的高潮终于来了,A带着许多手下在那对情侣私定终身的小公园里,围住了手牵手的他们。女孩求他放过情人,她说她也知道,但他们深爱着对方,他们已经决定第二天就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城市,离开黑道白道。
A举着枪不为所动,女孩慢慢跪了下来,掏出了一把匕首。那把匕首是A送给女孩的,那时他们关系亲密,他教她防身,她嘻嘻哈哈地挥舞匕首。
女孩说,她一直把他当大哥,但是她从没爱过他,她爱的是她牵着手的这个男人。如果大哥杀了他,她也只能替他报仇。
她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中,口气时而强硬,时而凄婉。她一声声唤他大哥,说他们行李都打包好了,只等着黎明上路。她求他给他们一个机会。
A说,不。
A说,他竟然让你跪下来,他就该死。
然后他开了枪。
女孩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抱住倒下的男人身体沉默地哭泣。然后她疯了一般冲过来,狂乱地挥舞着匕首,A怕她伤到自己,上前抱住她,匕首在混乱中划伤了A的脸,鲜血淋漓。
A手里的枪掉在地上,女孩扑过去捡起来,对准了A。

A满脸是血,他的眼睛在鲜血之后平静地看着女孩。女孩的手指开始颤抖,她摇摇头说,不,我没有你狠心。
然后她举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子弹穿过头颅,掀飞了半边头骨,鲜血和着脑浆喷射出来。女孩倒了下去,伏在了B的尸体上。
这个故事讲完了,作为大反派的A自然就是韩穆,那时与韩穆情同父子的黑帮大哥是秦叔,B则是当年媒体上大肆渲染的悲情英雄纪凡。这个年轻的刑警,踏上工作岗位没多久,就因为一次危险的卧底任务牺牲了。活着的时候他默默无闻,死后却成了人人交口称颂的英雄。
唐果始终都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是背叛,还是嫉妒?那场惨烈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是宁折不弯的痴情,还是成本高昂的报复?
后来唐果怀疑这段故事里掺杂了太多自己添油加醋的想象。故事发生的时候,她还只有三岁,那一年,她的亲生母亲刚刚死去,他的亲生父亲刚刚娶进了另一个女人。
那一年,她悲惨的童年刚刚开始。
对于她仅有的十岁年龄来说,那是个太遥远的年代,连亲生母亲充满怨毒地死去的场景,都渐渐在她记忆里模糊了,可是那段她未曾见识过的故事,却在回忆里越来越清晰,细节丰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唐果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在这段记忆中发挥了多少作用,但是当年程时绝对没有讲得这样声情并茂。他干巴巴的几句话就说完了,经过唐果不懈的努力追问,才很不耐烦地有一句没一句地答上两句。
即使程时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让唐果很不满,结局那近乎惨烈的鲜血和死亡还是让小女孩听呆了。
她睁大了眼睛,呆愣愣地看着程时,好半天才问了个没头没脑的问题:“那个小公园是在哪里?”
“问这个干吗?”程时一脸惊异地望着唐果,还是告诉了她。
唐果慢慢叹了口气,在那个地方唐果第一次见到了刀疤脸。
“那刀疤脸后来怎么样了?”
“你说呢?死了个条子这事总不能糊弄过去吧,这事当年闹得很大,没法随便推一个人出来。韩哥那时候大概是心死了,又不想让秦叔为难,就自首了。”
“刀疤脸他......进监狱了吗?”
“秦叔那老东西,我看他当时根本就是半推半就。虽然花了钱疏通,判了过失杀人,但是因为杀了警察这种事进去,那是人过的日子吗?上头都睁一眼闭一眼的,那些拿枪的垃圾肯定是把人往死里整啊,真不知道韩哥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唐果想起韩穆身上那大大小小遍布的伤痕,一时间心头各种滋味:“可是他......毕竟杀了人了......”
程时冷哼一声:“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不杀他我们就得死!这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
“可是......你们可以去做好人呀......”唐果的思绪打了千百个结,解也解不开,她隐隐约约总是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你们做好人,大家就不会杀来杀去的了。”
程时笑了一声:“你觉得我们是坏人?”
他做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凑近唐果:“坏人会把小猴子从街上带回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吗?”
唐果被他吓了一跳,往后一缩,还是硬着头皮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杀了人,你们还是坏人。”
程时倒是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小女孩。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凝视着天边淡薄的红日,在覆了新雪的高楼上洒下淡淡金点。
“可能是这样......可能你是对的......这件事很奇怪,我这一辈子都在做着打打杀杀的事,可是我刚发现,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坏人。”
“也许你是对的......”
晨光里程时的背影深刻,像一幅光与暗的油画。
当时年幼的唐果所笃定的黑是黑是黑白是白,在多年以后,唐果自己也模糊了。她开始无数次的怀疑,到底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午夜梦回,唐果会怀念起多年前十岁的那个小女孩,在她的眼里,有着清清楚楚不容置疑的一条线。
长大后的唐果失去了那条线。
程时的手机就在这时候响起了。窗外红日稀薄,寒风卷起满地积雪,年幼的小女孩躲在沙发里玩着总也玩不腻的洋娃娃,她并不知道,缠绕她一生的梦魇即将开始了。
程时接了电话,叫了声韩哥便立刻被打断了,没说几句他立刻脸色大变。
他和韩穆都没有想到,秦叔竟会在茶楼就痛下杀手。幸而那里毕竟不是秦叔的地盘,只带了不多几个人,也没有用枪,才被韩穆逃了出来。可是他也只来得及打电话通知程时,只怕秦叔的人已经到了他这里。
挂了电话,程时快步走到窗前,向下望了一眼。尽管距离很高,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上横七竖八地停着数辆黑色轿车,聚集在大厦门口。
他皱眉骂了一句:“该死!”
唐果不明所以,她站起来,困惑地看着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赶快,我们得离开这里。”
程时一个箭步越过沙发,抓起唐果的手向外冲去,向来嬉笑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他的严肃感染了唐果,唐果不由也紧张起来,她被他拉扯得跌跌撞撞,莫名的恐惧充盈了她幼小的的心。
跑到门口,唐果突然想起来了什么,甩开程时的手又奔了回去。
“快!没时间了!”程时一脸的焦急。
唐果抓起落在沙发上的洋娃娃,揣在怀里,又快步奔回来。
程时索性一把抱起唐果,快步奔了出去。
唐果的脑袋搁在程时的肩上,随着他的步伐一下下磕着他的肩膀。过道昏暗,紧闭的房门一个个在眼前闪过,视野里的景物晃动着。唐果觉得自己快被晃散了架了,可是她紧闭着嘴唇,不敢说话,程时紧张粗重的呼吸声清晰地传入耳里,让唐果害怕极了。
她忍不住颤抖着轻声问:“刀疤脸呢?”
程时的声音出乎她意料的温柔:“他没事。别害怕,闭上眼睛。”
唐果听话地闭上眼睛,黑暗给了她虚假的安全感,她慢慢平静下来。
程时奔到电梯前,按了向下的按钮,然后便迅速顺着楼梯冲下去。这一手也是无奈,对方人太多,只能寄希望于这样能够分散他们。
没跑几步,就听见楼梯下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程时暗叹一声,退回楼梯口墙壁的背面等待着。
那个等待过程其实很短,在唐果的记忆里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程时放下唐果,蹲在她身边,欲言又止,他的眼神是唐果从未见过的悲伤和沉重。他轻轻拍拍唐果的脑袋,最终只是说:“小猴子,别害怕,呆这别动。”
脚步声终于近到身边了。一个声音在不耐烦地抱怨:“该抓的跑了,来找个毛头小子有个屁用啊。”
另一个声音鄙夷地回应:“你懂个屁!目光短浅,难怪做不成大事。”
前一个人顿时骂开了,一个颇为稳重的声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都给我闭嘴!安静!”
一个识趣地闭上了嘴,另一个气焰也小了许多,一边还在小声的嘀咕,一边跨过楼梯口。
程时闪电般抓住那人的手臂,狠狠向后一折,那人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手里的枪掉下去,被程时眼疾手快捞在手里,对准了那人的太阳穴。
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般流畅,只发生在一秒钟,其他几个人回过神来,纷纷举枪对准了他。
程时把那人挡在身前,笑道:“都给我小心一点,不要走火了。”
他眼神紧盯着其余人,小心缓慢地向电梯移动,唐果躲在他的身后,小脸吓得煞白。
这短短几步路走得几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到了电梯旁,程时用手肘撞了下按钮,仍是紧紧盯着他们:“我劝你们不要跟上来。”
电梯升了上来,门缓缓打开了,三人小心翼翼地退了进去。
眼看电梯门缓缓合上了,那些人愤怒不甘的脸渐渐消失在门缝里,程时和唐果都松了一口气。
被枪指着的那人一边肩膀脱臼了,疼得满脸是汗,他抽着冷气说:“哥们,能先松开我一会吗?”
程时用枪托狠狠敲了下他的肩膀:“少废话。”
那人发出一声惨叫,不吭声了。
程时低头看了看唐果,她怀里紧紧抱着洋娃娃,浑身都在颤抖,脸色却还算镇定。
程时悄悄叹了口气,低声对她说:“别害怕,小猴子,会没事的。”
唐果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他,轻轻点了点头。
电梯到一楼停了下来,门缓缓开了。对方得到了消息,电梯口围了一圈人,都是神色紧张地拿着枪盯着他们。
程时身体紧贴着身前的人,枪抵在他的后腰,另一手把唐果护在怀里,小心地出了电梯,贴着墙朝着门的方向缓缓移动,每一步都艰难无比。
只剩几步了,对方几个人已露出了愤怒失望的神色。
就在这时,唐果做出了让她后悔一生的举动。
她怀里的洋娃娃不小心掉落在地上,走了几步才发现,唐果下意识地挣开程时,低着头往回跑,弯腰捡起了那个洋娃娃。
那个淡黄头发,粉红裙子的洋娃娃,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蓝色的大眼睛像水晶剔透。
唐果拾起那个娃娃,听到了身后程时焦急的大喊声,这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晚了。
几个人扑上来,一把拽住唐果的头发,举枪对着她的头。
唐果感觉到冰冷的枪管贴在头皮上,沿着头骨传来一阵冰凉的战栗,她吓得一动不敢动,只闭上眼不停地尖叫着。
程时露出了绝望的神色,他身前的那个人微笑了起来。
举枪对着唐果的那个人开口了,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程时,快放下枪吧。”
程时低下头沉默,过了一会,他把枪远远地扔在地上,垂下了手臂。
唐果流出泪来,她恨死了自己。
程时身前的那个人一得自由,扶着肩膀跳开了几步。他捡起程时扔下的枪,恨恨的说:“臭小子,跪下来!”
程时低着头,仿佛没有听到。
那人毫不犹豫地冲着程时的腿开了一枪,程时发出了一声低声呻吟,可还是勉力站着没有倒下。
那人又要开枪,身边的人阻止了他:“行了行了, 别把他弄死了。”
那人一脸的不爽:“这小子弄断了我胳膊!”他恨恨地放下手,怒视了程时一眼:“便宜了这臭小子。”
唐果的泪快要流干了,她紧紧咬着嘴唇,鲜血混着眼泪流下来。
几个人走上前把程时的双手绑到身后,嘴上不干不净地骂着,手上也小动作不断。
程时任他们摆布,被推搡得摇摇晃晃,一双清澈的眼睛却穿过人群,眨也不眨地看着唐果,然后慢慢地笑了。
他温和地笑着说:“小猴子,别哭了,我不怪你。”
唐果的眼泪更汹涌地流下来,滚烫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怀里洋娃娃的脸上,那双蓝水晶般的眼睛忽然盛满了悲哀,宛若在无声地哭泣。
接下来的一切犹如一场梦魇,那是一场怎样哭叫、怎样挣扎,都无法醒来的梦魇。譬如溺水的人从水底仰望明月,波光荡漾冷月无声,那无力的绝望是水里的每一条波纹,是每一点从指缝流逝的空气。
唐果一直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她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黎明和黄昏,不知道刀疤脸和黄毛小子在哪里。
她又冷又饿,她害怕这没有尽头的黑暗,她想念刀疤脸叼着烟似笑非笑的脸,想念黄毛小子嚣张刻薄的大笑。
这里只有黑暗,令人窒息的黑暗。唐果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潮水的声音,也许是在海边吧。渴得极了,唐果贴到冰冷潮湿的石壁上,舔着那里偶尔滑落下来的水滴,那里散发着浓浓的鱼腥味,唐果的舌头感觉得到滑腻的青苔。
还有洋娃娃,唐果一直紧紧地抱着,死也不肯撒手。曾经有人试图扔了它,手还没有靠近便听见小女孩撕心裂肺扯破喉咙的尖叫,简直像指甲从玻璃上尖锐地划过,那人只好作罢。
唐果在黑暗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怀里的洋娃娃,抚摸她长长的柔软的头发,那是蜂蜜的淡黄色。抚摸她卷曲的浓密的睫毛,那之下的眼睛是天空的碧蓝色。抚摸她蓬松的褶皱的公主裙,那是樱花的粉红色。
唐果紧紧抱着那个小小的洋娃娃,像抱着世间的所有珍宝。
时间漫长得像凝固了一样,唐果在黑暗里睁着恐惧的眼睛,她以为至少过去了一个星期。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地方是码头附近的一个仓库,秦叔是靠贩运水货起家的,那里就是他黑白生意无数的大小地盘中的一个。唐果也没有被囚禁在仓库里一个星期,事实上只有两天,准确的说只有两个夜晚和一个白天,第二天她就被人从仓库里带了出来。
那时唐果又冷又饿,昏昏沉沉地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仓库门打开的时候,光线漏进来,唐果下意识地挡住了眼睛。
门口传来一个没好气的声音:“小鬼,快出来!”
唐果迟疑地站起来,慢慢走过去,那人不耐烦地推了她一把,大声怒道:“磨蹭什么?快点。”
唐果被他推了一个趔趄,却反常地没有回过头怒视他,只是低下头,更紧地抱住了怀里的洋娃娃。
又是一个阴雪天气,正是黎明时分,东方微白,天光半明,清晨的寒风吹乱了唐果的头发,带来一阵阵海水的咸湿味道。
原来真的是在海边啊,唐果想。远处的海水在微弱晨光里呈现出深沉的蓝,近处的海水泛着白沫,翻滚着咆哮着涌上海滩。
唐果被那人推着,一路往那通往码头的木板路走去。窄窄的木板,被海水浸的潮湿而冰凉,脚下是海浪奔腾翻涌。
到了码头的空地上,那人故意用力推了唐果一把,看她跌倒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旁边一些人笑着骂他:“这小子,真够缺德的。”
那人还是笑着,倒是一脸的得意,仿佛那是在夸他。
唐果蜷缩着靠在一堆集装箱上,腥咸的味道呛得她难受。她迷迷糊糊地闭着眼睛,寒风一阵阵割在身上,身上却又燥热难当。
她听到有人在不耐烦地说:“怎么这么久,那小子呢?”
“急什么?那小子的腿还不是你给搞的,能走的快吗?”
唐果在昏昏沉沉里猛然睁开了眼睛,光线刺目而模糊,隔了好久她才看清楚,对面几个人正百无聊赖地倚在集装箱上聊天。
“那韩穆会不会来?”
另一人沉默了一会:“谁知道。他总不至于傻到来这找死吧。”
“我想也是。那小子也够狠的,听说在茶楼那捅死了两个,秦叔带的几个人没一个完整回来的。不过听说他也受伤了。”
“再狠也没用,他勾结条子那就是死定了。”
那人迟疑了一下,压低声音:“这事我老觉得不靠谱,他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啊,秦叔这样跟弟兄们说的?”
“是啊,管他靠不靠谱的,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办吧,我可不想像程时那小子一样。”
唐果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是生锈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那些人的话,她只模模糊糊地想着,刀疤脸和黄毛小子要来了么?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两个人推着程时走过来。程时被反绑着双手,他的右腿上,暗红的血迹染红了大半条裤管,大概是没有得到治疗,他皱着眉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得很慢。
身后一人长松了一口气,一脚把他踢在地上:“可算到了。”
程时被踢得跪倒在地上,他试图站起来,可是腿伤无力,只是徒劳。
唐果哭叫着扑上去,环住他的脖子痛哭。
程时看到唐果,脸上现出温和的笑来:“是你啊,小猴子。”
“是我,是我......”唐果哭着说,滚烫的眼泪流进程时的脖子。
身后有人骂骂咧咧地拉起她,把她拎到一边:“行了行了,以后有你们哭的。”
在被强行拉开的一瞬间,唐果的手绝望地在空气中挥舞,声嘶力竭地哭叫着。朦胧的泪眼里,她似乎看到了程时微笑了,他轻声说:“小丫头,乖一点。”
唐果猛地安静下来,她忽然想起了刀疤脸,想起刀疤脸说,“小丫头。”想起他对她说,“在家乖一点。”
想起他说,“我很快会回来。”
唐果仔仔细细擦干了眼泪,擦干净了脸上每一点泪痕。然后仰起头,眼睛还红肿得像桃子,却咧开嘴微微笑了。
她想,刀疤脸,我会很乖,你快回来吧。
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高高的身影远远从木板路那头走过来。
他大步地走着,步伐从容,海风掀起他黑色的西装,衣角翻动犹如飞鸟的翅膀。
有人急忙进了码头里的大厅,通知秦叔。
很快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长相并不凶恶,还有点和善,细看头发已经有了些微花白。
其他人见了他都恭恭敬敬叫了声秦叔,他却没有反应,甚至没有点点头,只凝神望着大步走过来的年轻人。
韩穆停在了不远处,看到跪在地上的程时,一人正用枪抵着他的脑袋。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唤了声:“阿时!”却又生生顿住了脚步,脸上闪过了愤怒的神色。
秦叔微笑起来:“放心,你的好兄弟死不了,只是腿上中了一枪。”
唐果这时叫了起来:“刀疤脸!刀疤脸!”她爬起来就要奔过去,却被身边一个人死死抓住,动弹不得。
韩穆温和地注视着她,眼神里似乎有悲哀。他轻声说了句:“小丫头。”
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唐果突然觉得安下心来,一瞬间她似乎听到了长风呼啸着掠过海面,海鸥盘旋着拍打洁白的翅膀。
她专注地凝视着韩穆,他的脸色更苍白了,黑色的西装在腹部破了个口子,似乎是被利器划破的,里面的白色衬衫血迹斑斑,不知道哪一处是他的血。
唐果突然鼻子又开始发酸,她用尽最大力气控制住了眼泪,直累得身体都在发抖。她想刀疤脸要是知道了,他一定会为她骄傲,一定会揉揉她的头发,温和地说:“小丫头。”
韩穆这时看向秦叔,平静地说道:“我来了,你们要的无非就是我,现在放了他们吧。”
秦叔看着他,眼神居然带一点钦佩,他叹了口气说:“韩穆,你知道我不想这样的。我怀念七年前,阿月还在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像一家人。”
韩穆的眼神抖了一下,没有说话。
“可是阿月死了,你入狱了,一切都变了,我没法像以前那么喜欢你了。”
“阿月......是我对不起她,可是我没有对不起你,不要把阿月扯进来。”
“好吧,虽然我不喜欢你了,可是我觉得你是条汉子,我佩服你,韩穆。”秦叔又叹了口气,“所以我不想让你死在我手上,你明白吗?”
韩穆低下头沉默了一会,然后低低笑了起来。
“我明白,秦叔,但是你也要信守诺言。”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父亲,我和......阿月的父亲。可是这也没有关系,在里面我就想通了。有些东西,不是我的,就永远都不会是我的。”
秦叔的眼神闪动了一下:“我知道,阿穆,我不会食言。”
韩穆低低笑了一声:“有时候我觉得,秦叔,你也很可怜,你和我一样可怜——我们都失去了最爱的人。”
韩穆又看向目次欲裂的程时,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韩穆低声说:“阿时,不要这样,我并不难过。你伤好了后,去找一份干净工作,娶个好女人,好好地活。”
那个中了枪都没有哼过一声的男人闭上了眼,两行泪滑落下来。
韩穆的目光转向还有些迷惑的唐果,他看着她,眼神里仿佛有悲哀闪过。唐果下意识地一抖,终于慢慢地明白过来。
韩穆叹了口气:“小丫头,抱歉把你卷进来。事情结束了你去找你的外婆吧,她现在在你家里等着你回去,她会带你回老家抚养你。你父母已经同意了。”
唐果用力摇起头来,一直忍住的眼泪被摇得纷飞如雨:“不!你带我回去!你带我回去找外婆!我不要一个人去!我会迷路的!”
韩穆的眼神柔和而平静:“你不会的。”
“刀疤脸!不要丢下我!”唐果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宝贝似的举起那个洋娃娃,“看!你送我的洋娃娃我一直带着,从来没有丢掉!你也不要丢下我,刀疤脸......”
韩穆低下头沉默,抬起头时似乎笑了笑。
他摇了摇头,低声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唐果撕心裂肺地大哭着,哭得太用力又剧烈地咳起来,边哭边咳,眼泪和鼻涕一齐流出来,那样子滑稽又可笑,在场却没有一个人笑出来。
韩穆慢慢从后腰掏出一把匕首,正是她会第一次见他时亮出的那把,原来他一直随身带着。
韩穆摩挲着锃亮的刀锋,轻轻说:“这匕首是我送给阿月的,却害死了她。我欠她的,现在可以还给她了。”
他反转匕首对准了自己的心脏,对唐果说:“小丫头,闭上眼睛。”
唐果听话地闭上眼睛,眼泪不停地从紧闭的眼皮下流出来。
然后她听见了程时痛苦的一声大喊,听见了身体倒在地上的声音,沉闷的一声响,像天边的一声闷雷砸在唐果心上。
然后是尸体被扔下水的声音,几个人拍拍手,叹了口气。
然后有人对她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有人在问:“秦叔,这小子呢?”
“也让他走,他的腿算是废了。”秦叔似乎叹了口气。
然后程时温和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小猴子,我带你回家。”
然后他抱起了她,一瘸一拐地走了。
唐果一直听话地闭着眼睛,一直一直闭着眼睛。
直到她感觉到风拂过她的脸颊,如同那人向来冰凉的手指,温柔地擦拭着她的眼泪。唐果终于睁开了眼睛。
海面的尽头,一轮红日已然跃出,生机勃勃。
后来,唐果长大了,她嫁人结婚生子。
再后来,唐果的孩子也长大了,她看着他娶妻结婚生子。
直到最后,唐果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她一直忘不掉那轮海面上的红日,那么红,那么圆,那么美丽。
唐果再也没见到过程时。她不知道他去了哪个城市,那里是否有一样的海。她也不知道他娶了什么样的女人,她笑起来是否如同夏日的阳光。
那个早上,程时把唐果送到了家门口,拍拍唐果的脑袋,欲言又止。
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眼里有一样的悲伤。
程时后来沉默地离去了,他一瘸一拐的背影看起来滑稽而可笑。
他只对唐果说了一句话:“好好活着。”
唐果知道,那句话程时也在对自己说。那是韩穆最后的愿望,他们俩都好好活着。
唐果的那对父母端坐在家中,看到唐果,脸上竟然有一丝敬畏。唐果不知道韩穆做了什么,想必把这对平凡的男女吓住了,他们一生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偷情,随后就又陷入了与上一段婚姻无异的琐碎之中。
他们不认识一样盯着她,平凡的脸上闪着惊异的光,可能还有一丝嫉妒。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年轻人为了带走唐果,留给了他们一大笔钱。他们上下打量着这个瘦巴巴的小女孩,不明白她有什么地方出奇。
唐果在里屋收拾着东西,隐约听到外面他们小声的对话。
“也说不定,有人就喜欢这种小的。”
“有可能,看他的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人。”
唐果出来后,他们立刻闭上了嘴,神色里却带有了一点鄙夷。
很多年后,唐果不知怎么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她想着那对所谓的父母,他们的脸她已经记不清了,她却忍不住慢慢伏到水池边,干呕起来。
那时唐果的外婆愤怒地盯着他们,然后抓住唐果的手,头也不回离开了这个家。
韩穆也给了唐果的外婆一笔钱。外婆有一次跟唐果提起,那数目唐果都有些不敢相信。她有时恶意地想着,如果她的那对父母知道了,抚养她竟要比卖掉她还要值钱,他们大概会后悔而死。
后来,唐果的外婆病重时,有一次她拉着坐在床边的唐果的手,有些悲哀地凝视着孙女:“丫头,你的命不好。但是你遇到了贵人。”
唐果愣愣地看着躺在床上的老人,她苍老疲惫得仿佛即将死去,向来昏花的老眼却熠熠闪着光。
“那个年轻人,他是个好人。”
唐果一直相信这句话。
end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