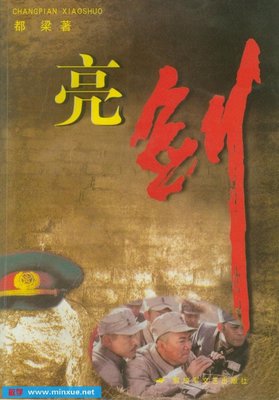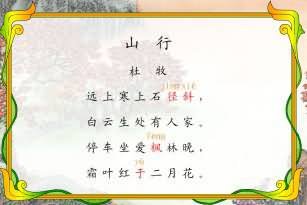荒诞小说《大师行》(之一)——行路难
秋高气爽,孔丘约了正在泰山旅游的鲁迅、闻一多两位先生,让颜回、子路等几个弟子套上牛车,从曲阜出发,一路往西,欲至河南面唔老子,庄子,探讨一些哲学问题。
谁想刚刚到了菏泽,便被一交警拦下。那交警训斥道:“谁是驾驶员?这儿条条道路都是高速,而且这会儿正有一队HC赛车通过,连时速达不到200麦的汽车都不允许行驶,就你们这破烂货也敢上来么?驾照拿来!”
颜回愕然,答曰:“何为驾照?观汝神态,似乎气势汹汹,无礼也!须知: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汝无礼即非爱人,即不仁!不仁者岂可当道?!”
那交警听不大懂他话里的全部意思,但“爱人”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便笑着说:“你这个老头倒新潮得很,满口‘爱人、爱人’的,也不嫌寒碜。别跟我绕弯子,快把驾照拿出来!告诉你,我们大队长的小蜜——就是你说的‘爱人’,这两天正跟他闹,逼着他离婚,所以他心情不好。在这个时候我要不把你们这事处理好了,那这个月的奖金还不泡汤?”
子路本性耿直,且孔武有力,上前一把推开那个交警,说:“昔日吾师领弟子周游列国,难堪亦不过于缺食,尝未见有阻于道者,且索要‘驾照’。莫非确如吾师所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乎’?
那交警更不懂他说了些什么,不耐烦地说道:“要去海上玩,去日照、连云港、青岛,那里海滨浴场多的是,美女如云,还可以租游艇。如果想在这高速上赶牛车,没门!没学过《道路交通安全法》吗?上路不带驾照属于无证驾驶,是要拘留的,懂吗!”
坐在车棚里的闻一多本来不想说话,此时听这个交警说出一个“法”字来,还说要拘留云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跃身而出,指着那个交警训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百姓爱走哪条就哪条,你管的着吗?蒋介石不给人民自由,难道你也要学他吗?告诉你,凡是与人民为敌的,终究要被人民埋葬……”
他这边话还没说完,高速公路上一阵电闪雷鸣,十几辆形状各异的赛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见有一堆人和一个破牛车档路,纷纷紧急制动,刹车“叽叽”地给踩得一片山响。继而十几个红男绿女跳下车,围拢过来想看个究竟。
还没等他们过来,鲁迅已经将闻一多拉回至车上,然后用他那一贯的饱含哲理的语言对交警说道:“你们口口声声说‘道路’,还有什么‘安全法’。你懂什么是路么?其实地上本没有所谓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
“呀!是鲁迅!嗨,爱德华夏,韩寒,那是‘中国革命的文化旗手’鲁迅吔!”红男绿女队伍中有几个人兴奋地嚷了起来。因为在上小学的时候,课本上面还有这个老夫子的画像,他们还没有完全忘记。
“瞎嚷嚷什么!不就是鲁迅吗!”被称作韩寒的那个人将头向侧后一甩,一头青丝便如同雄狮的鬃毛往后飘去,这才露出亦狮亦马、酷的无法形容的面孔。旁边几个穿着吊带裙、露出大半个乳房和臀部的女“粉丝”见了,均“哇塞!”一声,赞叹不已。
就见那个叫韩(寒)之又寒的用冷酷逼人的“秋波”将所有人打量了一遍,然后嘲笑道:“坐在最里面的可能就是孔圣人吧。你最兴旺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到处推销你的儒学,而后一毁于秦皇,再败于文革,现在又有人把你抬出来了。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那是用你来骗钱的。所以,上下五千年的所谓中华文化统统要扫除干净,否则崭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就无法生根发芽。”
听了这话,孔老夫子低眉垂首,淡淡地嘀咕了一句:“无源之水?”鲁迅却连眼皮也未抬,图未穷匕首已现:“那么你是谁?今日之狄克么?”
韩寒尚未答话,那个叫“爱德华夏”的已经大为不满,嚎叫道:“你连他也不知道?可见你们这些人孤陋寡闻。他叫韩寒,当今青年的杰出代表!你不就是鲁迅吗,有什么了不起?你当年虽说有‘旗手’之誉,但那是虚名,还不是住在亭子间里,靠稿费吃饭?你有传媒公司吗?你开过宝马吗?敢赛车吗?”
![[转载]荒诞小说《大师行》(四篇) 转载 小小说投稿邮箱](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41031t01ac8131544f999433.jpg)
鲁迅微微一笑,不再理睬他们,而是对闻一多道:“秋白当年曾预言:试看明日世界,必是赤旗之天下。大谬不然矣!我的阿Q似乎比他们还要好些。”
闻一多颔首称是,愤愤然说道:“一群声色犬马之徒,白白地叫我等挨了国民党的子弹!”
“两位先生差矣!”一个声音遥遥地从北边传来,看那个方位,应当是刚刚开挖不久的曹操墓:“孤千余年前已有名言——世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此之谓也!”
那个交警观颜察色,见至高无上的孔圣人和大名鼎鼎的文化旗手都搞不过这个年轻人,便走过去拍了拍韩寒的肩膀,不无嫉妒地说:“怪不得有那么多MM为你尖声嗷叫,果然是厉害!”
他话没说完,就见又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至,刚刚停稳,车上下来一个穿便服的胖子,不问三七二十一,冲那个交警吼道:“这都是干什么的?嗯?在路上堵了这么长时间你都解决不了?非得要老子把私事丢下来替你处理?”
“大队长,这几个人是……”
“管他是什么人,统统带回大队部,该扣车的扣车,该罚款的罚款!听见了吗?”
……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荒诞小说《大师行》(之二)——做人难
却说扣牛车和赛车的时候,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没问清楚,及至回到了队部才知道,被扣押来的人中既有千古之圣人又有近代之文豪,还有名噪华夏的青年才俊,不由得慌了神,连忙启动应急预案向局里、并通过局里向市里汇报。
市里一听,了不得!一面报告正在秋季土地拍卖会现场亲自坐镇的市长,一面通知电视台、市文联、作协等单位。
要说还是新闻媒体反应来得快,没用几分钟,一辆实况转播车呼啸而至。然而,刚刚现场直播了四十六秒,市长的电话来了,命令交管局立即护送这些先生们去市里最大的一家宾馆,市长将在那儿与他们亲切会见。于是,实况转播不得不暂停而忙着转移设备。
现代社会快捷的电讯网络早已将时间和空间压缩至最小化。仅仅四六十秒的实况转播,嗅觉灵敏者就能从中捕捉到千载难逢、再一次表现自己的绝佳良机。分别身在北京、上海的于丹、余秋雨二位立即推掉了充当形象大使,去某地剪彩、演讲的小事情,乘最早的班机直扑目的地。
再说那一行人进了富丽堂皇的宾馆后,孔老夫子倒还好,虽然坐在真皮沙发里感觉身子直往下沉,无法正襟危坐,与他一生倡导的“礼”不合,但还是能坐住了。闻一多是个爽快人,不讲究那么多。鲁迅却是不容苟且,只见他用左手食、中二指将香烟从嘴上移开,淡淡地问道:“有藤椅么?我看书,写字,会客历来都是坐藤椅的。”
就在宾馆的总经理忙着去找藤椅的时候,文联、作协的主席都到了。寒暄了几句,气氛有些冷淡。作协的主席便偷空悄悄地问文联主席:“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闻一多,鲁迅等人,闻一多戴的眼镜镜框应该是黑色珐琅架,现在怎么变成金丝的?鲁迅的头发历来是短而平,如今怎么也留起了长发,有点大背头的样子?莫非是有人化装了出来行骗的?现在超级大骗子可到处都有。”
“哈哈、哈哈哈哈!”文联主席还未回话,一旁的韩寒已是放声大笑。毕竟人家年轻,耳朵好使,作协主席刚才说的一番话给他听得清清楚楚。就见他又是将头向侧后一甩,还没等那几个穿吊带裙的MM喊“哇塞”便训斥道:“按照现代男人的标准,镜框、发型都需要经常变换,不然就无法满足与时俱进的要求。至于他们是否是别人化装的,我现在就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不是!他们是穿越来的,“穿越”懂吗?如果不懂,建议你上网去好好地看一看玄幻小说。”
稍停了一小会儿,见那个作协主席眼睛眨巴着,一脸不服气的样子,韩寒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咆哮般地吼道:“我早就说过,所谓作协只是一个摆设,它对繁荣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不仅起不到一丝一毫的作用,相反,它无所作为,还压制新生力量,就偏爱那几张不死不活的老面孔。因此,所有的作协应当全部取消!”
“那可不行。”正在这时,市长带着市政府秘书长和一个贴身女秘书进来,恰好听见,连忙纠正道:“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触及到的领域不可随意取舍,改革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以为改革完成了,其过程任重而道远。”
听了这些模凌两可的话,鲁迅立刻以他那辛辣的语句讽刺道:“呵呵,改革,改改革,改改改革,改……”。
市长不知是没听懂鲁迅的嘲讽,还是假装没听见,抢上前来与孔老夫子及其弟子热烈握手,表示欢迎。
然而,孔丘从来没有握手的习惯,仍是双手拢在袖子里,艰难地要从沙发上起身还礼,因为“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但他几经挣扎仍然无果,反而歪到在沙发上。子路急忙俯身把他扶起。颜回则面向市长恭立良久,代师回礼,答曰:“令尹治下,宋国之疆土,礼仪之邦。然襄公愚,谬解仁义,兵败,丧。”
市长根本就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鸟语,却又不能露出一点都不明白的样子,无奈之下一屁股坐在颜回对面的单人沙发上,没话找话地说:“今天天……”
谁知他话未说完,鲁迅便接着道:“‘今天天气……哈哈哈!’这是我几十年前在文章中便写出来的句子,不信你可查阅我的文集。”
那市长给噎的半天讲不出话来,但人家久经官场,经常给领导熊得灰头土脸,什么世面没见过?所以很快便缓过颜色来,接过笑声“哈哈哈”一串干笑后,略微回头吩咐秘书长道:“酒宴就安排在宇宙厅,座位要够三十人坐的,完了你签一下单。”
秘书长刚刚转身要去布置任务,就听一直没说话的闻一多突兀问市长道:“听阁下话里的意思,是要请我们喝酒吃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岂能没有酒饭乎!”这前半句话还是前两天跟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学的,此刻现学现卖,在这么多文豪面前拽了回文,市长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可是,闻一多的脸色开始阴沉下来,一句一顿地问道:“请问,这酒席的花费是国库支出还是你私人掏腰包?”
“啊?啊……”
为市长解脱窘境的是于丹教授。
本来,于丹和余秋雨几乎同时到达,在宾馆大门前略一寒暄,余秋雨便止住了脚步。因为他想,即使是现在他已经是厅局级的官员,据闻已有风声,最近就有可能宣布他担任文化部部长。那么,在这个小地方,就算圣人、前辈文豪自重身份,当地的官员也该出来迎接吧,你那个小小的市长够厅局级吗?他这么一摆架子,便给了于丹抢先一步的机会。
于丹这几年在百家讲坛练就了一副好嗓子(虽然普通话说的不太标准且后鼻音咬得太重),还掌握了极好的与听众互动的技巧。因此她一进来就笑靥如花,大呼小叫道:“老夫子呀,您老人家重返神州真是太好啦!您见到我在百家讲坛讲解您的大作《论语》了吗?”
孔老夫子刚才在沙发上歪了一下,他年纪大了,便觉得腰背不怎么舒服,要不是讲究个“礼”字,他早就想躺倒睡一觉。再说,《论语》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的语录编纂而成,他老人家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一说。现在听这女人如此问,便一头雾水,瞠目结舌。
于丹见这老夫子不仅不答话,反而张口结舌地盯着她胸口看,(她喜欢里面穿一件低胸的背心,外面套一件短袖)就觉得圣人亦不是全无七情六欲,正所谓“食色,性也。”但也不能让他就这样一直看下去,正好宾馆服务员给她送上来一杯茶,她便以茶说事,来岔开话题。就听她说道:“各位请喝茶!这‘茶’字拆开来,就是‘人’在‘草’‘木’之间,寄情山水,令人心旷神怡。于此境地读书悟道那是何等的美妙!读书是要用心的,所以,一个竖心旁加‘吾’才是悟……”
“啊!噗!”听到这儿,鲁迅将刚刚喝进嘴里的一口茶笑得全喷吐了出来,然后手抚胸口,半天才缓过气来,却笑对闻一多说:“我怎么感觉心里闷得慌……”
“‘闷’是‘心’在‘门’中,有压抑感,出去走走就好了。”于丹紧接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闻一多至此也不禁仰天大笑,好不容易止住了,这才笑着问于丹道:“按你的说法,‘茶、悟、闷’三个字都是会意字了?”
“是。会意有时候就是意会,比如《论语》中有些内容只有靠‘意会’方可解释。”
“请问,女士现在供职何处?”
于丹还没说话,旁边一个服务员抢着答道:“于丹老师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可有水平呐!我们都是她的粉丝呢。”
闻一多听了与鲁迅对视一眼,又摇摇头,但还是忍不住地对于丹说道:“有时间应当去看一看《说文解字》,六书中就有答案。那三个字不是会意字,而是……”
“那明显是形声字嘛!”余秋雨在门外等了半天也没人去迎接他,只好带着秘书悻悻地踱了进来,接过闻一多的话便高谈阔论起来。
就见他西装革履,右手稍微举了一下,算是向众人打了招呼,就差“哈罗”没喊出口,然后优雅地将西装往两边一掀,露出捐献灾区后剩下的尾款买的金丝利皮带,一副“大师”的派头,大刀金马地坐了,接着道:“六书主要是讲字的,字都认不清楚怎么读书?这些其实应该在小学、最多是在中学就必须做完的功课。”
“哼哼,那也不尽然,譬如我,到晚年却也没离开过那本康熙字典。”鲁迅抬头望着天花板说。
一丝阴冷的寒光从余秋雨那副价值几千元的眼镜片里射出。但说话的人是公认的文豪,无可奈何,他只好装着没听见,继续发表高论:“到了大学,就要讲究读书。我在台湾高雄大学演讲时就说过,‘阅读最大的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
“学而时习之,悦乎!求知,知礼,后治国平天下。”子路不知道怎么也能听懂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大师”的语言,出声驳斥道。
闻一多鉴于适才那个女人搞不清六书的经验,生怕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听不懂子路的文言,连忙解释道:“他的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为了求得知识,懂得礼仪和道理,然后才能去为天下人做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平庸’。”
“倘若瓦匠、木匠读建筑学,那是为了将房屋盖得更好,以此换来钱粮养活一家老小,却还是‘平庸’。他也感觉不到‘外部世界的精彩’,因为明天还要拼命地干活。更感觉不到‘生命涵义的丰富’,和‘人类历史的厚重’,倒是将那些泥土堆砌成墙,他才感觉十分沉重。”鲁迅说到这儿,意犹未尽,继续说道:“当今青年,与那些自封为‘导师’、‘大师’的人须十分地注意,那些人的‘教导’愈是‘高雅’、晦涩、神秘,愈说明其内在空洞无物,自相矛盾,将其剥开来看一文不值。”
“噢!‘大师’丢丑喽!原来‘一文不值’呀!”那帮赛车手中有几个人幸灾乐祸,乘机起哄。
“走了走了!就听几个老家伙在这儿扯来扯去,一点意思也没有!”韩寒说完,跟谁也不打招呼,领着那些红男绿女扬长而去。出大门时,他可能又是将头向侧后一甩,那毕酷的姿态惹得粉丝们“哇塞”的赞叹声在宾馆大厅里久久地回荡。
……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荒诞小说《大师行》(之三)——说话难
因为闻一多、鲁迅坚持不吃“嗟来之食”,把那个平时处理事情果断干脆的市长也急得没办法。闻一多见他为难,便从衣袋中掏出几张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面值都是千元的,说:“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不过身上也就有这点钱,虽然是几千,但按当时的市值只能买两斤大饼。估计几个人也够吃的了。”
余秋雨见了,灵机一动,上前便将那几张金圆券接了过来,然后吩咐他的秘书道:“让当地政府出示账号,从网上划五千块给他们,今天这顿饭我和闻先生共同出资请客了。”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于丹却将头别向一边,满脸不屑地说:“去北京的古玩收藏市场,一张千元面值的金圆券可以卖到十万。不动声色间几十万赚到手,真是敛财有术啊!”
余秋雨听见了急忙过去,趁别人都还没注意,悄悄地塞了一张给她,笑着说:“大家都是想搞点收藏品嘛,难道你我还缺钱?”
……
于是,大伙去餐厅就餐,吃的是四菜一汤的份饭。现代的菜肴比战国时要好多了,孔老夫子与他的两个弟子讲究“饭不语”,不像其他人一边吃一边还说上两句,所以最先吃完。老夫子被折腾了一天,腰背酸疼,要找地方睡。宾馆总经理连忙开了贵宾房,亲自领他三人去。鲁迅嘱咐道:“将床上的‘席买思’撤了,就给他睡木板,否则明天老人家会腰疼得起不来。”那总经理先是听不懂“席买思”为何物,待前后一联想便知是“席梦思”音译的不同说法,遂抿嘴一笑,照办去了。
从电视直播开始到他们吃完晚饭,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就在这段时间里,孔丘、鲁迅、闻一多“穿越”的消息早已传遍了世界各地。比于丹、余秋雨嗅觉差些的各路媒体、精英们纷纷紧急行动,运用各种手段赶赴目的地。
七点左右,宾馆大厅里已经汇集了路透社、朝日新闻驻京记者站、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二十多个记者,又过了十分钟,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正在上海看世博会的台湾名人李敖父子,名博、博文产量极高的点石斋、沂蒙星辰等人全到了。大伙找到市长一商量,认为单个、私下的交流已不可能,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搞成记者招待会的模式。
于是,宾馆的大会议室里顿时热闹非凡,布置会场的,记者们架摄影机等设备的,乱成一团。自然,主席台正中特地摆了张藤椅。
八点整,鲁迅、闻一多被人左劝右拉地在主席台就坐,余秋雨老实不客气地坐在了鲁迅的右边,于丹则临时充当了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首先发问:“鲁迅先生,有报道说,有关部门将要把您的文章从小学、中学的课本里撤出。对此请问您有何感想?”
“我那几篇小东西,从来都是正人君子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鲁迅双目炯炯地接着道:“何况现在是歌舞升平的时代,不再需要匕首和投枪。阿Q们都已经成了赵老太爷,也不会再有祥林嫂,因为假设还有那种境况,这类人物是有去处的。”
“请问鲁迅先生,假如还遇到那样的困难,她们能去哪儿呢?”
鲁迅尚未答话,名博点石斋先生已接口道:“今早六点整我发了一篇博文,题目就是《少妇更丰韵美妙的奥秘》,你看了就知道,她们既可傍大款,又可以去酒吧,‘天上人间’之类的,最不济还有浴室、发廊,收入不会低。”
“连鲁迅先生自己都这样说,可见社会是进步了。”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是著名学者,最听不得低级趣味的语言,就见他叉开右手的食、中二指,将因为皱眉头而滑落下来的眼镜往上推了推,说道:“我主张,中、小学课本里,不仅鲁迅的文章要取消,就是古文也不要编进去,因为那是‘死文字’。”
“哇!吽!”大厅顿时一片哗然,闻一多虽然脸涨得通红,但还是忍住了。李敖历来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闻言拍案而起,却给点石斋拦住了。就听点石斋问葛红兵道:“您的意思是铲除‘死文字’,创造新文字?”
“对,鲁迅先生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提出,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字。”葛红兵说完瞥了鲁迅一眼。
“其实,鲁迅先生的主张建国后已经实施,比如汉语拼音,比如简化字”。点石斋说到这儿话锋一转:“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现在就实行起来,恐怕就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您先生姓‘葛’,声母是‘G’,您大名的声母分别是‘H’和‘B’。但如此一来问题就多了。大家知道,汉字的约定俗成还没到那种程度,仅仅说出声母便能明白其意思,还要与韵母拼起来方能有准确的表义。假如将‘G’与‘OU’搭配,便读‘狗’,而声母‘H’、‘B’能够搭配的韵母就太多了,我们可以将先生您的贵姓大名读成‘狗红鞭’,又能读成‘狗胡掰’,这究竟哪一个是准确的呢?”
“哈哈哈哈……”所有人都被点石斋的妙语逗得哄堂大笑,笑声稍歇,另一个名博沂蒙星辰补充道:“何况,按照现在大家认可的约定俗成,声母‘B’可让人产生许多联想……比如‘傻B’,‘呆B’等等,如此搭配,不知是‘死文字’还是活文字?”
“庶子不足与语!”葛红兵情急之下,中学时学的一句古文脱口而出。
“哎!你刚才说的不正是‘死文字’吗?一个记者毫不留情。
“可见,无端编织绳索的,终究要被绳索勒死。”鲁迅又点燃了一根烟,身子往藤椅的椅背上靠去。
“哗……”顿时,大厅里响彻一片掌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荒诞小说《大师行》(之四)——挖祖坟也难
闻一多刚才没能说话,此时等大厅里稍微安静了一些,便语重心长地说道:“按道理说,我们这些过去的人管不了现在的事。然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他的文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不学这些还能学什么?我倒是不得而知……”
“对!鲁迅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将这个脊梁摧毁了,想让中国人挺不起腰杆吗?其居心何其毒也!”李敖拍案而起,怒目圆睁。“另外,哪个说古文是‘死文字’?司马迁的《史记》、唐诗宋词都是‘死文字’写出来的?你用‘活文字’写给我看看!要我说,应该全民公决,我敢保证,全国人民每人一口唾沫,不把说这话的人淹死才怪!要是放在台湾,‘红衫军’说不定已经把那个人的住宅包围的水泄不通了。这简直就是第二个阿扁么!想搞‘去中国化’?形式不同,本质一样嘛!”
“所以。”余秋雨不会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接过话来说道:“我在青歌赛上多次提醒选手注意,必须注重历史的厚重,自身文化程度的修养……”
谁知他话没说完,大厅里一片哗然。“就会到处卖弄。”“喧宾夺主!”等议论声不绝于耳,人人似乎像吃了苍蝇。
凤凰网的一个美女记者站出来提问道:“我想提几个问题请余先生回答。一,有报道说,你捐献给灾区希望小学的款子根本就没到账……”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我的律师。”
“好。第二,据说您是学戏剧出身的,但至今我们没看见您有一部戏剧作品,请问……”
“我把精力都用在戏剧理论和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上了。”
“那么第三,有文章披露说,你当年曾是张春桥在上海写作班子中的重要成员,是吗?”
“恐怕未必是真的吧。”鲁迅一生实事求是,看人精准,就听他接着说道:“虽说张春桥当年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过我,但那是政见之争,小张的理论修养和文字水平还是很高的嘛。以小张的眼界能看得上他这样的绣花枕头?”说完,鲁迅气呼呼地站起身,自己把藤椅搬到会议室的门口坐下,连续吸了几口烟。那神态似乎是说:我鲁迅岂能与伪君子为伍!
“岂有此理!”余大师知道再坐下去更下不了台,借此机会假装怒气冲冲,拂袖而去——反正那几张金圆券已经在腰包里了。
如此一来便有些冷场,点石斋正欲旧话重提,不想朝日新闻的记者抢了先。
就见那个矮个子日本人操一口流利的、略带点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向葛红兵道:“教授先生,您无与伦比的才华令人倾倒。您会书画,还能写小说,懂外语,搞翻译,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博导。您真是当今中国文化界屈指可数的精英!”
“谬蒙夸奖!”葛红兵谦虚道。
“这个‘谬’字似乎也是‘死文字’。倘若用当今的‘活文字’该如何说?”鲁迅问道。
“这……”
别说鲁迅就是厉害,如此一个简单的问题便令“精英”张口结舌。
那个矮个子小日本见葛红兵一脸窘态,杖着他自小便学中文的功底,插上来说:“‘谬’就是错误的意思,这有什么难解的呢。”
闻一多一生最恨日本人,闻言立即反唇相讥道:“乌鸦也会唱歌。照你的解释,那么‘谬蒙夸奖’便应该解释为‘承蒙错误的夸奖’。既然如此,你前头所说的一大堆话都是‘错误’的,而你明知是‘错误’的却用来‘夸奖’人,岂不是恶意的嘲讽?”
“不愧是前辈文豪!”李敖赞道:“闻此言直比浮一大白还要让人舒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即使是一字一句也蕴含着高深和无穷的变化,岂是尔等撮尔小邦之流所能知!”
“小鬼子,滚回你那小岛上去!”“到靖国神社哭去吧!”在众人的嘲笑、呵斥声中,那个朝日新闻的小矮子知道众怒难犯,悄悄地躲到人群后面去了。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乏“勇敢”者。连日本人都知道退避三舍,葛“精英”却站出来打抱不平了:“不要老拿靖国神社说事,人家参拜,其实是祭奠他们的老祖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不要总记得日本曾经侵略过我们,其实耻辱的是他们,这就像一个人无端地去打另一个人,真正的耻辱者应该是打人的人,而被打的人似乎也没必要老是记着仇恨……”
因为那个人走了,所以鲁迅的藤椅又给人搬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他听“精英”如此说,不禁把烟从嘴上移开,转头问闻一多道:“过去的事情记不大清楚了,当年华北自治委员会、满洲国以及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里有姓葛的么?”
“哈哈哈哈哈哈!”这边闻一多还未回答,那边李敖已是怒极反笑。笑声一停,他“忽”地起身,手指着葛“精英”问道:“按照你的逻辑,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只是‘耻辱’,而被杀的人还不能记住仇恨,对吗?”
“真正的耻辱者就是侵略者,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感到羞愧。”“精英”答道。
“他们的子孙‘羞愧’的正在钓鱼岛撞我们的渔船、扣押我们的船长!”沂蒙星辰插上来说道。
李敖向沂蒙星辰点点头,接着对“精英”说:“好,就按你这个逻辑我们不妨来做一番推理和假设——假设有一伙强盗闯进你家里,打杀抢劫一番后还把你的姐妹、妻子甚至你老妈都奸污了,然后扬长而去——那么,‘耻辱’的是他们,而你是‘没必要记住仇恨的’。是吗?”
“你怎么骂人?”
“骂你还是轻的,不骂你不清醒!”“这种人骂有什么用,枪毙算了!”一时间,大厅里七嘴八舌,记者们也都激怒了。
“告诉你,侵略是犯罪,那叫罪恶!”李敖义愤填膺,继续道:“把罪恶与耻辱混为一谈,企图偷换概念,你以为自己真的是精英,把其他人都当成傻瓜?专作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我就不明白,大陆当局怎么会容忍这些败类!难道上海大学挂的是太阳旗吗!”
“可惜,文革时你不在大陆,不然,你李先生或许就是现代的伍子胥……”
“慢点,慢点。”点石斋起身说道:“葛教授刚才好像是说‘伍子胥’对吧?但你那一口洋径浜的苏北口音太重,让人听得费力。我来教你一个法子——你用手紧捂着嘴,连续大声说十句‘伍子胥’,问题就解决了。
他这么一弄,不要说葛红兵茫然不解,就是其他人也糊里糊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怎么,那些混账话都敢说,这区区的三个字不敢念?”
“有什么不敢!”葛“精英”将鼻梁上的眼镜又往上推了推,顺势用手捂嘴就念了起来“伍子胥,伍子胥……捂着……”
“哦!啊!哈哈……”大厅里顿时笑倒一片。沂蒙星辰故意问点石斋:“我怎么听到后来,就听他念成‘捂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应该是在女性的腰部以下的呀。难道他捂着的不是嘴,而是……那个东西?”
至此,连一贯严肃的鲁迅和闻一多亦不禁莞尔,鲁迅笑着对闻一多说:“上下颠倒,阴阳不分,这混沌的世界啊!”
闻一多颔首答道:“看来,我们这次‘穿越’与孔老夫子欲去找老子、庄子探讨哲学问题一样,全是多余的了。走吧,眼不见为净,还是‘穿越’回去的好。”说完,他二人起身便行。
“哎!二位怎么就走了?”一位记者喊道:“最后一个问题,鲁迅先生,您对现在挖祖坟的这些人宽恕吗?”
“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的回答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