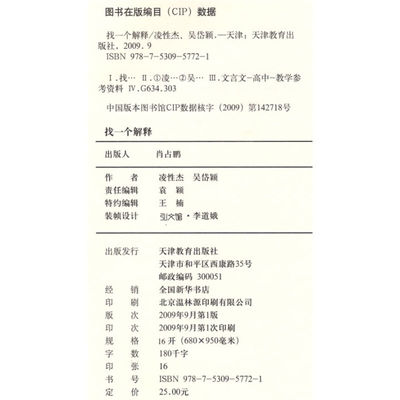这部作品的诞生可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作品的指挥家和创意人郑小瑛说:
“天时”者,是事件发生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我的父亲是龙岩地区永定县的客家人,90多年前从山区的小径走出去求学后,与老家联系不多,因而我不觉得自己是客家人。2000年2月我与妹妹郑小维、妹夫葛顺中到闽西永定偈祖寻根时,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参观了曾被美国的地球卫星误认为是密布在闽西山区的导弹发射井的客家土楼。当我走近那些沿着山涧小溪修建的密密麻麻的土楼,看到它们是只有一扇大寨门和上半部才有一些小窗户的雄伟敦实的庞然圆形大堡时,我的内心产生一种疑惑,在这样封闭的土堡里人们怎么————生活?可是当我走进那扇大门,迎面看到的是大天井里灿烂的阳光,是祖厅里和厅堂两侧高悬着的各式满含我中华文化特色的庄严的楹联和匾额,天井里的几口古井可在被盗贼围困的情况下,为聚族而居的几百口人提供生存必需的饮水,环绕在我四周的一、二层楼房是面向豁亮天井的各家的厨房和粮仓,而往上看,高大的、间隔有序的环行三、四楼层,才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屋中向外的小窗,既能采光,又能向外打枪,屋檐下,廊柱上都有精致的雕刻,大门上还有防御土匪火攻的“自来水”灭火装置,有一座土楼里竟先后培养出了受过高等教育和获得博士、教授头衔的100多位知识分子在体现着古雅朴实建筑艺术的土楼里,竟处处体现着厚实的中原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无穷智慧,原来这些客家人的祖先并不是一般概念里的“逃荒者”,也许,他们中更多的是历次改朝换代时持不同政见的“逃亡者”,因而他们才那样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文化;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以永定为代表的土楼正在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告诉我当年11月在龙岩将举行一个世界客家人的代表大会,这可是6000万遍布世界各地的事业有成的客家人的代表们,第一次在它的祖地聚会啊!从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异想:为什么不在那个大会上演出一部“土楼交响乐”呢?
“地利”者,距离龙岩仅仅三个小时汽车路程的厦门已经有了一个交响乐团,虽然它还非常年轻,但由于领导重视,社会支持,经过全团上下2年半的努力,现在已能基本胜任一般中国新作品的演奏;因而只要有作品,就能方便地在龙岩奏响了。试想,如果要说服闽西山区的领导人去遥远的外地请一个乐团来演奏交响乐,恐怕就不大可能了。然而,事在人为,最要紧的还是“人和”:运气来了!知道了我这心愿的一位资深记者杨力同志正好认识香港崇正客属总会会长、世界客家研究会会长郑赤琰夫妇,她向他们极力宣传我为客家人大会设计的“精彩壮举”,后来又得到了崇正总会理事长黄石华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和龙岩市领导的欢迎,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作曲家!谁最合适呢?

我期待着一部既能满足乐队演奏员和专业听众要求“出新”的审美要求,更要能被许多可能是第一次欣赏交响乐的客家山区听众喜爱的作品。这时,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副教授葛顺中向我极力推荐他所了解的刘湲,接着,在第一次与刘湲的长时间通话之后,我就认为此曲的创作非他莫属了:因为在曾那里度过少儿时光的闽西客家地区几乎就是他的故乡,他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喜爱它的山山水水,特别是他也赞成音乐应当是“受听的”..成了!正好郑赤琰教授经厦门赴龙岩参加筹备大会的事务,对于作曲家的人选,我们一拍即合,激动得在饭桌上就给刘湲打电话,要他马上从上海飞来,匆匆忙忙的刘湲到了机场才发现没带身份证,于是又跑回去了一趟,等他赶到厦门,已是半夜了。郑教授与刘湲一见如故,送给他许多从香港带来的资料和山歌录音带,他们兴奋地连夜畅谈客家历史,客家精神,第二天结伴驱车同访永定土楼,当地的同志热情地向他们展示了客家特有的,在大锣大鼓伴奏下的舞狮耍龙,他们还欣赏了能唱18种曲调、一千多首歌词的74岁“闽西山歌王”那苍劲高亢的客家山歌,听到了用树叶吹奏的清脆悠远的客家旋律,加上那从山谷一直绵延到山顶的,沉积着厚厚的中原文化的客家土楼群给作曲家心灵的震撼和冲击,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创作冲动在他胸中油然而生,我想这正是他落笔时“乐思奔涌、下笔顺畅、神清气爽、状态奇佳”的根本原因吧。旅居海外第二代的客家老人郑教授也站在山头上无限感慨地唱起了从父辈那里学来的山歌,他脱口而出:这部作品就叫〈土楼回响〉吧,这是古老的客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回响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