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千年一叹》题跋
一
“读了几篇余秋雨的文章,张口闭口就是文明、文化,仿佛你就是余秋雨似的!”多年以前,一位貌似很铁的朋友向我发难道。
“去了一趟敦煌,又去了一趟平遥,回来后,张口闭口就是余秋雨怎么说余秋雨怎么说,好像余秋雨是你家二哥一样!”多年以前,一位火热心肠的同事曾经这样嘲笑过我。
微微一笑,算是回应。回应之后,心中难免有一丝酸楚与悸痛。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周围,很多貌似有文化的人,都以非难余秋雨为乐事;或许因为距离过去遥远的缘故吧,还有一些貌似很有文化的人,便转身非难余秋雨的读者,且以此为乐。
其实,这些人并不懂余秋雨,或者说没有读懂余秋雨。
二
一位学者,在做行政管理工作方面,在做专业学问方面,均已达到人生的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却能够断然割舍尘世间的挂碍,拂一拂衣袖,抽身从深深学院和静静书斋中走出来,走向自然,走向大漠,走向洪荒,走向残垣废墟,用脚步去实地丈量历代文明的尺度,用眼睛去打量和寻觅世界文明的壮美,用心灵去叩击与碰撞史前文明的圆缺……跋涉数万公里,纵横数十国度,伏下身心,去体验寰球的凉热;舍得,放下,阅读,行走,探究,写作……这样的一位学者,遍寻十亿国人,搜索千万教授,几人能够做到?只有余秋雨,唯有余秋雨,一人而已。
三
新旧世纪之交,余秋雨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节目组旅次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时候,凤凰卫视台长王纪言先生请余秋雨为此次旅程写一首主题歌。余秋雨徘徊在两米直径的弹坑面前,略一思忖,拟就一首歌词道: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车轮滚滚尘飞扬,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昆仑的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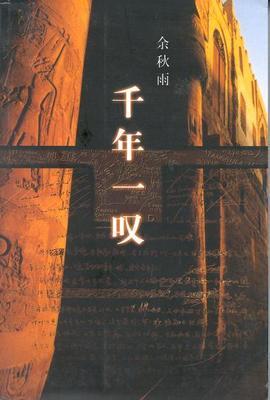
我是黄河的浪,
我是涅槃的凤凰在飞翔。
法老的陵墓,
巴比伦的墙,
希腊海滨夜潮起,
耶路撒冷秋风凉。
我是废墟的泪,
我是隔代的伤,
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屈原的梦,
我是李白的唱,
我是涅槃的凤凰在飞翔!
不愧为大家手笔,歌词写得真好。后来,这首歌由著名歌唱家腾格尔先生演唱,情真意切,回肠荡气,闻听令人无不敛容唏嘘。
四
2000年1月1日,当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彻环宇的时候,余秋雨一行也结束了“千禧之旅”的考察与探访,来到了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交界之处。经历了千万种 艰险,先后寻访了希腊、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代文明之后,一步步走近国门,感觉到“离别之后”才真正地读懂了中国文化。平静一下情感涌动的心绪,余秋雨写道: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这是一位目光如炬、气度恢弘的学者在比勘了中外文明之后,站立在新世纪的门槛之上,回视历史的蜿蜒曲径以及峰峦叠嶂时,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很有感性色彩,也渗透着理性地思辨。
五
余秋雨之所以受到某些文人的“围剿”,并非其学问不高,文章不好,人品不佳。余以为,恰恰相反。如果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由于他过于自傲、过于自负、过于自珍、过于自惜、过于标榜所致。在当下的社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过”,则必定会走向其反面。所以,余秋雨便注定会长期地遭到“围剿”。池鱼之殃,受到伤害的当然还有当代戏剧界大师级的人物马兰女士,因为,她是他的爱妻。
六
很少关心文化界以及艺术界里那些鸡皮蒜毛的屁事儿。前不久搜索了一下“围剿”余秋雨的名单,出乎意料的是,真的有一位我所敬重的文化大家,沙叶新先生。作为剧作家,尽管他早年也创作有不够水准、且有“紧跟”之嫌的剧作,但因为后来创作出了《假如我是真的》和《陈毅市长》两部话剧,成就突出,影响巨大,便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戏剧界中的重要地位,至今无人能够撼动。
遥想当年,余、沙二人,一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为上海人艺院长,交情确实不浅,彼此视为同道,亦在情理之中。及至后来,一对好友竟反目成仇,以至相互攻讦,其间不排除社会环境原因、个人性情原因、人际误会原因,甚至也不能排除良善人士反而遭受居心叵测者的利用等原因。不过,站在局外角度,两个文化人,可以文攻,亦可以武斗;可以做心灵的沟通,亦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才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至于彼此交恶的一方,竟然拿另一方的夫人去说事儿,以对方的婚变来拨弄是非,口舌之剑,锋利无比,剑锋所指,伤及无辜,则如此人性品行,真令人侧目矣。
七
“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新旧世纪之交,余秋雨在考察了人类古代文明之后所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啻至理名言。
我想,如此慧语,在给予我们这些凡俗之辈以棒喝、以警醒的同时,著者本人,还有如著者一样高明的学者们,以及那些不遗余力地“围剿”著者的诸多文化人们,很有必要首先自己应警醒一番。能够做得到否?真的很难说。因为,拿着木棒指点别人,去敲击别人的脑壳很是容易,而敲击自己的脑壳则真的不易做到,此无它,痛呀。
必要时,再痛也得敲。这样,头脑才会清醒,血脉才会贯通,体魄才能强健,迷失的人性才会回归。
周末闲暇,捧读《千年一叹》毕,心有所动,匆匆草于明斋。2014年3月29日晚23时50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