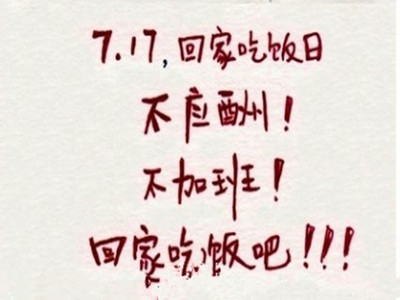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是很听家长话的,那时接受的教育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言行举止要儒雅文明,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凡是与人体不文明的部位有关的词语都不能入选语言的。由于“屁”的出身不好,我小时候说话时是从不触及这个字的,诸如“屁股”、“放屁”、“狗屁不如”等词,在我的语言里一般时候是听不到的,甚至于“拍马屁”这个使用率极高的词在上中学前我都没说过。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人们的观念更是在不断地更新,就像领导们不再批评下属穿奇装异服、婚外情不再只遭指责、孩子们关于“性”也不再是谈虎色变了一样,人们对“屁”这个字也已经不再像父辈们那么“忌口”了。
前几天上语言训练课时,有一个小女孩儿就以饱满的热情讲了一个关于屁的笑话———奶奶总放屁,一日要出门做客,怕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走时嘱咐好,奶奶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真能放屁!众客皆笑。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见奶奶还没要走的意思,便不耐烦地高声问道:奶奶,你还放屁吗?我想出去玩了……
这使我又想起三年前看到的一个关于屁的更可笑的故事,讲故事的人是长篇名著《国画》的作者王跃文,据此公讲这绝对是真实的。说:“文革”期间,某文豪正在田间劳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知乃放屁之兆,此人生性滑稽如东方氏,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接着哈腰蹶臀,洪渲一屁,声隆如雷。人们放声大笑,几秒钟之后四野鸦雀无声。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XXX揪出来!结果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说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没过多久,被判了三年徒刑。
学生和名人都敢大谈特说“屁”字,我又何惧之有?况且是在我自己的博客里,博客的英语意思就是网上日记,我在日记里说点不文明的话,谁也管不着吧?只是要请爸 爸妈妈的在天之灵不要怪女儿太粗俗了。
“屁是一股气,在我肚子里串来串去,一不小心串了出去”,这是很多绅士淑女放了屁以后红着脸的自我嘲解,说的时候一定笑着强调“不小心”三个字,似乎有了这三个字的搪塞,当众放屁便是理所当然了,自然,绅士的风度和淑女的矜持便不会打丝毫的折扣了。其实,放个屁是太自然不过的事了,何以用得着如此遮遮掩掩?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放屁不过是生理需要而已嘛!
屁,只是屁,但倘若把它同“话”连在一起,结合成“屁话”,可就不是需要问题了。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把没用的话叫“屁话”,我对这一认识却无法苟同。没用的话突出的特点是“没用”,因此它存不存在无所谓,它既不动听也不难听,人们听也行不听也罢,因为它对听者的心理不产生任何震动。而“屁话”却不同了,再小心放出的屁也是有臭味的,都是薰人的。所以我认为,“屁话”不仅指没用的话,也指带有强烈的伤害性而令人无法忍受的话。它让人感觉臭气薰天,恶心透顶,却又无可奈何,你总不至于让它哪来回哪去吧?“屁”放出来是收不回去的。

日常生活中好说“屁话”的大有人在,比如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骄傲自大孤芳自赏的人,喜欢街谈巷议造谣惑众的人,自以为是刁钻刻薄的人,他们每每不小心串出来的“气”会薰得身边的人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俗语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按声音的大小,屁可分为不太臭、挺臭、特臭几个级别。没一点声音的屁是最臭的,这种屁叫“哑巴屁”或“蔫屁”,人们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是放哑巴屁或放蔫屁,好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放这种屁的人不多。
有屁放出声来,尽管觉得不雅,好在知道是谁放的,大家调侃一番也就过去了,管他是不是不小心;倘若被薰得晕头转向还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弄不好还让人怀疑,那才是最窝心的事呢!
但话又说回来,放屁从某种角度看毕竟是极端个人的事,谁也保证不了自己一生当中能做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屁不放,臭也好,不太臭也好,放就放了,谁能把放屁者怎么样呢?但换个角度看,人们不只有生理需要,还有尊重需要吧?就算响屁不臭,那肆无忌惮的响亮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啊!希望诸君还是讲究点好,有屁忍着点出去放,别人不反感,自己脸上也能挂得住。
唠唠叨叨说了不少关于“屁”的话,很多人看了会嗤之以鼻,不愿意看的朋友就权当我在说“屁话”好了。2006年9月30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