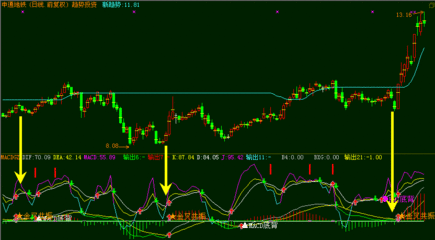红指甲
樊健军
这是高中同学央未生单独道给我听的故事,在虚构枯竭的时候,我将这个拿来道给你听。
大概有几年时间,央未生隐遁了,在赣西北的这座小城里谁也找不见他的身影。聚会了很多次,才发现少了一个人,央未生呢,问谁,谁也说不上他去哪里了。他会说冷笑话,话不多,可少了他聊天时就缺失了一些味道。这帮鸟蛋混在一堆,少不得海喝胡吹,十个倒有八个会讲黄段子,一个有一个的风格,一个比一个雷人。讲冷笑话的就央未生一个,他不在,就像做菜少了味精,怎么吃怎么不对味。有人拨打了他的手机号,是机械的提示音,对不起,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手机号不对,在坐的几个人相互求证一遍,都是同一个号码。这小子,换了号码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有人就有了怨声。也有人暗自嘀咕,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不测的事,或者离开小城了。几个人都在回忆最后一次见到他在什么时候,搜肠刮肚地回想,可谁也想不真切了,说得牛头对不上马嘴。有些朦胧记忆的就一次,中秋夜相约去赏月,带了酒和月饼,央未生喝醉了,让人架下山来。可是,乖乖,那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央未生醉酒,那是罕见的奇观了。他从来不喝酒,无论怎样的环境,多好的酒,都经得起诱惑,也顶得住压力。不喝就不喝,谁也奈何不了他。中秋夜的酒是他主动喝的,拿了酒瓶,嘴对咀直接往肚子里灌,灌了多少,都不记得了。那样的喝法,只有一个有心事的人才喝得出那种气势,何况平常他滴酒不沾。若要问什么心事,除了失恋别的伤心事还没出生呢。有了情事八卦,众人的耳朵都尖了,可听来听去听不出个所以然,说的人只不过猜测,对于央未生的事情知道的甚少。倒是有个女生犹犹豫豫站出来说,我知道。众人心痒难挠,就鼓掌怂恿她说,可她知道的也有限。同央未生好过的女孩叫叶乃倩,是个幼儿教师,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了多久,不知道,崩了都好几个世纪了。为什么崩了,也不知道,反正已经崩了,无可挽回地崩了。叶乃倩早成了别人盘中的鱼,别人床上的女人,别人孩子他娘。
央未生的事鲜为人知,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他。他在人民医院的传染科上班,人民医院在小城靠北的山脚下,传染科爬到了山腰上,还围了铁栅栏。对于传染二字,我们都是满怀敬畏,像鼠疫,天花,霍乱,艾滋病,让人很是犯悚,所以轻易不敢招惹他。
央未生的故事就是从醉酒之后开始的。这些年,其实他哪儿也没去,一刻也没离开小城。他说他在画画,画什么画,工笔画,说得暧昧些就是美人画。魏晋的仕女,唐代的贵妃,传说的仙女,敦煌的飞天。修颈,削肩,柳腰,洛水女神,杨贵妃,赵飞燕,月中嫦娥,哪一个不是美人坯子。白描,勾线,着色,开脸,兰花指。他画的就是这个,为什么画这个,不为什么,就是想画,不画手痒痒心也痒痒。但他画的又不是这些,而是古代名妓,你知道多少,苏小小,李师师,陈圆圆,柳如是,绝色容颜,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问他为什么画这个,不为什么,就是想画,不画吃不下饭,不画睡不着觉。从内心说,你根本不在意他画美人画的原因,你急于想知道的就是他在哪儿画,画得怎样了。如果入了你的眼,你还想索一幅画,不管魏晋的美人还是唐朝的美人,画在画上都一样赏心悦目。
西摆街313号,就是央未生的画室。你要是去过那儿,就会知道那是非常安静的一角。这小城让一条河流锯成了两半,一半北城区,一半南城区,后来又长出了东城区,工业园区,良塘新区。北城区是老城,形状像只蝌蚪,头在东边尾巴在西边,西摆街就是长溜的尾巴,央未生的画室就在尾巴尖上。他领我去过一次,那是个封闭的院子,临街的围墙比两个人还高,墙中间长了一棵法国梧桐,遮天盖地的,将院子都掩没了。从一扇小门进入,院内却是别有洞天,宽敞的院子,古朴的建筑,临河的一面伸出了吊脚楼,有半间房子架在水上。这的确是个理想的画室,街头的热闹让围墙挡住了,对岸的喧嚣怎么也涉不过宽阔的水面。绿水盈盈,风清气爽。央未生就租用了临河的两间房,一间做卧房,另一间当画室。房东姓夏,是个老太婆,头发银白,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了美国多年,儿子本想接她出国,可她执拗,说什么也不愿远走异邦。夏老太婆平常也不同人多接触,一个人守着这空寂的院落,养几盆花草, 养了一只白猫,还养了几只鸽子。我进院子时鸽子丝毫不认生,扑棱棱落到了我的肩头上。夏老太婆静眉静眼,应该不会随便让一个陌生人搅了她的宁静。我问央未生用了什么法子,他只回答了二个字,你猜。
大概你也不会相信央未生当真在画画。但他自己坚持说在涂鸦,他的休息时间不多,周三下午,周六上午,周日下午,加起来一天半,全部用在绘画上了。你想他拿出作品,那是妄想了,就是纸砚笔墨你也见不着。你觉得他在说谎,几年时间还画不出一幅画,就是生个孩子也会打酱油了。其实你应该相信他,让一个从来没拿过画笔的人画画,难度可想而知。就算画出来了,那也是真正的涂鸦之作,不敢拿出来见人。他说他用铅笔在白描,描了擦,擦了描,总没有一幅白描让自己满意的,就别说着色了。你能够想象,他临着窗,宣纸铺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勾画着。鸟儿肚,美人手。他画几笔,直起身端详几眼,眉头拧紧了。又俯身将线条拭了去。窗外流水,屋檐流风,他的日子就虚耗在这反复中。
你瞧他日子过得神仙,不问世事,不管苍狗流云。如果不是另一件事搅乱了,闹不准他仍在西摆街的画室画着古代的名妓们。画一套古代名妓全图,这是他逝去的梦想。你现在若问他还画不画,还画个傻蛋,画在纸上的,又当不得真。事情发生的时候,央未生正在白描苏小小,苏小小长得怎样没见过,只能依照买来的画册照葫芦画瓢。他并不完全在画瓢,而是想将苏小小画成飞天的模样,轻盈,飘逸。这是周日的下午,直到一河晚霞,意兴阑珊,他才收了笔,连苏小小的一只衣袖都没勾画出来。同夏老太婆一块吃过晚饭,照例在院子里踱几个圈,当是散步。他在夏老太婆处搭膳,所以少操了许多柴米油盐的淡心。散步没两圈,夏老太婆却将他唤住了,交给他一只小纸盒,装手机的盒子那么大。说是快递公司送过来的,见他在画画,没敢打扰他,就替他收下了。纸盒很轻,几乎没有重量。他想象不出有谁会寄东西给他,可盒子上的收件人赫然就是央未生。再看寄件人,却是空白的,寄件的地址也是空白的。他的好奇心让一只陌生的纸盒子吊了起来,不管谁寄的,一定先打开瞧瞧。打开之前,他有了很多猜想,这么轻飘飘的身份,不可能会是炸弹,即使打开也不应该有性命之忧。也有可能是一枚钻戒,十克拉的,光芒四射。或者是一盒颜料,他需要的。他还幻想,打开盒子的刹那间,苏小小水袖长舒,衣袂飘飘,如飞天一样活灵活现。
你也猜猜,盒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央未生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是只小布袋,白色的,丝绸的,手机套式的袋子。袋子口有根活动的绳子,收紧了,就将袋子口扎上了。如果指望苏小小从这么窄小的袋子里飞出来,那真就患了幻想症。捏捏袋子角,像是装有什么。央未生松了绳子,将袋子里的东西抖落在宣纸上,是一簇炫目的猩红。细细辨认,竟然是一簇红指甲,不多不少,正好十枚。再往细里辨认,从大拇指到食指无名指,一双红酥手,十枚红指甲,一枚都不缺。
这个谜底逃出了央未生的想象。他将红指甲放在苏小小的指尖,指甲短了些,只有半厘米的长度。它不像苏小小的指头纤细,也不可能是苏小小的指甲。它是谁的指甲,让人感觉很诡谲。他迷茫了,困惑了,不知谁同他开了这个玩笑。他也没法弄明白这个玩笑什么意思,也许只有开玩笑的人自己知道。让央未生找他问一问就清朗了。可央未生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他想从纸盒子上找到蛛丝马迹,捧起纸盒子又怏怏放下,纸盒子上什么破绽也没有,有可能快递单都是快递公司的人代写的。他将红指甲托在掌心,像托着一簇烫手的红炭。它们身上有什么秘密,或者在提醒他什么,甚至别的更深一些的意图。他弄不懂这个玩笑,玩笑也就失去了价值。他将红指甲装进丝绸袋子,放入纸盒,随手将纸盒扔在了床头柜上。
央未生一门心思投入了他的美人画。他猜想,有可能别人将红指甲寄错了,收件人不该是他。如果寄件人发现了错误,说不定会有人来将红指甲要回去。他等着就是。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有人出现。他将红指甲从袋子里倒出来,放在掌心察看,那些红指甲好像有着某种特异功能,让他眼花缭乱,不敢正视。它们鲜艳,妖魅,向他抛着媚眼,像一群血红的小妖在掌心动荡不安。他吐口气,将它们关进了袋子。我很怀疑他是伪装的镇定,那样的红指甲该是女人才有的,有可能有个女人在暗恋他,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他的关注。或者他早知道了那是谁的红指甲,不便说出来。但反过来想,如果红指甲是某个男人的,那就有些可怕了。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呢,你想想看。
不管红指甲是个玩笑还是个错误,他都懒得理会它们。他将内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美人画上。他牺牲了所有休息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固定在画室。他的专注到了狂热,偏执,盲目的程度,可就是没有人叫醒他。他对绘画根本没有天赋,加上无人指点,所以进展非常缓慢。他勾画了大半年时间,连一张让自己满意的白描像也没有,苏小小仍旧活在他的想象中,一步也走不出来。央未生说这些时脸上抹不去暗淡,还在为他的失败感到羞愧。我问过他有没有想过那是个女人的红指甲。我想那些干什么。他答话时将目光转向了别人。我判断,他对我撒了谎。你就没想过叶乃倩?我决定不饶过他,直接捅了他的伤疤。央未生的眼神迷离了,有颜色在他的瞳孔中央变幻,一会儿绿,一会儿红。不,没有。他最后很干脆地回答了我。
你是聪明的,央未生的这种神情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敢断定,他同叶乃倩的确有过那么一回事。有可能红指甲就是她寄给他的,否则谁知道他隐身在这么个世外桃源。绝对不可能。他立马否决了我的猜想,谁寄的我都相信,但绝不会是她。我问他为什么。叶乃倩的手指很粗硕,指甲不可能那么纤细,而且她有一块指甲让刀子割裂过,指甲一分两瓣。所以她留不了长指甲,至少不会有十枚长指甲。我同央未生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他同叶乃倩的关系,他不知不觉钻入了我的圈套,但我没揭穿他。他对她的观察挺细心的,小到一块指甲都如此清晰。我没见过叶乃倩,也没见过她的手指和手指甲,央未生说什么我就只能相信什么。后来的一天,央未生拉我去看过一幅巨幅照片,是在一家婚纱影楼的展示橱窗。照片上的女孩一身洁白,手捧鲜花,嘴唇鲜红,一脸幸福的笑容。喏,这就是叶乃倩。央未生说。是个美人坯子。我的赞美很虚假,又不能不敷衍一句。所有经过婚纱影楼化妆后的女孩子都变成了同一个模样,一样的脸蛋,一样的笑容,谁同谁都没了差别。只有一个地方不同,那就是眼睛,瞳孔的内部,任何化妆都改变不了,也掩饰不了。叶乃倩的目光很空洞,瞳孔中央藏了很深的欲望。这幅照片就挂在百合新娘的橱窗里,你有空也去看看,我绝对没说瞎话。

央未生的做法并没有消除我的怀疑,叶乃倩戴着手套,她的指头全让洁白包裹了。我看不见她的手,正如我也看不到她的内心。其实她的手指甲完不完整同我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将这些道给你听,你我都一样,都在拿央未生的故事消遣,打发无聊的时光。再加上些八卦,人的本性本来就喜欢八卦,甚至隐藏着某种窥私的阴暗。
但你我的喧嚷丝毫影响不了央未生的宁静。他的美人画慢慢看到了希望。他消耗了大半年时间,终于勾画了一幅苏小小的白描像。虽然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但毕竟是他亲手勾画出来的。他又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它修改,到最后仍然有些地方不满意,他已经无法将它勾画得更完美了。他尝试着给她着色,可着色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调和出来的颜色要么色泽不对,要么就是深浅不适,浓了或者淡了。他软着性子反反复复调试,慢慢接近他需要的颜色了。这些颜色都是些调皮的家伙,在调色盘中是一副嘴脸,涂着宣纸上却成了另一副嘴脸。它们有时一脸阴暗,转眼又是一脸阳光,变幻极为迅速,让你无法捉摸。等到将你捉弄得精疲力竭,它们才同情你,怜悯你,对你俯首称臣。所以,你不能指望他第一次就画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也许将来有一天央未生会成为一个工笔画家,他的代表作就是以古代名妓为主题的美人画。
央未生有可能也对自己的美人画充满了期待。如果不因为红指甲,他还会无休无止画下去。我追问过那幅苏小小的画作,央未生摇了摇头,说,没了。我想拿到他画美人画的证据,他躲在这么一个幽静的角落,画画只是他的借口,我怀疑他不是一个人,有可能在同某个不能见光的女人偷情。但他告诉了我毁画的过程,他将它点燃了,从窗口扔出去,画纸没飘到水面上就焚为了灰烬。那些灰烬最后都飘落在水上流走了。
你相不相信他将画毁了,反正打死我也不相信。如果换了你,你会不会毁灭它呢,估计你也不会。如果是我,我就不会。
我估摸,那个寄红指甲的人一定在等着观看央未生的笑话。他或她,闪在某个角落,目不转睛盯着西摆街313号。可院子依旧是个安安静静的院子,鸽子在飞进飞出,夏老太婆偶尔出门一次也是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央未生下了班就呆在画室闭门不出。他或她就失望了,不过半年,央未生第二次收到了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同第一次一模一样的纸盒子,拆开纸盒见到的又是一模一样的丝绸袋,从袋子里倒出来的东西仍旧是一簇醒目的猩红。只不过这一次的红指甲比上一次的长那么一点点,一样的纤细,一样的小巧。从它们的模样看,这二十枚红指甲来源于同一双红酥手。第一次收到红指甲,央未生理解成了一个玩笑,或者是错误。相同的玩笑开第二次就有些不正常了,至少是故意的,说得严重就是个阴谋。央未生耸耸肩膀说,他脑子都想残了,就是没琢磨透这是个怎样的阴谋。可能这一辈子都是个不解的谜。二十枚红指甲,每一枚都是干净的,又是血红的,像二十枚诱人的欲望。托在掌心,就像一簇血红的火焰,灼得掌心生痛。
你知道了这些,也许能帮他思考一下,出个主意,假如收到红指甲的人是你,你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如果你不受它们的干扰,坚持安静做某一件事情,那你就修炼成仙了。央未生不过三十来年的修为,离仙境还很遥远。他只要闭上眼睛,那些红指甲就在他的眼皮上跳跃,像一群顽皮的小妖。睁开眼睛,它们更不放弃他,他勾画线条,它们就簇拥在铅笔尖,他给画着色,它们就在宣纸上奔来跑去,整张纸都染上了满目的血红。他想一定得找到那个寄件人,向他或她问个明白,为什么寄红指甲给他。他扔下画笔,将美人画丢到了一边。寄件人到底是谁,也许你会觉得央未生内心清醒得很,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央未生却发誓,排除了叶乃倩之后,再也想不到第二个人了。他只有拿着纸盒去找快递公司,也许他们能给他一些线索。他要找的快递公司在北城区的北门,一间废旧的仓库内,到处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纸箱子,仓库前有一辆辎重车正在卸货。接待他的是个年轻人,拿着大把的提货单,在货堆里翻找着。他搬着一只纸箱过来时刚好遇上了央未生。提货单呢?他朝央未生努了努嘴。央未生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让他在旁边等着。打发走几个提货的客人后,年轻人才将他领进一间从仓库内间隔出来的办公室,丢给他一堆帐簿,让他自己慢慢查找。帐簿上挤满了名字,都只有简单记录,就是收件人的姓名,收件地址,联系电话,货物件数。央未生不敢相信,这世界怎么了,这么多东西寄过来搬过去。他查找了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二次收件记录,都只有一行字:收件人央未生,地址西摆街313号,货物件数一件,最后是夏老太婆的签名。还有别的记录吗?央未生傻眼了,问发货的年轻人。全在这儿了,年轻人回答他。你上这儿来查查找找,还不如直接打个电话给寄件人。年轻人提醒他。央未生张了张嘴,发现自己没法同他解释清楚。如果他知道寄件人是谁,还上这儿来,神经啊。
央未生有了浅浅的愤怒。他已经没法回到美人画上去了。他的内心像燃了一簇火,那些红指甲烈焰腾腾,就差没将他焚为灰烬。但他拿那个寄件人毫无办法,他捉不到他或她,就连快递公司都隐瞒了他或她的踪迹。央未生若是想找到那个寄件人,只有发挥他自己的想象,从浩荡的人群中揪出几个怀疑对象,逐个去求证。这就不可避免牵连到了叶乃倩身上。我问过央未生到底找过叶乃倩没有,他嘴上叼着古巴雪茄,沉默不语。抽古巴雪茄的在小城找不到第二个人,据说一支烟都值好几百。在我穷追猛打之下,他终于承认了,他不只怀疑过叶乃倩,还跟踪过她。他远远地跟着,跟了好几次,都无法证实寄件人就是她。她已经不是幼儿教师,而是成了全职太太,还是一个一岁多女孩的母亲。她嫁给了本城一位地产商,地产商离异了,房室正空着。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占去了南城区的一大半,家大业大。叶乃倩出门都有专车,司机保姆陪同,央未生压根找不到单独同她说话的机会。就这么远远跟着也险些出了事,瞅着他鬼头鬼脑的,让治安联防队当做有企图的人盘问了一回。
央未生说到叶乃倩时始终锁着眉头,似乎很不情愿谈起她。这我也能理解,毕竟央未生不是原来的央未生,不再是传染科的医生,而是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他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功都让他有所顾忌,生怕有什么事情会落人笑柄。在跟踪未果之后,央未生坚决将叶乃倩从他的怀疑对象中删除了,她连十个完整的手指甲都没有,绝对不是她。他重新拟定了一个怀疑名单,所有的同学,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到大学,认为有可能的都在名单之内。这份名单实在太长了,每个人都值得怀疑,每个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可能找到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寻找各种理由替他们开脱,到最后,名单上一个名字也没能留下。他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他的同事。他惊讶地发现,传染科竟然藏了那么多女人,从80后到70后再到60后,每个年龄段的都有,加起来有二十多人。环肥燕瘦,软语吴声,玉兰纯白,这些原来都忽视了,现在突然专注,他的风景也随之绚烂了。可央未生无心欣赏风景,她们都是他的怀疑对象,也许那个寄件人就隐身在她们中间。对她们每一个,要说了解,他都了解,平常工作中都有接触,接触的都是表面的,要说了解多少,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可每一张脸都是模糊的,她们是怎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离她们很远,很远是一种感觉,实际的距离谁也算不出来。将怀疑落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他很茫然,不知谁是他青睐的对象。
他的六神无主,漫无目标,都是寄件人嘲笑的内容。央未生无可奈何,只有将美人画暂时放下了。他努力搜寻那个寄件人。他锁住了传染科的一位护士,她是外省应聘过来的,80后,有着可人的脸蛋和诱人的身段,只是个头小巧了些。她追着他要他请客,还希望参观他的巢穴。正是她的这些异常举动让他注意了她,她的手指细长,指甲纤瘦,不过不是血红的,而是镀了莹白。他瞄上她好长一段时间,却没发现她有更进一步的异常。他试着靠近她,可她的反应不卑不亢,不热情也不冷淡。有一次,他同她一块当班时聊到了手指甲,她的表现很平淡,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甚至暗示她,他喜欢红指甲。他的话不知是她没听入耳还是她迟钝,过些天,她的手指甲仍旧闪着莹白。如果她有所表示,他有可能会将红指甲的事告诉她。但最后他只有收回了失望的目光,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人。
传染科的同事让央未生筛选了一遍,几个可疑对象都让他逐一排除了。也许他不应该怀疑同事,医院有规定,无论医生还是护士都不能留长指甲,更不能涂指甲。下一步,他该怀疑谁呢。他想到了他医治过的病人,对于他们,更没有很深的印象。除了必要的治疗时间,他同他们很少接触,毕竟在传染科,多少存了一份戒心。他们的影像是模糊的,不会有具体的模样。她们留不留长指甲,谁染了红指甲,就是对着病历,他也回忆不了这些细节。这时候,他在内心已经认定寄件人是个女的,年纪轻轻的女人。她用红指甲在暗中挑逗他,诱惑他,让他骚动不已。红指甲是妖野的,是欲望的。它代表了什么,他不知道,就像她一样是个谜。二十枚红指甲就是二十个小妖,在他的内心跳着舞,狂欢着。他逮不着她,也就找不到答案。他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从开始就弄错了,红指甲不是寄给他的,他是个错误的收件人。她这样做的阴谋是什么,是炫耀她的指甲,还是她在暗恋着他。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睛里的光芒越来越锋锐。我恨不得强奸了她。央未生回忆寻找的过程时依旧难掩内心的愤怒。
央医生,别太熬夜了。夏老太婆安慰过他。
她以为他仍在画他的美人画。她一惯都很安静,从不随便打搅他。你可以想象央未生当时憔悴的程度,有可能惨不忍睹了。他当初选择这儿做画室,一半因为环境的清静,一半因为夏老太婆内敛的性格,不喜欢多管闲事也不唠叨。央未生猜测,也许有人出于相同的原因,在他之前租住过她的房子。没有,从来没有。夏老太婆当即就否定了他的猜测。
你猜猜看,接下来央未生该做什么,上哪里去找到那个寄件人。这个人是一定存在的,有可能就生活在小城中,或者在央未生的身边,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在他的世界之外。可他就是找不到她,她是个没有谜底的谜语。他试图想让自己沉静下来,回到美人画上。他不去思想她,不去猜测她,也不去怀疑她。让红指甲见鬼去吧,他说得恶狠狠的。他一个人躲在画室,对着宣纸,对着画册,对着窗外流水屋檐流风,勾画,着色。给美人开脸。可他的手在颤抖,不受他的控制,不听命于他。颜色也来捣蛋,明摆着需要黄色,偏就成了红色。粉红的地方描成了朱红。圆脸成了方脸,高挺的鼻梁成了塌鼻子。一切都变了样,美人不是美人,而是丑八怪。满世界都找不到画纸上那般奇丑的女人。
央未生的内心有一种不明之物在乱冲乱撞。他没法平静自己了。西摆街313号成了他的旅馆,只有在极端疲劳时他才回去睡一觉。他闲瑕的时候就在大街小巷游荡。他说起这段散漫的经历时语气是新奇的,激荡的。也是令人窒息的。这外面的世界同西摆街的院子完全不一样。他走进了一个红指甲一般的世界。到处都是红色,高跟鞋是红的,裙子是红的,头发是红的。灯是红色的,广告牌是红色的。云是红色的,花是红色的,女人的内衣也是红色的。眼睛是红的,猴子的屁股也是红的。女人的嘴唇是红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红色的,她们说话的声音也是红色的。红色无处不在,红色无孔不入。流动的是红色,静止的也是红色。在街边站立的是红色,在舞台上跳动的也是红色。躁动的红色,欲望的红色。像血液一样滚烫的红色,像冰一样彻骨的红色。红色可以钻进你的耳朵,红色可以漂染你的目光,红色可以穿越你的思想。他跌入了一个红色的陷阱。有无数双手在向他挥动。她们都有着长长的红指甲,波澜壮阔的红色海洋。那么多的女人,她们的指甲都是血红的。他发现了一个制造红指甲的地方。一双交叉的手在玻璃橱窗里向他揭穿了这个秘密。他又发现了另一个同样的地方。再一个,后来无数个。红指甲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源源不断,滔滔不绝。那个寄件人就是其中一员,二十枚红指甲只不过是其中可以忽略不计的红色。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央未生要离开西摆街313号了。我的感觉不会出错。央未生说他在第三次收到纸盒子时告别了西摆街。那是同前二次一个模样的纸盒子,又是十枚同样的红指甲,长度比第二次收到的稍长一些。可不管它们怎样,他已经放弃寻找寄件人。这寻找本身就是荒谬的,他很后悔之前的找寻,那么执着想去揭开一个谜底,压根就是犯傻。夏老太婆对他的离开也没有激动的表现,只告诉他一件事情,她有个女儿,像他一般大,几年前不知遭遇了什么变故,从央未生居住的房间跳了河。夏老太婆说这些时语调是诚恳的,是真挚的,好像对他有些愧疚,本应该早些让他知道。听了这个故事后,央未生也没有过多反应,只是回头望了一眼自己的画室,好像夏老太婆的女儿就在画室的窗口微笑,向他招手。他在画室里勾画,着色,夏老太婆的女儿就在窗外陪着他。对此,他毫无所知,也毫无感觉。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停留,而是快速走出了院子,走出了梧桐树的绿荫,绿荫之外正是一个明媚的上午。他在阳光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回头望了两眼院落,夏老太婆倚靠在门框边,满头银发飘动,朝着他走出的方向。这是个孤独的老太婆。有一只鸽子划了一道弧线,栖在了梧桐树上。他想他不会再回到这个院落了。
央未生后来的事情想必同学们都知道了,有可能你也听说了。他向医院辞了职,去了南方。摸爬滚打几年后又从南方回来了。现在他是小城的一位地产商,在东城区,良塘新区都有他开发的楼盘。他的产业盖过了叶乃倩的男人。环绕央未生的,同所有商界大腕一样都是香车美女,灯红酒绿的生活。他的女人是小城电视台的一位主播,普通话标准,人更是标准的美女。我问过央未生那些美人画藏哪儿了。他回答我的仍是那句话,烧毁了,一张也没留下。你还想见叶乃倩吗?我又问他。我见她干什么。他反问我。我这么问他其实是想告诉他一个秘密。我曾近距离接触过叶乃倩一次,特别留意了她的双手,她的十枚指甲,不仅红得鲜艳,而且每一枚都完美无缺,并没有央未生所说的分裂。我猜想她有可能做过指甲修复,我进一步猜想那些红指甲说不定就是她寄给央未生的。我甚至猜想,如果真是她寄的,她想拿那些红指甲向央未生透露什么信息呢。我只是猜想,最终答案是不是这样谁也不知道。但我终究没将我的猜想告诉央未生。
那些红指甲呢?哪儿去了?也许你会关心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央未生,但他没有回答我。我问话时他正好背对着我凝神望着窗外,指头上夹着古巴雪茄,窗外是他刚刚开发的楼盘,正像红指甲一样迅速生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