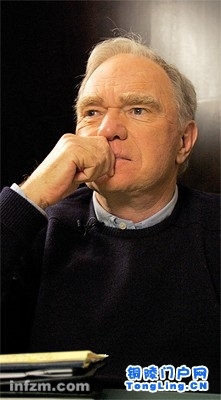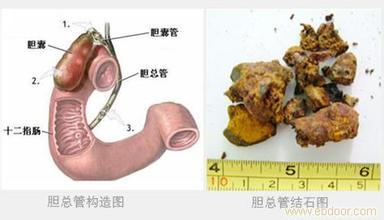其实这个不是为了夏达一个人而写的,当时写的是回忆在北卡的很多生活,提到了很多作者,都很艰苦,只不过因为跟夏达接触比较多所以写她的部分多一些。反正说的也都是实话……如果大家看到之后确实收获到的是很积极的东西,那我想保留应该也没有关系吧,毕竟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回忆录里讲过很多漫画人的经历了,据说很多人看我们的生活,看得很羡慕。大约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回忆录才会一直让很多人感到排斥。
其实,如果把这些年见到的快乐和痛苦一起放在天平上称一下,真的不知道哪一边会更重。也经常看到一些哭喊的文字,说自己为了漫画曾经多么多么地痛苦,可是这些大约打动过不少普通人的文字,在被我们看到之后多半只是得到淡淡一笑。或许真的没有人能想到我们究竟经历过什么。今天我在这里写到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曾见他们对任何人哭喊过,或是抱怨过。因为他们都是骄傲的,包括我在内。我们不屑用自己的磨难和痛苦去博得别人的同情,更不屑用这种同情来换取任何支持或是赞赏。我们每个人想得到的,只有基于作品之上的,不论是认同还是否定。至于那作品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其实根本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
然而,今天我把这一切写出来,或许只是因为看过了太多可笑的误解吧,是的,我想他们仍然不需要任何基于同情的赞赏,但是至少,或许这可以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平等和尊重。毕竟有这么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我们曾经努力,把自己能够创造出的所有快乐和欢笑呈现给大家,仿佛从来就不曾有人掉过一滴眼泪。而这里,就是我们不曾告诉过你们的,那些眼泪的故事。
2
来到北京之前,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曾经有过两个人劝我不要来,一个是姚非拉,另一个叫惊尘。他们的理由是一样的:“做漫画很苦的,你可能会受不了。”
姚非拉给我讲过很多他的经历,比如穷到没有钱吃饭,去买大米的时候一般人都要一买几十斤,而他只能假装挑剔地跟老板说:“我不知道这米好不好吃呀,先买一点点回去尝一下。”然后买上很少的一点点回来,小心翼翼地尽可能多吃几天。再比如在画连载的时候病倒了,却没有办法休息,于是每天自己一个人哭着在画那些搞笑的漫画,这后来竟然练就了他一种超人的本领——如果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工作却很多,就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能生病,绝对不能生病,绝对不能生病……”然后竟然就真的不会病倒。后来他用这种理论教导每一个他身边的人,不知道对其他人来说是否真的有效,不过在我身上似乎还真的灵验过~
惊尘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后来做了《漫动作》的最后一任主编。当时他还在北京做另一本漫画杂志,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们正住在一间没有窗子的阁楼里,据说老板不见了,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不知去向。他用来教育我的不只是他的现状,还包括他再之前住在地下室里做漫画网站时的痛苦遭遇……
可是我想了想,这些受过这么多苦的人现在却仍然在做漫画,那么说明这些苦我也能承受。事实证明,我想的没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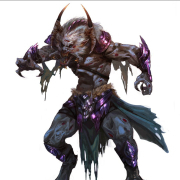
来到北京之后第一个和我关系变得非常亲密的作者就是夏达,因为我们俩一开始住在一间房间里,后来虽然有了各自的房间,但却也一直住在一起,直到2004年才分开。所以如果说漫画人的生活,介绍她的生活我应该算是最有权威了~
我们住在回龙观的二拨子新村,一个名字很怪的地方。不是回龙观新开发的那些小区,而是为原来当地的农民回迁准备的一片居民区。房租很便宜,平均每个人大约只要200块钱。我们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才在这里安顿下来。然而,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虽然房租便宜,但那里进城却非常之不方便。
我每天上下班如果坐公共汽车的话一共要花大约四个小时,而且晚上8点以后就没有车了。当时北卡的小编们经常加班,晚上十点以后才干完是常事。如果那个时间要回家就只能打车,一趟就要30块钱左右。如果索性不回家,夏天还好,春秋冬三季一到后半夜,办公室里就会变得非常冷,而且办公室没有沙发,我只能蜷缩在两张拼起的折叠椅上睡觉,这样根本谈不上恢复体力。这样一个月偶尔熬上一两天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受不了。结果后来我的收入就变成一大半都花在了路费上。
与此同时,夏达的收入就更加紧张。刚来北京的时候她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还在电影学院上班。地下室虽然苦了点,但是离上班的地方很近,但是搬到回龙观以后,每天在路上花费大量时间和体力让她根本没有精神画漫画,最后只好决定辞职。辞了职,收入就只能靠作品。当时她大概几个月才能发表一篇短篇,所以收入拮据不言而喻。
在二拨子的那段时间里,她完成了后来很多人很喜欢的那篇作品《雪落无声》。大概可以说,作品中那忧郁和无奈的情绪正是她当时状态的写照。考虑到她当时还处于短篇创作阶段,在多处露面可以更有利于作者的宣传,所以这篇稿子先是投给了漫友。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她已经快要吃不上饭了,而漫友的稿费听说可以比北卡发得快一些。
稿子投过去不久,负责的编辑就告诉她,可以在最近一期上刊出。我们都很高兴,同时她也已经开始了下一篇《路》的创作。然而一个月过去了,稿子没有登出来,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她于是惴惴地去问,才得知当时负责她作品的编辑已经离开了漫友,在离开之前,并没有把她的稿子转给下一任的编辑。
当她终于找到了现任编辑时,得到的答复是稿子要重新审,审过了才知道能不能用。她听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算了,还是不审了。”之后她问我,是不是她的稿子不好,我说怎么会呢,拿来,我给你登。
虽然只是一次无奈的巧合,导致的直接结果却是她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了。短篇作品在北卡是不可能预支稿费的,本来已经拖了两个月,就算当时就决定使用,那么杂志制作需要一个月,发表之后还要两个月之后才能领到稿费,这样前后加起来,结果就是她将近半年没有收入。
那段时间我们吃得很讲究。比如我,通常午饭是在楼下的小馆子里买一笼包子上来一边吃一边工作,只要三块钱。如果再拮据一点,就是一个鸡蛋煎饼,两块钱。虽然又便宜又有肉有蛋,但天天如此,吃到最后会忍不住有点想吐。可是夏达实在比我要厉害多了。她就自己躲在屋子里泡一碗比较便宜的方便面,然后一直吃。对,就是一碗面,中午起床泡上,吃几口,然后去画画,晚上累了再吃几口,然后去画画,半夜饿了再吃几口……凡正她的饭量小,有的时候这一碗面竟然可以持续吃上好几天。大家都知道,面条泡久了是会发胀的,口感……就不用说了。我们偶尔进她的屋子,在她的电脑旁看到一碗褐色的奇异的东西,问她是什么,她就会回答我们:“不要扔,那是我的方便面,我还要吃的。”
大家住在一起,当然很难看着别人挨饿不管。所以我们两个的钱有时候是会混在一起花的。但因为她的自尊心太强,如果饿了病了,就连我也不告诉,除非我主动去问才会知道她需要什么。而我自己也并不宽裕。最糟糕的,是当她的钱都花完,而我也还没发工资的时候,两个人就变得真的没有饭吃。交房租的日子到了,我们没有钱,只好向谷强借钱交房租。但是除了房租之外,我们不好意思再借吃饭的钱,于是就只好饿着。记得有一次她的口袋里已经一块钱都不剩了,而我还有一点点钱,我们两个当时躺在她屋子的床上,我说:“我用这点钱去买点东西,咱们两个吃。”她却摇摇头:“别去,我有经验,只要一直躺着不动,就可以不耗体力,还能撑几天。你现在如果出去买东西,体力一下子就耗完了。”
可是人可以不吃饭,猫却不能。咪咪是夏达刚到北京时买的小猫,因为当时在猫贩子手里瘦得厉害,她一个不忍心就花二十块钱买了下来。我们饿得不能动的时候,它当然也没有东西吃,它不懂得忍耐,只是在屋子里一声声地哀叫,最后听得人难过,于是我最后那几块钱,就拿去买了一根火腿肠,成了它几天的粮食。
那一次我们最后还是没撑到我发工资,而是www闻讯赶来,带了一堆肉啊菜啊,给我们做了好几顿饭。朋友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能救命的。
3
如果买过夏达的《四月物语》,会在里面看到一篇没有对白的短篇,叫做《寂静的地图》,那是唯一没有在北卡上发表过的作品,是她当时专门应邀画给一本家乡的新杂志的。故事的结尾,女主角在陌生的城市里,站在路灯下,一个人哀哀地哭泣着,华灯初上。那一幕的灵感也来自她当时的亲身经历,因为她就曾经在北京的街上突然地哭起来,只不过不是因为逝去的初恋,而是……因为饿。
除了挨饿的情况之外,我们偶尔也会生病。然而因为大家都不是习惯被人照顾的人,所以往往即使有人生了病也不会告诉别人,只会自己偷偷地躲在屋子里苟延残喘,等到有一天活过来了,才把这些当作笑话去跟别人分享。
在二拨子的时候,我发过几次高烧,所以都会自备体温计。严重的时候不能去上班了,就自己买点药在屋里发汗。有一次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去厨房倒水吃药,结果因为头太晕,拿杯子的手伸错了地方把滚烫的热水直接浇在了自己手上。当时自己还在那里发愣,幸好赶上mint来厨房看到了,赶快把我拽到她屋里去清理伤口,贴创可贴。那伤口在烧退后不久也就自己愈合了,只是至今还能隐约看到留下的疤痕。
夏达刚来北京的时候大病过几次,不过后来反而再没怎么去过医院,又或许是因为她自己躲在屋里,生了病也没人知道,慢慢也就好了。不过后来她跟我们讲有一次头晕得最厉害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医院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早上起床她从床上半个身子爬起来之后一阵晕眩,然后直接整个人跌到了地上去,因为那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所以她就这样一直在地上躺到了傍晚,居然慢慢清醒过来,自己又爬起来了。所以说,人的生命力这个东西,还是很顽强的。
奇怪,怎么越说越想笑,感觉我们实在好像小强哦。
在这里想跟其他还想来北京的外地朋友说一下(如果还有的话),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下室和郊区的楼房之间尽量选择租郊区的楼房,但是郊区和市内的楼房之间还是尽量选择租市内的。虽然房租上可能会贵了将近十倍,但是生活环境对人的心情和工作状态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二拨子,我们的住处距离最近的超市大约要步行近半个小时,这并不算远,但是这条路上没有任何树木和建筑可以遮荫,只有无穷无尽的从附近工地刮来的黄沙尘土,在气温40多度的北京炎夏,那简直就是地狱。偶尔甚至还可以看到蝗虫……房间里当然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一天到晚都开着窗子,到了晚上,猫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在我的床上捉蛾子,大大小小的蛾子,大的吃掉,小的就把尸体留在那里,变成床单上非常有个性的装饰。超市是我们那附近唯一可以闲逛逛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基本没处可去。所以除了每天上班的我之外,像夏达就索性整天待在家里,除了漫画圈子的聚会(通常有人请客)之外,一两个月才出门一次。
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总是爱美的,逛街买衣服这样的心愿虽然奢侈,但总还是没办法从心中挥去。于是每当终于拿到了一笔稿费,总还是会有人急切地想要出门,进城去看看。通常我们会叫上www,有时还有喵呜,然后坐上两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往那个非常拥挤但衣服却超级便宜的地方——动物园批发市场。
这么称呼这个地方只是因为它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当然卖的东西跟动物没啥关系,不要误会。之所以不顾旅程的漫长和颠簸,也不管那里的人流有多么拥挤空气有多么污浊都一定会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无数各种各样只要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的衣服。然后用尽一切砍价的手段,装可爱,扮可怜,谎称自己还是学生…………记得有一次,她们发现了一家店出售各种各样的白色连衣裙,每件只卖20块钱,于是兴高采烈地一下买了三四条回去。那些裙子夏达穿了很久,先是作为正式出门时的着装,后来裙子慢慢皱了(我们没有熨斗),开线了,就改当睡衣。这就是这些便宜衣服的另一大好处——它绝对是纯棉的。
现在各位知道了,你们每年在漫展上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夏达”,其实就是由这些东西装扮起来的。每当我们在论坛上看到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宣称夏达“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大笑起来。事实上,除了基本的护肤品之外,我见过夏达唯一买过的一件化妆品,是一支睫毛膏,因为一年也难得用几次,大约直到现在还在。
在二拨子生活了一年多,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生活上的困苦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其实也并不算是什么痛苦的事情。真正让我们觉得难过的,是另外一些经历。
我说过,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属于回迁农民的居民楼。然而就在我们租房合同到期的前几个月,非典开始了。住在那里的其他人都尽快地离开北京避难去了,只留下我、夏达和夏达的另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似乎也没什么可觉得害怕的。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疾病,而是人。很快,居民区开始设关卡,禁止外人出入,尽管他们不能把付了房租的我们马上赶出去,但却可以百般刁难。只是出门去买点菜,前后花费不到十分钟,再回来就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诘问和盘查,甚至语带侮辱。更可怕的是,白天还会有喝醉的男人跑上来咚咚地敲门,在门口醉醺醺地胡言乱语,而当时只有夏达一个人在家!即使把这一切都默默地忍了下来,最后还是被找到了理由——据说非典可以通过宠物传染,所以房东禁止我们再养猫。
软磨硬泡,连哄带骗,终于拖到非典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新的住处,租房合同也已经到期。最后搬家的那一天,房东突然又出现了,而且还带着他二十多岁的儿子,两个男人赤裸着上身,一个站在门口,另一个则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告诉我们“客厅的玻璃有一个洞,要赔50块钱,厨房的洗手池管道松了,要赔一百块钱……”本来我们叫上来收旧家电的人也被他们赶了出去。“不赔钱,房子里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叫他来干嘛!”“报警?好哇,这一片的人我们都认识,你叫警察来正好,这边的警察跟我们熟得很……”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把所有不打算搬走的旧洗衣机、旧显示器、旧桌椅……全部留给了他们,还加上两百块钱,这爷儿俩才心满意足地放我们离开。
这不能算是漫画给我们的遭遇,只能说是,每一个北漂族必须面对的吧。因此虽然这是我生活经历中最令我无法忍受的部分,我却从未把它怪罪到漫画头上去。
不过接下来的部分就和漫画密不可分了。
离开二拨子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个不错的房东,夏达也慢慢开始了《米特兰》的连载。然而我想,离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短篇作者生涯而步入连载,对她来说大概只能算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吧。。。。。
曾经在杂志的专栏里写过她曾经为了赶连载三十多个小时不睡觉,二十来个小时不吃饭,或许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当时我在她隔壁的房间,和她一样不能睡觉,因为我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过去大叫:“快点画!还有多少了?快点!”要不然,她一定会一不小心睡着。
还有次,截稿日前后,她生病了,痛得在床上打滚,然后觉得稍微好一点就爬起来继续画画。她的助手看得不忍心,跑过来对我说:“她都那样了……就让她休息一下吧!”我冷冰冰地回答:“不行。”眼皮都没有眨一下。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真像个恶魔。
夏达的作品肯定还存在着很多这样那样的不足,也经常会有读者来信督促她进步,但是在我做漫画编辑这几年里,只有她的连载我从来没见过读者来信说“这期画面太粗糙了,有赶稿的嫌疑”这样的意见。因为即便是饿到吃不上饭,忙到不能睡觉,病到爬不起来或是截稿日已过,都不能让她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即便是在上面说过的那样可怕的情势下,她仍然会执着地用笔尖的侧面在女主角的裙褶上画花边,或是把男主角一件全黑的斗篷排满手打线。我和www都会因此而恨恨地大骂她只会做些无用功,但她却会认真地说:“我知道这些印出来以后就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但是读者看到这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时候也一定会感受到画面的细致的!”犟得像头牛。
像这样主动严格要求自己到变态的地步,国内作者我听说过的人里,除了她大约也就只有姚非拉了吧。虽然我知道她一定不喜欢我这样比较……
4
夏达的事情说了很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连点滴的细节都晓得。但其实,她绝对不是过得最苦的一个,只是其他人我知道的就没有这么详细了,所以可能写不了这么多。
还是住在二拨子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生,名叫田丰。他和家人关系不太好,来到北京的时候,有点类似离家出走的状况,所以差不多算是身无分文地来的。接待他的时候,谷强给了我两百块钱,让我用这些钱给他买套被子,然后,他就这样在二拨子的一张折叠弹簧床上住了下来。
田丰的性格有点古怪,大约可以算是非常孤僻的一类,但是如果聊起漫画,有时又会变得非常多话,热情澎湃。我们给他讲了以前曾经有漫画作者在北京穷得四处借钱,之后消失无踪的故事,鼓励他一定要自己奋发努力,因为当时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无所成地离开的人实在太多了,简直数都数不过来。他虽然才只发表过一个小短篇,却让我们觉得很有潜力,很希望他能坚持下来。
他在二拨子那些短暂的日子里,我和他聊我想写的长篇故事,跟他讨论故事的情感和走向,让他尝试着画一下看看,还帮他找了一些游戏的图片作参考。他画了一个短短的开头,还有一些人物设定,我觉得非常喜欢,几乎以为我的连载就将这样来到这个世界。
之后,虹宇创作中心成立了。我非常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画我的故事,可是他没有钱,不能这样一直吃我们的住我们的,而创作中心可以立刻解决他的经济问题。于是他离开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有点生谷强的气,他挖走了我遇到过最适合画我故事的作者——虽然谷强可丝毫不这样认为。
田丰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者,然而他与人交往的能力差到更加超乎想象。即便是在每一个编辑都非常欣赏他,乐于和他交流的情况下,他仍然几乎没办法和大家交流。在创作中心的那段时间,几乎永无休止的情绪问题磨掉了每一个企图和他配合的人的热情,在几个月后,创作状态跌落到谷底的他终于决定离开了。看着男生屋里那张又破又旧的折叠床,偶而还是会让人想起这个靠着大家资助的一床被褥在这里住下来的男孩子……每次,心里都止不住地有些酸。
如果说田丰的离开已经让人心酸,那么更加让人心酸的,是另一个男孩子的坚持。我想熟悉北卡的读者应该知道那个名字——他叫张腾。
当听说张腾也决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觉得这样高兴,每一次听说一个有潜力的短篇作者到来,都让人觉得前途又多了一线希望——尽管他们大多数的结果都是悄然离开。(应该说,非池中就是当时他们之中的一员。)
张腾来了北卡,也去了少漫。当时我们和少漫新招的小编们联系也很密切,一个为人非常热情的小编告诉我,说张腾现在过得非常清苦,但是自尊心却非常强,她说见面之后她想请张腾吃顿饭,可是张腾却说什么都不肯。
张腾来北卡的时候,我手头刚好有一个朋友写的故事脚本,后来漫画叫做《飞旅》的,原名其实是《FREEWAY》,因为是奇幻风格的,所以打算找个男生来画画看,给张腾看了,他很感兴趣,我们几个小编也觉得跃跃欲试。因为有了做连载的打算,加上我们人多一起怂恿,总算是成功地请他吃了顿饭,这让我颇窃喜了一下,仿佛觉得自己还是比少漫有些面子(真是没出息的窃喜)。我们在编辑部附近新开张特价大优惠的店里吃了一顿小火锅,很便宜,但是大家都吃得好开心,张腾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我们鼓励他说:“等拿到第一个月的稿费,你再请我们好了!”他仿佛心里有了些底,高兴地答应了。
之后再见面,就是在张腾的住处了。他和一个一起来北京的朋友在回龙观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他的朋友姓金,朝鲜族,也是打算来北京画漫画的,我记不太清他的名字了,就先叫他小金吧。说到画故事,小金的水平还没有张腾成熟,但是也颇有潜力,而且风格有些像mint。因为这样,我们曾经想过介绍他去给mint当助手,然而,虽然他所要求的工资并不高,对他来说只不过勉强可以应付温饱的程度,但对于mint不多的稿费来说,却也非常吃力了。所以终究没有谈成。
来到张腾的住所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或许在看过前面之后大家觉得我在二拨子的生活已经算是清苦了,可是和张腾比起来,那简直可以说是豪华。他们住的那一带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楼房,他们住在一幢二层的小楼,不过与其说是住在二楼,还不如说是住在小阁楼上。他们两个人只有一间房间,四壁透风,门上的玻璃还有裂缝。屋子里除了他们的床和画画的桌子,就没有什么地方了。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我、高二和阿提拉,加上他们两个,在屋子里就有点转不开身。他们有一台电视机,我忘了那本来就是黑白电视,还是因为太破旧所以看不到彩色。还有一台二手的ps,张腾说,他用上一次的稿费买了这个,因为他觉得除了画画之外,他们总还是需要有些娱乐的。这台被他视若珍宝的破旧ps,就是他们全部的娱乐。在那里我第一次玩到了海贼王的ps游戏,还玩得很高兴。他们没有电脑,当然是因为没钱买。所以当我们建议他用电脑上网点可以省掉买网点纸的钱时,他显得很为难,还考虑了一下在网吧上网点的可行性。
他们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我已经记不清他们当时是靠烧煤还是煤气罐来取暖了。当然,做饭也一样。因为吃不起外面卖的东西,所以这两个男孩子每顿都自己做饭。还记得小金一直笑着说,他们两个在家里都没烧过这种东西,特别是张腾,笨手笨脚的总让人觉得他会不小心把炉子弄爆炸。“我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呀~!”虽然只是句玩笑话,却让人听得心酸又害怕。
那时是冬天,屋子里很冷,他们的炉子也不是随时都点着的,因为太浪费。这样的环境要怎么画画呢?我觉得有点不敢想象。我们想过让张腾搬来二拨子,这边的环境似乎还好一些。可是张腾坚持要和小金在一起,而我们那里已经住不下两个人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太不喜欢让别人帮忙了。
在我们从二拨子搬走之后,阿提拉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在燕郊租了一所房子。张腾终于去了那里,我一直以为这下好了,以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地画画。就是那段时间,我和他的联系少了,因为他画得很慢,又回了几次家,我想他画好了之后自然会来找我的,于是放心地去忙别的,放心地等着,直到有一天,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
他说,他已经在广州了。在冬日工作室。
那时我才知道,他在工作室的状态并不好,整个工作室的创作气氛也不好。而他听说,冬日不仅可以提供吃住,还可以提供助手。
那是我在做漫画编辑的四年生涯中,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放下电话之后,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自责得没有办法停止。为什么这么关键的时刻我没有多去了解关心一下我的作者,不知道他的状态有问题。为什么和他配合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有得到他的信任,以至于在决定离开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来和我商量一句。我觉得自己简直失败到了极点。
他太年轻,也很冲动,所以他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个改编自他人脚本的作品来说,距离可以产生的交流障碍是多么致命。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和这篇脚本的作者认识,所以他对于这篇脚本的理解完全要依靠和编辑的交流。他的个性太单纯,但这篇故事出自一个热爱含蓄与讽刺的作者之手,所以有很多隐含在作品中的东西是他那热情单纯的心所无法了解的,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很难独立判定什么要删去,什么该增加。
而我更加清楚,在冬日,上网并不方便,因为他们所有的电脑都是苹果机。而电话也并不是随时都能打进去,因为住在一起的人太多,而且他们的两栋房子距离很远,要找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冬日的作品很少接受外人的意见,等到作品拿到编辑面前时,可以修改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
这篇连载的失败简直已经成了必然。
之后,匆匆开始的连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另一个错误。张腾在广州的创作状态依然持续低迷,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重重。张腾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言辞的人,失去了面对面优势的交流,让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变得充满坎坷。在很多期之后,当我终于欣慰地看到他找到了改编故事的状态时,主编已经下达了结束连载的指示。
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按我的要求提前结束故事,或许他觉得很不甘,当几个月后在《可乐少年》中看到他说“之前的故事被编辑停掉了,停得好!”的时候,那种觉得自己失败到极点的自责让我几乎又要流下泪来。我想心地善良的他已经原谅了我,又或许他从来就没有责怪过我,只是自责自己的能力不足。后来《可乐少年》上也看不到他了,仿佛听说他还在坚持着,继续努力着……
5
最后一篇其实星期五已经写好了,结果在贴的时候网络错误,那么长一篇东西就全部丢失了。当时很沮丧,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在文中我未经允许透露了一些别人的隐私,遭到的报应吧。所以这一篇,我就写得简略一点了。
刚刚看了一个在上海同样做动漫的朋友,李牧羊的blog(参见下面连接“某羊”),原来他也有过同样辛苦的经历。人没有钱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大抵只有两个,一是住处,二是吃饭。对于我们这些朋友还算很多的人来说,没钱交房租的时候总还能想办法借到点,所以只有在吃饭的问题上,大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大家的方法:
前面已经说过了,夏达的方法是泡一碗方便面,一直吃下去,并且多睡觉,少作体力活动,可以节省体力的消耗。
李牧羊的方法则是买两个馒头,蘸酱油吃,或者也可以蘸白糖,实在都没有了,就把剩下的酱油阿盐啊白糖阿的底儿一锅烩一下,然后用馒头来擦盘子。其实这个味道想来应该还是不错的,类似红烧嘛。所以说放羊叔叔实在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好男人。
大家大约还记得北卡曾经有一个小编名叫克克,她的辉煌战绩是可以在除了夏季之外的任何时间吃下几个星期以前的剩饭,经典名言:“米饭 放了几个星期之后上面会长霉,只要把长霉的那一层刮下去,其实下面的饭还是可以吃的!”
不过最值得佩服的还是一个和克克住在一起的作者,名叫毕鸥。她能够只用五毛钱就做出一顿让她和克克两个人都吃得很饱,而且非常美味健康的饭菜来。所以只要她在家,就算再穷,克克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
还有一位曾经在北卡的小编,名叫绯寒,如果去查以前的北卡杂志,大家可以在《编辑部的故事》里看到一个穿着忍者服的家伙,就是他了。他省钱的技能是专门吃土豆。因为土豆不但便宜,而且抗饿,对于一个饭量不小的男生来说,这可比方便面实惠多了。
最后就是我个人的心得,在经历了四年的艰苦奋斗之后,我总结得出的最好方法是:吃炸酱面。面条很便宜,不用说了,而炸酱的秘诀是一定要用东北的大酱,因为这个东西比盐还要咸,只要放一个鸡蛋进去,炸出来的酱可以够我吃两个星期,而且不用搁冰箱也不会坏掉,真是实惠又方便。
最后再来介绍上面提到的几个人。
如果是北卡的老读者或许会记得一篇名叫《指戏》的漫画小说,它的作者就是我在上面说到,和克克住在一起的毕鸥。毕鸥是一个性格温柔,善解人意而且烧得一手好菜的女孩子,最擅长用黑白两色画出惊人细致,对比强烈的建筑背景。《米米》中mint使用的一些背景图就是我们请她帮忙画的,而她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做姚非拉的背景助理。然而,这样一个热衷于伏案画画的女孩子,却有着严重的眼疾。她的视野比我们普通人要小得多,就是我们所谓“余光”的部分,她是看不到的。只要稍微一受刺激或是身体不适劳累过度,她的双眼就会严重充血,甚至有失明的危险。由于这个原因,她曾经一度放弃漫画,但只要病情稍一稳定,她便又再拿起画笔,执著得义无反顾。
执著,这个词在绯寒身上则表现得更加让人无奈。他是一个平时为人温柔腼腆,但有时候却有热血冲动得惊人的大男孩儿,来到北卡的时候,他才只有二十岁。他在北卡待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里,他静静地完成了杂志大部分枯燥的的排版制作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他在距离编辑部很远的地方和陌生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当没有钱交房租的时候,去向房东求情,用他那惊人执著的经历和对于漫画的热诚,竟然感动了房东同意他延期付房租。
他就这样工作了将近一年,怀抱希望和热血,这一年之中,北卡没有给过他一分钱工资,直到最后离开的那一天,他终于拿到了一千块钱,遣散费。于是,他用这笔钱终于缴清了欠下的房租。
我想我是不应该把这背后的故事说清楚的,所以上一次的文字老天都不让我发出来,就让这北卡历史中最龌龊的一幕永远埋藏在我们心底吧……毕竟,过去的都已过去了。
§附录
“国内动画市场很畸形,真正能不能赚钱根本不在于你的作品好不好,而在于你有没有关系能让电视台放你的作品。。。所以不是说能做出好作品来就行的。何况如果没有真正靠谱的人来做,反而糟蹋好东西。
另外子不语在日本连载并不是说工作室推荐了就可以的,不客气地说夏天岛还没那么大面子。。。是日本编辑过来亲自挑选,工作室提供了一堆作品备选,由日本编辑选中了子不语的。”——askask--------金小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