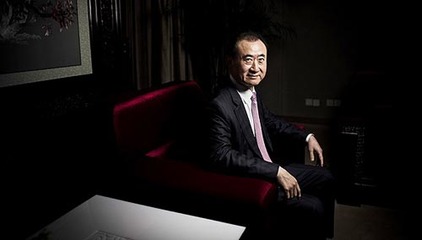全球公民社会:一个概念性考察郁建兴周俊摘 要:全球公民社会是新形势下“全球化”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是区别于公民社会的全新概念,同时又与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并不必然为特定、单一的政治理想服务,而更多的是一种影响价值分配、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既可以为西方利用,也能够成为非西方社会的斗争工具。全球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挑战着主权国家的概念;它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它蕴含着建立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民主秩序的希望,也存在着强化全球不平等的可能性。关键词:全球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主权国家;全球治理;民主“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Society)概念及分析框架的提出可被视作上世纪末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它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炽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论题和“公民社会”(CivilSociety)话语相结合,不仅努力描述现实政治,而且试图通过对全球秩序的重新定义和再阐释以勾勒人类社会的未来。但是,在汉语世界中,人们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认识至今仍十分缺乏,对全球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民主等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更是鲜有讨论。结合全球公民社会的现实发展,对它作出一个概念性的考察无疑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全球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当公民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区别于国家的力量为世界所关注的时候,还不存在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东欧的公民社会运动尽管在后期展开了与西方和平运动的对话,并从中获益,“东西对话”的欧洲模式也逐步形式,但超越国家的公民社会交往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获得合法性。因此,尽管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为主权国家所承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Society)和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Cross),并且到191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已增加到1083个,[1](p.87)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讨论只是到跨国性结社和社会交往成为一种普遍的、对现有全球政治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形式之后才开始形成。[1](p.50-77)本文所要考察的就是以1989年为开端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一处于特定历史场域中的概念。1989年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联系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全球化的性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1989年后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获得了确立。就前者而言,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带有独特的时空和组织特征,在它创造的世界里,全球关系和网络的广泛延伸,伴随着更高的强度、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冲击力,并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从经济到环境,无不受其侵淫。”[2](p.2-3)对此,修尔特(Jan AartScholter)用“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来描述这场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全方位运动。他认为,当前全球关系的最大特征是“超领土”(supraterritorial)、“超越边界”(transborder)或“遍及全球”(transworld)。[3](p.178-179)回顾几百年的全球化历程,“去领土化”确可被看作全球化运动最具野心的追求,尽管它在目前还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1989年是“去领土化”进程中的重要时刻,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促成了冷战体系的崩溃,从此民族国家得以重获主权、重返国际社会,为全球化运动创造了前提;而且更在于它本身即是一种“去领土化”的典范:如果离开了西方和平运动的支持以及东西方对话,1989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可以说,正是中东欧“重返欧洲”的过程开启了全球公民社会活动的舞台,使它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就公民社会而言,很多学者赞同中东欧的巨变是代表“社会”的力量对于代表“国家”的力量的胜利。玛丽·卡尔多(MaryKaldor)对20世纪80年代中东欧公民社会的研究表明,正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汇聚成了强大的“反政治”(anti-politics)力量,最终促成了原有政治体系的崩溃。这种“反政治”也即伊萨克(JeffreyC.Issac)所谓的“造反政治”,它是“反叛性政治”和“非政治的政治”的结合,是“一种自愿结社的政治,它独立于国家,设法创造空间以反对冷漠的、使人软弱无力的官僚结构和法团结构。”[4](p.357)“反政治”的努力是要使国家退出日常生活领域,确保它不干预公民社会,它的矛头直接指向使一切国内国际因素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冷战体系。这种全球性的思维是中东欧公民社会运动的最大特点,而它与西欧和平运动的结合便构成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开端。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公民社会运动史,可以看到,东西欧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开辟了绕过主权国家进行跨界合作的平台,在合作中,和平的话语与权利的话语相结合,一国内部的权利问题逐渐具备了普遍人权的意义,国内公民社会也逐渐获得了与外部社会的普遍联系。这种变化在1989年之前只是潜在存在,直到1989年和1990年,这一状况才获得改变,公民社会的合法地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①]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公民社会是“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的结合。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的话,其前提在于,这里的“全球化”和“公民社会”都是与1989年相关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被讨论了几百年的那些传统概念。如果“去领土化”还没有成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果“公民社会”还没有成为一种跨越边界的斗争策略和手段,那么,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也许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看到,当人们审视过去以及为权利继续斗争时,总习惯于从公民社会理论中寻找依据:将过去一个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将拉美、韩国和赞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对独裁政权的颠覆看作是公民社会作用的结果,将西方国家大刀阔斧的“去国家化”改革也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重建。正是在这种理解中,公民社会得以扩展自身的内涵并提升自身的价值,继而发展为当代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框架。这无疑也是全球公民社会概念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此,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公民社会概念往往以一种政治策略的面貌出现,与这一概念早期所追求的价值和规范有一定的差别。基于这种理解,那种将今天之全球公民社会看作是一度沉寂的西方公民社会全球扩张的复兴的观点便不可避免地遭到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公民社会早在19世纪就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除了利用政治手段进行控制外,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出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模式,比如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礼貌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等。不可否认,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确曾影响了部分非西方国家,但各国在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模式时,更多地是将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分析路径,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为了实现诸如自由和正义等目标而必需采取的(或必须避免的)行为”。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关注权力组织和运动的策略以及对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潜在的)政治得失的制度化限制和机会。不仅如此,全球公民社会的“策略性”途径的规范理解是既定的,即它主要关注获得或建立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方式。[5](p.9-10)卡尔多也认为,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个体得以在全球层次上与政治和经济权威对社会契约和政治协议进行谈判和再谈判的机制和过程。[1](p.78-79)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考量必须看到它所具有的策略性和过程性特征,看到它并不必然为特定、单一的政治理想服务,而更多的是一种影响价值分配以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它既可以为西方利用,也能够成为非西方社会的斗争工具。当前的全球公民社会因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但将它等同于西方公民社会流向全球的单向运动显然已不合时宜。可见,全球公民社会已不再是那个古老的术语,而是一个具有多层内涵的全新概念。那么,全球公民社会到底指称什么?由于它所针对的现实的复杂性,学术界至今仍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定义。星野昭吉的定义是:“它是世界范围内为人类共同幸福而展开的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与斗争的舞台;它是为以实现处于沉默之中的人们以及集团基本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它是把个别的民主主义斗争于更高的普遍人权志向相结合的过程……无论怎么看,全球公民社会都是一种与国际体系权力建构的支配相对抗的、反权力的自主权力建构。也就是说,今天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维护市民社会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在市民社会之间结成的广泛关系基础上建立有法的保证的国际支配。”全球公民社会是由超国家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组成的,它们与其他主体一起构成了世界政治的行为体。[6](p.305-306,307)由此,全球公民社会获得了与国家和国际体系权力相对立的属性,它旨在绕过国家权力实现自主的治理。在非常接近的意义上,卡尔多也将全球公民社会看作个体得以影响国家内外决策的过程,其活动主体是全球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者:全球社会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超国家的倡议网络、公民社会组织、全球的公共政策网络。[1](p.79)与星野昭吉、卡尔多不同,韦普纳将全球市民社会定义为“处于国家之下、个人之上,但又自发地组织起来跨越国家边界的领域”。非政府组织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以不受国家疆界的限制为划分标准,它包括几乎所有跨国运作的组织,从国际科学团体到跨国公司到所有其他跨越边界活动的自愿性协会;其中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市场是全球公民社会运作的重要经济基础。[7](p.181,190-192)修尔特则不同意将全球市场纳入全球公民社会,他认为全球公民社会是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力求影响现存政治秩序的志愿性结合,它包括除政党之外的所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3](p.174-175)尽管相对于全球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努力去衡量的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来说,任何对它所作的思想上的衡量都过于简单和不完善,[5](p.7-8)我们仍然试图整合这些不同意见,从中得出有关全球公民社会的几点基本看法:首先,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渐已形成的现实,它的展开至少依赖于以下条件,一是全球性的议题,二是全球性的结社,三是全球性的交流,四是全球性的团结。其次,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权力相关联的概念。它虽然并不意欲夺取和控制政权,但它以影响国家的和全球性的公共政策为目的;并且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直接挑战着传统的主权观念。再次,全球公民社会的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领域,即私人领域、自愿性社团、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在目前,自愿性社团的活动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尤其引人注目。最后,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化运动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它以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活动,通过各个领域的活动参与全球规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之一。它代表了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秩序的追求,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懈追求的一种公共秩序追求与公共生活信念,即一种集‘生存’、‘利益’、‘命运’等多重意涵为一体的新质的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直接反映”。[8](p.12)在当前,它实际地表现为一种为全球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共同参与的实践运动。显然,全球市民社会已不是一个能够在传统公民社会理论中获得说明的概念。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局限于国家的属性,它的行为方式以及目标追求,它的影响力等等,都无法运用于描述全球公民社会。由此,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能够被割裂开来对待。修尔特、卡尔多、约翰·基恩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全球公民社会的分析起点仍然建立在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其突出表现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及其中尚未解决的分歧大多转移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之中。这一判断至少可以从两者在分析框架上的一致性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对传统公民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袭中得出。公民社会理论的常见分析框架有国家/公民社会二分法和国家/公民社会/市场三分法。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两分法的倡导者,他们特别强调市场体系之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意义。当代学者基恩继承了这种传统,坚持将经济领域保留于公民社会之中;韦普纳也是二分论者,他特别批评那种剥离公民社会商业功能的观点。与此不同的是,许多学者拒绝将经济领域纳入公民社会范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概念有基本相同的涵义,他的“世界公民社会”指称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交往与行动领域。柯亨和阿拉托也坚持使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成为与国家和市场并立的公民社会。修尔特也沿袭了三分法公民社会理论,反对将具有经济功能的组织和行为纳入全球公民社会范畴,甚至建议具有商业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诸如商会和行业协会应被排除在公民社会的讨论之外。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蕴含着公民社会的诉求,同样承载着不同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当中东欧的和平愿望与自由和民主追求相结合时,公民社会就承载起众多的价值功能,它不但是实现各种价值的一种策略,也被看作一种价值目标。公民社会在17和18世纪所蕴含的政治权利要求,在19世纪被赋予的市场功能以及在20世纪被赋予的社会文化功能交织在一起,体现在全球公民社会之中,使其成为了一个无法简单分门别类的综合目标体系。如果对照汉语对“civilsociety”的翻译,则全球公民同时具有“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文明社会”、“公民社会”等不同的涵义。我们可以从公民社会生存的政治环境及其具体主张中找到一些多元价值的例证。比如,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公民社会直接与经济权利相联;在绿色和平运动和人权运动中,全球公民社会则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紧密联结的多元权利主张;在全球性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公民社会意味着对市场霸权的反抗。基恩曾经说过:“全球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没有界限。”[5](p.27)它们在理论分析中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在经验事实中,所有地方的、地域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公民社会机构,无不在相互依存的复杂链条上融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全球公民社会这个庞大的场域。因此,那种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观点应该被抛弃;那种将民族国家内部的、局限于影响国内政策并且从来没有想过借助国际共同体解决地方问题的公民社会排除在全球公民社会之外的看法也应该被抛弃。简而言之,全球公民社会发端于上世纪末,是公民社会运动和全球化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结合。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公民社会的全新概念,同时与公民社会又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二、全球公民社会与主权国家[②]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论述都涉及到了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观点可概括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促进了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互动为特征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体认了当前全球秩序的一些变化,但是否准确地描述了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却有待分析。在“去领土化”和公民社会确立“合法性”的进程中,国家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否选择向全球开放以及选择何种程度的开放,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除了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冷战结束后令人目眩的快速全球化,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运用媒体轰炸和外交谈判的结果,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寻求外部资助以谋求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地,公民社会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也是各国政府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在90年代,许多国家都修订了法律,使公民组织的发展成为可能,这尤其出现在一些后全能主义国家中,如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在其他国家,比如泰国和日本,也对公民组织实施了限制性的许可。[3](p.183)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首先表现在国家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安全和制度空间。[1](p.109)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国家的法律体制所允许,尽管各国都对公民组织的发展设立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在法国,仅仅在1990年就建立了6万多个社团;在巴西圣保罗,有近45,000个非营利组织在发挥作用,而整个巴西有近20万个非政府组织在发挥作用。[9](p.261)在全球层面上,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四倍, [10](p. 229)从1990年的6,000个上升到1999年的26,000个。[11]另据统计,在现有的48,350个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ICSOs)占95%以上,至少在46,000个左右。[12](p.30或者p.28)不仅如此,跨国性交往和行为也为国家所允许。1995年,30万人参加了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3,000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正式会议。2004年,9万人在孟买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其次,国家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许多公民社会依靠政府获得资助,在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中,非营利组织有大约41%的收入来自政府,相对于私人募捐和服务性收入而言,“政府成了非营利性收入的主要来源”。[9](p.263-264)全球性的公民组织也以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资助为主要活动经费。据世界银行报道,过去15年中,世界银行已资助60个国家的100多项社会基金项目,总额近40亿美元。除直接的资金援助外,公民社会还分享着国家提供的其他资源。比如“国际规制就为跨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网络打下了一定基础。国际规制为许多跨国行为制定规范,从而降低了参与者的交易费用”。[7](p.189-190)可以认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部分地源于国家体系的支持,后者提供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和物质资源是前者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然,国家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是有选择的。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公民社会部门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教育和研究、健康、社会服务和文化与娱乐组织。这四个部分占据了公民社会部门近80%的开支。在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组织结构不尽相同,发展组织和住房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9](p.264)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则更多地集中于某些具体的全球议题,比如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清洁空气倡议、遏制结核病倡议及全球水事伙伴关系等。那种单纯以实现公民权利为目标的全球公民组织只在少数。这些事实表明,当扮演一种提供补充性社会服务、帮助国家解决问题的角色时,全球公民社会更可能获得国家的承认和支援。此时,两者之间可以达成一致,并结成友好合作的关系。从国家的视角看,事情更是如此。比如,英国在90年代的福利制度改革中,因向上、向下和向外[③]转移国家职能的需要,主动提出要发展公民社会,认为“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3](p.82)上面我们考察了国家对待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和合作态度,然而,国家在两者关系中的作为远不限于此。杰佛瑞·埃若斯(JeffreyM.Ayres)曾指出,国家可以自由地取舍对待公民社会运动的态度,两种最常见的态度是温和反应和强硬反应。[14](p.35)温和反应常见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会议之前与抗议团体一起举行空洞的咨询会议,这些咨询会议表面是给抗议团体发言权,实则是减少来自反对者的压力,是在为国家从事公关活动。比如,1998年在“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Foreign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FTAA)谈判的公民抗议中,国家的反应是设立一个政府代表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并不鼓励国家和激进主义者之间真正互动,相反,公民社会组织被鼓励将意见投进一个“邮筒”,被告知贸易部长将阅读这些意见。事实上,这些意见并未被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策建议在接下来的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谈判中并没有被考虑。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强硬反应常借助于国家强制力和暴力警察。在1997年的加拿大,大学生集会和平地抗议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他们主要不满对会议的警察保护和印度尼西亚的著名独裁者苏哈托与会。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无视抗议者的宪法权利,向抗议者喷洒胡椒粉。1999年在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千年圆桌会议的国际抗议者集会中,西雅图警方与抗议者起了冲突。2001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针对八国峰会的抗议游行中,一位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抗议者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意大利内务部长对此作出评论说,“国家永远不能丧失对暴力使用的垄断……必须保证高峰会议的安全。”[14](p.37)除了针对大规模运动的显而易见的行动外,国家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监控着公民社会的行为。比如对反全球化者的电话和手机进行监听,拦截他们的电邮和传真。“9·11事件”之后,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大旗下,全球公民社会的活动被合法地纳入到更加严密的控制之中。尽管社会运动仅是公民社会一个组成部分,埃若斯的理论并不能对全球公民社会作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我们从中仍能窥见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的一般关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尚未受到根本性冲击的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主动者和操控者,是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全球体系的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尚没有分享到权力的一杯羹。这一点从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民间社会组织在联合国和全球施政中发挥影响的方式被归纳为三种。一是业务参与和伙伴关系,主要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业务和基层经验,加强联合国项目和方案的范围和效力。二是通过宣传、运动和抗议、对话和协商等多种形式影响政策和政策对话。三是通过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参与管理等方式影响国际机构的施政进程。公民社会的这些功能,用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Edwards)的话说,就是只拥有声音而非选票。[1](p.141)由此可见,全球公民社会远不像许多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已成为多元世界体系中的一元,它的地位仍是边缘化的,它之于国家的关系取决于当它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时所欲求的目标。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将全球公民社会看作一种消极存在,忽视它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所包含的可能性。从经验事实中看,全球公民社会对主权国家构成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它们的倡议,如关于禁用地雷、取消债务和保护环境等问题的倡议,常常能赢得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它们的建议有时也能获得国家的采纳,如在国际非政府组织“饥荒对策机构”的斡旋下,韩国于2004年接受了朝鲜咸镜北道罗先市出口的商品。不仅如此,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结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际政策的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系统内的妇女、儿童和青年、农民等群众组织经常会参加联合国的审议进程。而且,全球公民社会并不满足于影响主权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程,许多公民组织旨在谋求超越国家体系的价值分配方式。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成功地排挤了颁布会计标准的政府间努力,1998年以来发挥了得到西方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可的重要作用。国际商会(ICC)代表了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和协会,它宣称自己在制定管制跨界交易行为的规则中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威”。这些规则尽管是自愿性的,但它们每天为数不清的、金额庞大的交易活动所遵循,并已成为国际贸易结构的组成部分。此外,国际商会还提供国际仲裁法庭,它是世界首要的仲裁机构。[2](p.13) 迄今为止,全球公民社会仍不能完全绕过主权国家行动,但它却展示了在国家或政治权威之外参与、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20世纪的超国家政治发展中,全球公民社会部门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非常明显。[5](p.9-10)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仍然举足轻重,但它现在得到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后者所取代,或者被后者推到次要的位置。[15](p.12)全球公民社会常常能通过与非政府朋友的联合以及向政府间组织求助成功地向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施加压力,它不仅影响着主权国家的价值分配,也影响着全球的价值分配。不但如此,全球公民社会积极有效的运作还促进了主权国家的传统治理模式朝向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主权国家领域内的事务日益具有了跨越边界的特征,许多问题如果不纳入全球视域就得不到有效解决,比如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同时,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也日益增多,比如生态环境和人类和平。如何有效地治理这些问题便成为全球化中的一大课题。在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同时又不存在一个世界性政体的情况下,多中心多层次的治理方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而全球公民社会因其分散性、专业性而被认为是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这种看法当然也基于全球公民社会过去十几年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赫尔德推设的从全球化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全球公民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及其跨国联合和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既起到了促成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合作的作用,也是国家职能转移的主要承接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当然主体之一。[16](pp.68-122)而修尔特更是直接指出,全球公民社会推动了治理的私有化,促成了多层治理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从国家主义的单维度治理向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层次的多维度治理的转变。[3](p.185) 鉴于全球治理与全球公民社会一样,尚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目前还不存在关于全球治理模式的统一认识,因此全球公民社会之于全球治理的确切意义,尤其是它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仍难以确定,至少还不能肯定全球公民社会因其与国家的合作而必将取得与主权国家相平等的地位。与赫尔德的看法不同,也有论者假设了全球公民社会与主权国家的对立而非合作关系的关系。但是,无论什么模式的全球治理,即使在合作关系的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社会从本质上仍是否认国家的优越地位或其主权性的。[6](p.177)现实中的全球公民社会用来支撑自身发展的自主、自治、权利、民主等信念和口号无不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而每一种对全球治理的构想都意味着要分散决策权,弱化集中的政治权威。总之,无论是从经验现实,还是从理论推导来看,全球治理和全球公民社会是两个互相依赖和强化的概念。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曾经指出:“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 [17](p.272)全球公民社会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有力地支撑着这一论断。国家尽管仍主导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规制着它的前进方向,但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及其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都现实地挑战着主权国家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挑战不仅仅是现实的,更是潜在的:全球公民社会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对全球秩序的影响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得以展开的可能性。三、全球公民社会与民主修尔特在论述全球公民社会的效应时指出,全球公民社会促进的不同形式的发展都涉及民主概念和实践。传统的“民治民享”只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统治,但在今天,治理超越了国家,共同体超越了民族,公民身份超越了民族的权利和义务,诸如参与、协商、公开讨论、代表性、透明度和责任性等问题如果仅仅在领土内的机构或共同体中就难以获得解释。全球公民社会扩大了民主实践的范围,它创造了别样的大众参与渠道、大众协商模式、大众讨论论坛,创造了大众代表与选举议会和立法者的新场所,以及要求公开、负责任的治理的新的大众压力。这些创造使公民更近距离地接触了区域的和世界的规制代理机构(regulatoryagencies)。这即是说,全球公民社会与存在于当代政治中的许多民主赤字正好是相反的。[3](p.188-189)修尔特的上述观点极具代表性,多数全球公民社会论者都赞同将全球公民社会看作弥补主权国家民主赤字和全球治理民主赤字的重要工具。如卡尔多就认为,全球公民社会意味着新民主,全球治理的框架和一个积极的全球公民社会为不同层次的参与提供了可能性。[1](p.110)从历史上看,全球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民主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西方,干预式国家在石油危机爆发后成为众矢之的,失业、贫困等问题都被提升到与公民权相关的高度。在嗣后的改革中,民主是核心概念,而公民社会则扮演了重要角色。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在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首次提出治理和善治概念后,它更以治理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指导,而治理的基础与其说是在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和公民社会。[18](p.326)新左派政治以“制度”而非技术的思路来化解福利国家面临的全球化风险,其理论核心也在“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即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13](p.73)这一时期,从非洲到东欧、从亚洲到拉美的诸多国家也走出了单纯对“人民统治”理念的追求,逐渐将参与的观点引入民主,使自决和自主的概念与民主相衔接。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国家的反应汇聚成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卡尔多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无论是西方对干预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反应还是东方对家长制国家、威权主义和战争国家的民主反应;无论是表现为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吁求,还是表现为对道德、自治和个体责任的关注,针对国家的反应都强调个体主义,不但要求提高个人作为个体的参与权,还要求提高国家作为个体的参与权。[1](p.113)卡尔多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世界性民主化进程,指出它是一种针对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运动;更重要的是,对权利的关注不仅带来了主权国家民主的变化和发展,也开启了全球民主的建构。如前所述,日益增多的全球公共事务要求全球性的共同治理,但是共同治理的代表性、透明性和责任性从何而来?一个积极的全球公民社会被认为可以对此作出回答,因为单是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这一事实就预示着一种全球民主的来临,如米克什·马绍尔所说,“公民参与承载着自生自发的合法性”。[19]可以看出,对国家的反应、对民主的吁求是促成全球公民社会成长的直接原因,而随着它的日渐壮大,必然对政治权力和民主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讨论,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出发,经由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最终必将聚焦到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全球公民社会之于民主的意义是预示着一场世界性变革的核心因素,它对民主的新理解直接地触动了传统的政治认同,对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构成了最根本的冲击。换言之,全球公民社会之于民主的意义与其说在于作为一种手段以弥补传统民主的不足,不如说它本身即代表着一种替代国际体系的民主化世界秩序的未来。赫尔德曾经指出:“国家的民主体制如果想在当代得到维持和发展,就需要一种国际性的世界主义民主。”[20](p.24)这即是说,主权国家的民主化和世界性的民主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着转型的过程,而后者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尤为突出。哈贝马斯在研究欧洲民族国家的福利危机时也曾指出,在全球性的政治实践中福利国家转移职能的任务不可能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完成,而必须存在国家职能向上运动的过程,而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一个“世界公民社会”是全球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那么,这种全球民主是什么?它与全球公民社会关系如何?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过时论”、“民族国家终结论”等理论。这些理论对主权和国家功能变化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无不认为国家已经掉进了全球性相互依赖的天罗地网当中,深受跨国关系和力量的层层渗透,如果不借助国际合作就越来越不能履行其核心职能。比如罗西瑙认为,世界正经历着三个根本性的变化:从传统国家中心的无政府体系向一套新的多中心世界的两极格局转变;曾经在世界政治中显赫一时的权威已岌岌可危;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标准的改变。[21](pp.325-328)罗西瑙通过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概念,构想了全球秩序中国家体系与非国家体系并存的二元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全球秩序的民主化依赖于社会联系和社会参与,“通过在相互作用中加强社会力量,它将为民主化的实现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21](p.308)受罗西瑙影响,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内格里(AntonioNegri)提出了“帝国理论”。“帝国”区别于传统的帝国主义,它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帝国通过指挥的调节网络管理着混合的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22](p.2)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帝国首先是继民族国家的主权之后接踵而来的一种新型主权。它通过单一的主权原则把三种古典形式的政府——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合而为一而取消了这三者的相互更替。其中,一些强势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常常体现出君王般的权力;当少数国家联合行使其权力时,贵族制表现得昭然若揭;而当民族国家并没有足够资格代表他们的人民退而诉诸非政府组织时,帝国就成为具有民主制或者代议制特点的制度。[23](p.168-169)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正在于它是帝国民主制借以实现的载体,与其他的力量一起共同支撑着帝国主权。无论是罗西瑙的二元格局还是哈特等人的“帝国”,实际上都是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状态,强调代表、分权、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以及通过协商进行统治。这与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的精神是一致的,代表着自由主义的全球民主理想。这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多元主义有助于实现更为有效的代表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透明度和责任性,但它仍无法解决困扰着全球治理的民主不健全问题。正如安东尼·麦克格鲁所指出,民主多元主义既忽视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又忽视了全球资本与全球公民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失衡;它不愿意承认,权力的不平等往往使得民主成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24](p.144)从质疑自由主义的全球民主模式出发,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和韦普纳等人的草根民主(或称为激进多元民主)理论都试图破解权力不平等问题,以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民主模式。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以其著名的全球治理理论为基础。全球治理理论力图发展一套管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的新规制和新机制,强调管理就是合作,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惟一源泉,公民社会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理看作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态。[25](p.35)全球治理依赖于多元的决策主体,是一个政治权威和权力中心相互交织的体系,其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地位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赫尔德强调:“如果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区域性的政治组织等被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含义之外,那么,全球治理形式的动力将得不到恰当的理解。”[16](p.7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贝克(GideonBaker)将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看作全球公民社会的模式之一。[26](p.117)具体而言,赫尔德认为民主必须服从全球化变革对国内和国际权力中心的影响,“不然的话,民主在决定政治活动的样式和界限方面就很可能变得越来越缺乏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形式与结构,必须被构筑到民主思想和实践的基础当中去”。[20](p.143)为此,他构想了一种全球新秩序:“在区域性和全球性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只有当所有其他各种行动、政策和法律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交织的共同体都作出承诺时,人们在自主性方面的共同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护。因为,民主法若要有效,它就必须国际化。于是,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就在于实施世界主义民主法和建立世界主义共同体——所有民主社会的共同体。他们有责任建立政治行动的跨国性共同结构,这一结构本身就能够最终为自决的政治提供支持。”[20](p.245-246)此即世界主义民主。其中,自主性被视为民主的核心,它是在七个权力位域[④]中充分实现的自主;而民主法则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它设定了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在世界主义民主模式中,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依赖于各共同体建立一个联合的规则体系,全球公民社会受制于世界主义民主法的广泛框架,它既是治理主体也是客体,本身并不具备一个自治的、积极活动者的身份。[26](p.117)用赫尔德的话说就是,“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展来解决”。[20](p.300)这种观点仍属政治中心主义。世界主义民主想要超越国家主权,但在其理论中,国家仍是实现其建议的惟一行动者。这体现出“自上的”全球民主模式实际上在用国家主义模式思考公民社会问题,它预设公民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需要生长于一个既定的权力构架之中。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必须在世界民主之前产生,以作为全球秩序的司法者,但这样一来,全球公民社会又会陷入与政治权力的契约关系中,再次出现代表性问题。同时,因为“自上的”世界民主所依托的全球治理并不基于传统的领土权威和政治权威,而是基于对议题的处理,即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如何选举代表对议题做决策,尤其当议题的边界频繁变动时?这些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治理的“代表性”难题。[1](p.140)“自上的”世界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还在于,它较多关注如何有效治理全球公共事务,而对多元权威如何联合以及每种独立权威的民主化问题缺乏兴趣。草根民主理论关注全球公民社会本身,关注外在于国家和国际法的政治行动方式及组织运作方式,这与世界主义民主的国家视野形成了鲜明对比。[26](pp.117-119)该模式认为全球民主的建立与其依赖于国家的主动建构,不如从业已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寻找动力。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韦普纳曾指出,全球公民社会具有建构全球秩序的功能,它的影响总是能波及到全球生活的制度:首先,由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多样性,规范集体的制度就可能因之而在无意中产生。全球公民社会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对世界政体施加了影响;其次,通过对民族国家施加影响而使相关政策制度化;再次,通过激发国家体系之外独立运作的治理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7](pp.194-197)草根民主的另一股力量新葛兰西主义则看到一个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它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一起构筑了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全球公民社会的民主意义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阵地,是弱势力量寻求保护和变革的途径。草根民主模式试图通过存在于全球公民社会中的分散的多元权利对抗政治霸权,实现全球秩序的民主化。然而,这种“自下的”民主忽视了全球公民社会自身的“民主赤字”。基于各种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极不平衡的体系。如果遵照两分法,将经济纳入全球公民社会,则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主导着跨国公司;从全球性公民组织的数量来看,西方远远多于东方,北方多于南方;从全球性交往和网络来看,一些国家甚至根本没有参与进来。不但如此,全球公民社会因其与国家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其独立性和代表性都值得再思考,而全球公民社会与资本的微妙关系也使其所蕴含的民主意义变得复杂。正如赫尔德所说,全球公民社会的民主背景非常单薄,“全球政策进程的许多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全球公民社会的主导实体,也根本代表不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2](p.21)更重要的是,“自下的”民主模式并不能回答目前依然很弱小的全球公民社会如何才能获得对抗政治权力的地位以及如何穿透政治构架等问题。另外,这种民主模式更多地强调全球性伦理,强调道德和知识权威,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尚未锻造出最基本的内聚力之前,这必将导致更大的冲突,放任的全球公民社会甚至可能会重返霍布斯所谓的丛林状态。从上可见,自由主义的全球民主、世界主义民主和草根民主模式都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它们更没有明确指出达成全球民主的具体机制。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全球民主完全没有发展前景。众多的设想实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此为基础就可能生长出一种更加完善的全球民主理论。当前,一种被称为协商民主的全球民主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它为全球民主的实现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协商民主起源于哈贝马斯的第三种民主模式,又被称为程序民主或话语民主,它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种合理的语言交往条件使政治的进程可以预计并且得到合理性结果,其出发点是政治活动的走向,也即从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出发,从形成构建意见和意志的普选活动和议会决议过程出发,所要实现的是一个非集权化的公开政治的构想。[27](pp.279-292)协商民主“既不低估对于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自由依恋的价值,也不低估建造世界秩序的民主宪法的世界主义式的要求”,[24](p.151)但它更强调一个开放、理性的全球公共领域对于民主建设的关键意义,因此它更多地授权予全球公民社会。协商民主关注自由、规制、理性和积极的表达,尤其重视民主程序;它强调协商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过程。这与哈特和内格里所构想的斯宾诺莎式的“绝对民主”——没有任何界限,也不可度量,它不仅属于平等的个体,而且属于对于合作、交流、创造都平等开放的各种权力[23](p.172-173,175-176,182)——极为相似,但更加明确。协商民主理论为全球民主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这一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许多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忽略了对话各方的差异性,也没有回答一致性如何达成以及权力在对话中的地位等问题。劳伦斯·汉密尔顿(LawrenceHamilton)更指出,以同意作为民主化的核心要素,必须追问构成对话基础的各种需求是如何形成的。他认为,特定的体制造就了特别需要,因此,民主化的第一任务是重建需要和权利体系。[28](pp.69-80)但协商民主理论明显忽略了这些问题。总之,全球公民社会虽然蕴含着民主的希望,但如何突破当前的民主局限迈向全球民主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索的课题。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全球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全球公民社会纷繁复杂且影响巨大,它有着多元的目标体系,追求影响国内和国际的价值分配;它依赖于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但又积极地影响着全球秩序,意在建立一个多中心、多层次的全球治理结构;它蕴含着世界性民主秩序建立的可能性,但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它也可能强化全球不平等。深入认识全球公民社会,努力使其朝向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参考文献:[1]Mary Kaldor,Global CivilSociety:AnAnswerto War,Polity,2003.[2]戴维·赫尔德.《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JanAart Scholter, Global Civil Society,inNgaire Woods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Globalization,Macmillan,2000.[4]Jeffrey C.Issac,CivilSociety and the Spirit of Revolt,inDissent,Summer,1993.[5]John Keane,Global Civil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3.[6]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保罗·韦普纳.《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治理》,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袁袓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2至19页。.[9]莱斯特·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转引自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与多部门关系》,载约瑟夫·S.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1]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中文网页:http://www.worldbank.org.cn[12]转引自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0至32页.或者:转引自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Jeffrey M.Ayres.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 No Swan Song Yetfor the State. in Gordon Laxer、SandraHalperin.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Its Limits. PalgraveMacmillan, 2003.[15]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6]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7]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米克洛什·马绍尔:《从国家到人民:公民社会与它的治理功能》,http://www.tszz.com/data/log/03/030101/pangjinyou01.doc.html[20]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内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3]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内格里.《全球化与民主》,载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希瑟·高特内主编.《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4]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5]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6]Gideon Baker. Civil Society andDemocratic Theory: Alternative Voice. Routledge,2002.[27]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载《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Lawrence Hamilton.“CivilSociety”:Critique and Alternative,in Gordon Laxer、SandraHalperin. Global Civil Societyand Its Limits. Palgrave Macmillan,2003.作者简介:郁建兴(1967-),浙江桐乡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俊(1977-),湖北鄂州人,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承认公民社会的合法性不等同于承认公民社会所有形式的合法性,不等同于所有来自公民社会的力量和行为都为国家所允许。比如对非政府组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管制方法。公民社会的合法性只是意味着国家承认公民社会这一客观存在,并且承认它有自己的活动领域,而这个领域是国家权力不能随意侵入的。[②]民族国家一词一直以来都用作指称国际社会中拥有主权身份的行为主体。但是当前活动于国际社会中的具有独立主权的行为者并不总是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常常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与其称其为民族国家,不如称其公民国家,以突出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联结特征。本文讨论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侧重于公民国家外部身份的考察,故统一采用主权国家这一概念,只是在征引他人论著时保留民族国家一词不变。[③]在当前各国的政府职能调整中,一般有三个向度的运动:向上转移至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向下转移至地方政府;向外转移至公民社会中的组织或机构。[④]这七个权力位域分别指人身、社会福利、文化生活、公民社团、经济、对暴力和强制关系的组织、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领域等。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5/283763.html
更多阅读

1994年,《全球公民社会》的作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以下简称萨拉蒙)指出:“事实上,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已经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大量的有组织的私人活动和自愿活动的高潮。”十八年过去了,历史已证实了萨拉蒙教

有人说看过<集结号>就不再相信领导,看过了<投名状>就不再相信兄弟!我觉得他们只看到了片面。<集结号>中我看到了那有情有义的谷子地,<投名状>中我看到了金城武为了信义而不顾一切的捍卫誓言。这世事都有两面性,看你如何去看待人和事,朋

“风险社会”一词因20世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教授的名著《风险社会》而滥觞。贝克以“风险社会”称呼一个时代——后工业社会时代。贝克以北欧尤其德国的发展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后工业时代的特点是“风险”,因此将其称为“风险社会

最近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营养奶昔风暴,到处都是:“健康的一天从一杯奶昔开始!”“健康减肥,办法问我!”“今天你喝奶昔了吗?”等等口头语!那营养奶昔到底是什么呢?一个字“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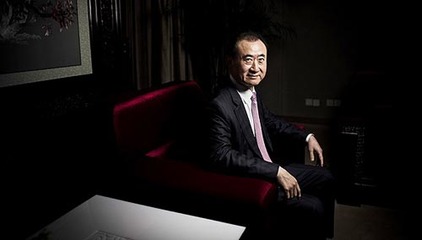
对于企业家、富豪们来说,手相的看法也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头脑线常常与生命线相交会一段距离后,慢慢往下弯一些,(比一般人多向上走一些)这样他们大多便是属于谨慎从事的多,但这与平常人没几多两样!许多企业家都带有文人色彩,这说明在当今这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