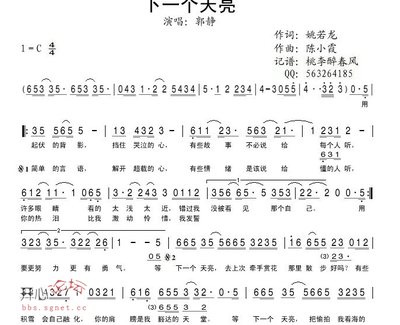“下一个平衡,归根到底,在人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把自己跟自然的关系搞定了,地球就搞定了。”7月22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在北京“一席”讲座上分享自己近30年来研究和保护故事的片段,探讨《下一个平衡在何处?》。以下为讲座实录:
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下一个平衡在何处?》。假设是,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平衡——在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我是做自然保护工作的,说到保护自然,总会有人问,你们怎么保护自然呢?自然听起来是个特别大的事情,几个人怎么保护自然?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们也在常常问自己。
说到自然,说到野生动物,说到熊猫,大家自然想到的是看到BBC纪录片那样的感觉,非洲的原野、大规模迁徙的野生动物、浪漫的野外生活……
我当年最早去野外的时候,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我现在还记得85年第一次到野外时的那种兴奋:在大雪中,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到林子深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在野外生活确实经常令人非常兴奋。我当时在北大生物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实验室的工作,一个是去野外——去野外其实是我自己拼命争取来的。在实验室工作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加一些什么化学物质下去,它应该产生什么东西。但野外是不同的,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今天会看到什么。你处在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下,即使没看到什么也会是“唉呀,光线真好啊”,或者是“这光线跟昨天不同啊”,让你自得其乐一阵子。
但是很快,这种兴奋——其实是很肤浅的兴奋——就被焦虑所取代了。呵,还是应该展示一个熊猫的照片,有时候会意想不到地看到熊猫,看到熊猫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有些科学家几个月没有看到一个熊猫,但是我稍微幸运一点儿,到野外一个星期就看到了四只熊猫。但是这种兴奋很快就被焦虑所替代。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林业局做熊猫研究,国家给林业局下达了采伐任务,当时的作业方式是择伐,采伐后剩下40%的树,让森林能够持续地恢复起来——国家在森林采伐上,其实是有可持续林业的概念的。采伐过后的森林仍然能够看到有熊猫出现,甚至有的时候竹子长得更好,因为竹子是喜阳的,有更多的阳光,竹子就蔓延的更快,熊猫也会常常到这儿来吃东西。我们当时还写了一本书说,熊猫可以和森林采伐共存,但是没想到我们是toonaivetoosimple。90年代市场经济开放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这才意识到以前是计划经济,采伐多采伐少没什么区别,多干没有多挣钱,林业局就按国家规定40%的树留下,采伐、销售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
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以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力量,确实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环境的代价。其实我们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背后都有这样的景象发生。怎么办?我跟林业工人住在一起,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从来没觉得他们是不好的人。他们都是周围农村来做工的,要养活家小,砍一棵树挣来的钱就有可能让上学的孩子明天多一点吃的东西,或者多一点文具。砍树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有错的吗?这是我当时回答不了的问题。
我也曾经跟我做研究时的野外助手走了120里山路到他家去吃哥哥的酒席。走了一天很累,第二天一早,村子里人声鼎沸,大人小孩都在叫,我好奇,赶紧爬起来看,发现一只毛冠鹿被全村的人堵在一个角落里。而这个毛冠鹿是一个怀孕的母鹿,不知道怎么跑到村里来,大家发现了以后就追杀。我看见的时候它已经不行了,倒在地上嘴里吐着白沫,要流产的样子,我心里很不忍,就想是不是应该去劝一下。我正准备往前凑的时候,就有村民说你可真有福气,来了就有肉吃。我当时一下就语塞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村子非常贫穷,他们一年可能就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猪,吃到一次肉。吃一点儿就挂在房上腌起来,味道越来越不好闻,但是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会切下一条来给客人吃,小孩子也会眼巴巴地盯着客人的碗。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鹿被当成肉来吃,有没有错?这些问题是我当时研究大熊猫、做论文回答不了的问题,一个科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所以我开始琢磨保护应该怎么做。
显然,保护是远远比制止人们砍树、制止人们打猎要复杂得多的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才能做到不砍树、不打猎而人们也能够满意地生活?林业工人和我关系都挺好,而他们最让我苦恼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始终问我的一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们从北京大城市跑到我们山沟沟里来,又冷又饿,吃不好住不好的,为什么?”我说熊猫挺好玩的,每天跟着熊猫看它们跑来跑去,研究它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生小孩、种群怎么扩大、碰到什么问题,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对方说)“没看出来哪里有趣。”
那么,墙上的标题写的也很明白嘛,“保护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这句话其实我自己后来也都说不出口,因为孩子一定要上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怎么能跟人解释我们为什么来这儿,说出来的话显得特别虚,你跟当地的生活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没办法用语言说得清楚。
后来媒体发现了我们,大家刚才看到我的名字后面有一大串这个奖、那个衔,这个是跟熊猫来的,其实跟我个人没太大关系,因为所有人都喜欢熊猫,所以有媒体追着来报道、采访。这时林业工人们说,“你早说嘛,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这个我们能理解。”(我)就更苦闷,更不想说了。这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是一个困扰,在更大的层面上也是一个困扰。
后来我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在熊猫最多、采伐最厉害的一个县,让采伐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当时想寻找一个替代的生计,就是生态旅游,90年代的时候生态旅游在中国还非常少。我们在四川平武县这条山沟做非常细致的调查,哪个拐弯上有一颗杜鹃树,哪个角度看起来前面的村落和后面的雪山是一个非常适合看的风景……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培训人,把这个地区所有值得了解的信息和看的东西以及背后的知识,包括地质、生物、历史、文化的都捆在一起,成为一个能够向外面的人讲解的一个个故事。
但是没过几年,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平武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伐是停止了,但水电开发开始了。这一轮的开发比采伐挣了更多的钱,但是所有我们当时设计这条线路上出现的景色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伤心,几年的心血还抵不上一个推土机。
这是我们在做保护的时候面临的真实情况。所以经常很灰心,甚至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与人性违背。因为所有这些,水坝也好,砍伐也好,打猎也好,都有非常合乎情理的逻辑在后面。我们能够撼动那个逻辑吗?是不是需要撼动?不撼动那个逻辑是不是没有办法保护?
沮丧的心情到了90年代,开始露出一线阳光。这时我开始到西部的藏区,在调查野生动物时经常会听到当地的林业局官员说,我们这个地区有50多个保护区。怎么会有50多个保护区?西藏有十几个保护区,我们都很清楚它们在什么地方。他说,有一个是国家的保护区,还有50多个是我们老百姓保护的神山。
神山是怎么回事儿?右面的这张图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是圣湖里的鱼,它从来没有被当作食物对待,它不知道被吃的危险,反而人走近后它会靠近索取食物,你可以拿手去摸这些鱼。这样的景象对于一个做自然保护的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实现它的不是法律,也不是我们这些以做自然保护为职业的人,而是神山。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个项目来了解神山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发现它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行为上仍然在实践。它是一块地,同时也是人的心里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这块地上有各种禁忌——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这禁忌时间长了以后,不需要警察,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督,已经成为人们自律的行为。这种情况,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在藏区我们到处走,跟老百姓讨论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山沟里来、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
其实非常简单,在当地的藏族人看来,保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人跟自然、跟其它生命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超越的,生命是轮回的。所以你要踩了一个虫子,也许是踩在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亲戚身上,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件事情。而神山上面居住着山神,这些山神是神灵,有的脾气好,有的脾气不好,有的小心眼,你要违反了神山的规定,他就可能会来整你,让你生病。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藏区看到有人生病了说,“我是因为在水源上撒了一泡尿,可能来惩罚我了。”或者是家里的牛羊被雪豹吃了,问怎么办,回答说“那有什么办法,它们是食肉动物。”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不同的。
而这样的震撼对我来说真正是一种教育,因为我自己原来到一个地方跟别人,跟当地的官员讨论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是抱着一种道德优越感。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吃肉、砍树,虽然你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做,但心里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很无力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说法,来改变这一切。而我们是想改变的,拼命想改变但是做不到。
但在这个地区,已经发生的事情,才让我真正地第一次意识到,保护原本就不是什么外来人、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的事情,而是当地人的事情。这里面蕴含的根本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当你看到这个老太太一心认为这个红嘴鸦是她过世的女儿转世的一个生命,眼睛里散发出光芒的时候,你不由得受她的感染,会跟她站在一起。这样的力量,是在我生长的环境里,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个时候让我意识到——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是蛮努力的,得了那么多奖,但是——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实际上非常狭隘,局限于我所受的教育、出生的地方、交流的语言、所读的东西,有这么大的世界我们没有认识。而答案也许在这些地方。
保护自然的科学道理是非常清晰的,人们已经说了上百年,生态系统是生存的根基、没有它我们人类也无法生存下去、地球会被毁灭、所有生命都会消失殆尽。但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跟人内心没有建立联系的话,说给谁都说不通。而这个联系的建立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沟通。在藏区,人们把自然看做是对生命的保护,是文化、精神的依附,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联系,就可能让自然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呵护的东西。但是在其他地方怎么办,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信藏传佛教,都来信神山这个体系。
因为藏区的特殊性和文化根基,我们开始把老百姓做保护这件事,变成一个方法,希望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成为保护的主体,让国家、外界能够认识到他们所保护的价值,从而让他们从保护中受益,通过国家各种各样的生态补偿——除了精神的需求,藏区老百姓天然有这个东西。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保护的各种补偿和投资,应该落到这些人的头上。这是我们正在尝试的事情。
那藏区以外怎么办呢?价值是多方面的,事实上自然被轻易地破坏,是因为它高昂的价值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在美国有人估算过,如果把一棵树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保护水源——这都是人们生存必需的依赖,以及保护水土、调节气候、提供美好景色等等这些价值都算下来,一棵树应该是20万美元。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砍一棵树要付20万美元的话,那所有砍树的人可能都会犹豫,被砍的树就会少很多。
这样的价值,目前还非常少被市场认可,但是有没有可能让市场更向前走一步呢?人们很有创造性,创造了那么多的金融产品,互联网游戏有Q币,等等。我们创造那么多非实体的商品,为什么生长在树里的这些价值,不能够变成商品呢?这是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东西。
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熊猫蜂蜜。用一瓶熊猫栖息地产出的蜂蜜——而蜜蜂是由当地的老百姓养的当地土蜂——这个蜜不仅是一瓶好蜜,而且把城市的消费者和熊猫栖息地连接起来,而收入成为熊猫栖息地老百姓参与保护所需的经费和他们发展跟环境不冲突的其它生计所用的基金。这瓶蜜就变成了一个媒介,它的价值除了蜜本身以外,还有人们保护的服务。人们的保护带来的是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良好的森林,这个价值是不是能够从这瓶蜜上得到市场的偿付?所以这瓶蜜从5块钱卖到现在500块钱,希望你们下次看到不会吃惊,因为它背后有这样的价值在里面。如果一棵树是20万美元的话,这样一瓶蜜500块钱支撑的是一个村子用来保护熊猫的行为、服务,还有他们的生计,恐怕这不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
也有一些新的商品在被创造出来,比如说种树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树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二氧化碳,树除了可能为熊猫提供栖息地以外,在关注气候变化的情景下,树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回去,实际上是减缓了气候变化的进程。每年因为气候灾难要损失多少钱?如果说地球上森林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就会增强,带来的灾难会减少,我们是可以算出这个价值的,市场上也已经开始创造出“碳汇”这样的商品。所以这样的一些新的生态友好的商品或生态产品,有可能在更广大的区域把生态的、自然的价值转化成为人们的收入。这样的体系如果一旦建立,自然保护才是有希望的。
这张图显示的是中国我们现在知道的几百个濒危物种出现的地方,集中在中国的西南、青藏高原东缘这一带,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区域。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因为栖息地仍然在下降,包括熊猫的栖息地。在98年国家发布了禁伐令以后,我们想熊猫应该是安全了,但是事实上熊猫最好的栖息地仍然在不断地后退。虽然我们国家森林面积看起来在扩大,但是好的、天然的森林面积在不断地下降,因为人类的开发速度实际上更快了,更多的路修进去,更多的人涌进去,开矿、城镇化……等等,我们最好的自然在消失,而很多物种越来越没有生存之地。
要让这张照片上这样一个和谐的情景出现——这是当年我做研究时,熊猫对我们很熟了,当地林业工人看录像的时候,它来了——这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我的题目是,下一个平衡在何处?我特别喜欢这张图,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是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这个蓝色的星球到目前为止,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大家都很清楚。我跟一位天文学家讨论过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NASA也在不断发布新闻说快了。我问他有多快,他说快的话,人到那里恐怕也得100万年的时间。100万年人们还能不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坚持下去?我们真的是很孤独了,如果自己不把这个地方搞好的话,我们没有出路。
所以,这下一个平衡,归根到底,在人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把自己跟自然的关系搞定了,地球就搞定了。谢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