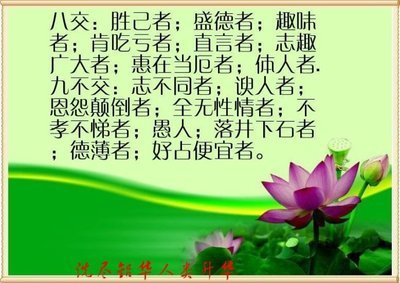前些天写了关于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一文,今又觉得不过瘾,特写下这篇文章。
曾国藩的一生无论从政交际还是带兵打仗均以一“谦”一“隐”一“诚”三字取胜。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谦”。曾国藩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守缺”的观点。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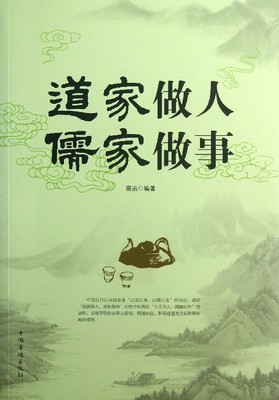
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经过默默的咀嚼,终于大彻大悟。尤其是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水能屈能伸,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地方。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和涵养,其深沉和宽厚。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至此,曾国藩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宁静谦退之心境。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忍”。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去长沙读书,当时他的书桌是放在窗前的,后来有个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一天他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近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曾国藩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这位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曾国藩来到没说一句话,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此人又来寻衅,气呼呼的:“你读书的地脚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在旁的别的同学为曾国藩打抱不平,问道:“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吆二喝三的非要换过来的吗?”这位同学无理取闹的说:“所以呀,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别的同学说:“那好啊你在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众人哄堂大笑,这位同学一脸狼狈,曾国藩在旁始终和颜悦色的听着。
在唐浩明著的《曾国藩传》中也多次提到,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最著名的,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他谆谆告诫道,“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我们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其“诚”。曾国藩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处世立人的不二法则。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身边的人。在写给九弟曾国荃和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之中,他说,“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在写给下属的另封信中更是强调,“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可见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人,以至于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甚至连号称忠王的李秀成也叛变了(在民间野史中记载,李秀成的投敌实为太子逃跑争取时间,可信度不大)。对于曾国藩的“血诚”之举,后人蔡锷极为认同:“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的一生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有荣有辱,虽没有平步青云,也从没有掉进深渊。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与曾国藩的一生坚持“诚”、“谦”、“忍”的原则有重要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