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山区的印度教僧侣 匆匆行走中的印度教化缘僧
“化缘”这个词来自于佛教传译中国之后,原本指释迦佛陀度化众生的因缘,后来流于俗化之后,几乎成了社会生活中一方向另一方无偿募化的特指名词。僧尼道士对信众的食物或财物募化叫“化缘”,平常人向朋友讨要物品也可以说是“化缘”。“化缘”虽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我们并不轻易向别人“化缘”,也不太看得惯别人的“化缘”。但在印度则截然相反,这里“化”与“被化”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印度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是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信仰,各种信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形态各异的宗教。所以,在印度,最常见的是各种庙宇。修庙需要钱财,可僧与庙本身都不具备生产能力,于是就得向民众“化缘”。在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庙宇,都会看到大量的功德芳名录,记载的都是修庙“化缘”时人们的捐赠数额。
印度寺庙的规模与穷奢以所在位置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一般来说,富人区的庙宇最奢华壮观,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次之,贫民窟的最简陋。但无论社区富裕或贫穷,庙宇都是一样地多。像中国一个村子或城市小区那样大的一片聚居区,至少有两三家寺院,多的可达四五家,这还只是指同一种宗教信仰的,若再加上不同信仰的宗教活动场所,那就更多了。僧多粥少要“化缘”,庙多人少也须“化缘”。相对而言,知名的大庙或以中产阶级以上阶层为主的聚居区的寺庙,“化缘”起来比较容易,不用任何人员外出操劳,只需把布告在庙内外一张贴,大把的钞票自然就来了。而那些处于贫民区的神庙,由于本区的资财有限,无论出世的僧侣还是处俗的庙祝,都要亲自出去“化缘”。
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邻近一个下层民众的贫民区,那里的庙十分简陋。路边搭一个小棚子,里面塑上几尊神像,摆上炉台供品,这就成了一个庙。庙虽不大,却还有一个庙祝在照看着。那个庙祝每周都要到我们小区来“化缘”几次,相当勤劳。而且每次“化缘”,不是清晨就是傍晚,为了让人知道他来“化缘”了,每走几步就要吆喝一嗓子,粗重的嗓音在安静的小区里非常具有穿透力,关着门都可以听到。一开始我以为是卖菜或收废品的吆喝声(这里民间市场很活跃),后来看到他一走过来,人们纷纷递钱过去,才发现是“化缘”的。看来,有钱人家不仅要供养本地的庙宇,还得照顾穷人的神灵。
印度人的“化缘”方式层出不穷,除了张榜贴告和走村串户,还有很多中国人想不到的方式。比如,有点上油灯端坐街头,旁边放一个盒子等着人们送钱的;有提着小筒四处流动,找人要银子的;有捧着神像,逢人便伸手乞讨的;有敲锣打鼓,挨家收费的;当然,印度教与耆那教那些手捉锡杖、浑身涂满颜色、或着装或裸体“化缘”的僧侣也随处可见,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缘”者的世界。
所有的“化缘”类型中,要数拉着猴子或牵着牛“化缘”的人最有意思。他们要是上了门,不达到目的是不会轻易离开的,猴和牛都是印度的神物,你可以不看人的面子,总不能不给神的情面吧?再者来说,这些个“神灵”不讲人的规则,在门前呆的时间长了,弄不好又拉又尿,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基本都会慷慨解囊,送神大吉。张讴在《行走在大神中间》中描述一个印度人牵着牛到他家“化缘”的故事,真实而又好笑,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样的现象大多发生在偏远地区,城市比较少见。
最让人讨厌的“化缘”是那种死缠烂磨型,他(她)不管你有没有事,也不理你有没有零钱,一旦盯上目标,跟在屁股后穷追不舍,左挡右围,拉衣扯包,钱不上手誓不罢休。有次在街上就碰到这样一个妇女,提着个油灯向我“化缘”。想想历史上印度教对佛教的“斑斑劣迹”,真不想给她,可是她硬是挡了我好几分钟不让通过,任你如何突围,总能阻拦得住,真佩服那种执着劲儿。好在,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不然每次出门又得增多一种提防了。
在印度,“化缘”并不局限于宗教界人士,它已然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化者还是被化者,皆不以“化缘”为耻。僧侣虽然有“化缘”的悠久历史,俗人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化缘”;生活贫困的人固然会去“化缘”求生,一些不愿意工作操劳的人也人去乞讨“化缘”;成年人固然是“化缘”的主流,大量儿童也自愿或被加入“化缘”的队伍。所以,初到印度来的外国游客,第一感受就是印度的乞丐特别多(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其实,换个角度 ,应该说印度的“化缘”文化极其兴盛。
击鼓化缘者 主动要求照相之后要钱的两个小姑娘 提筒化缘者
当一部分人以微小代价取得生活的资源,就会有另一些人尝试跟进。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学参观,正当沉浸在林木蔽天,景色悠美的校园环境中时,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Excuseme!(打扰一下!)”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锡克儿童,十岁上下,推着一辆漂亮的儿童自行车,长相十分可爱。他一边走向我,一边伸出手来:“Giveme twenty Rupees,please!(请给我二十个卢比吧!)”估计这个孩子是趁父母不在身旁的机会,想“化”个买糖果的零钱。我知道锡克族是不允许本族人乞讨的,也不想养成他见人就伸手的习惯,于是明知故问地问他是不是锡克男孩,听出了话里玄机的男孩脸一红,迅速离开了。我想,下次他可能再不敢向人“化缘”了。锡克人向以勤劳勇敢著称于印度,他们轻易不“化缘”,所以他们的儿童没有那么胆大,其它民族就不一样了。那些孩子“化缘”时软硬兼施,先哀求几声,没有反应就触你的脚摩他的头,表示礼敬,若还不拿钱出来,有可能就会拉扯了,有些调皮的甚至会抢东西。十月份是印度新鲜菱角上市的时候,味道鲜美的水果对小孩子特别具有诱惑力,所以菱角小摊前总有成群的孩子围观,当他们“化缘”不得,就会趁摊主不注意抓几个就跑,惹得摊主不断朝他们大喊大叫。但追了这个来了那个,摊主也只能不了了之。在印度旅行,遇到那些捡废品的或闲坐路边的孩子、大人,不要轻易看他们,扫一眼可能就会立刻追过来朝你“化缘”。
其实,除了个别不正常的“化缘”会遭拒绝,大多数“化缘”都会被印度人接受。在印度人的眼里,没有勤劳与怠惰之别,任何一种生活模式都有人去实践,也都会为人们所接受。他们可能不会施舍给某个“化缘”者,但绝对不会歧视任何一个“化缘”人。而且,很多印度人即便不大施,也都会小舍一些给那些“化缘”人。某些有钱的人家还会选择不忙的时候或特别的日子,在门前搭一个台子或帐篷,布施食物给过往的僧侣与穷人,这种布施每年每地都可以见到,非常普遍。长久以来的文化与习惯所致,印度人逐渐形成并接受了“化缘”这一社会现象。
有人求有人予,当施与和接受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承传的时候,“化缘”就成了一种社会传统。“化缘”风盛行,好处就是真正的穷人不至于完全陷入绝境,铤而走险,劫掠盗杀或聚寇山林。另外,真正的僧人常常在社会上活动,接触广大民众,使民众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僧人,从而遏制了假僧人的产生。而且,真正的僧人无论修行功夫有多深,道德素质总是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僧人还能解决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心灵安慰作用,对稳定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自古以来,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制止或限制“化缘”,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将僧人圈进山林或寺院封闭起来——因不喜欢某个宗教而对该宗教教徒的迫害是例外。施舍者若能以人法皆空的心态去布施,固然最好,可是接受者若认为得之应该,那就有点儿不对劲了。“化缘”的弊端在于当接受者失去了对给予者的感恩心,不以为然,就变成了纯粹的索取。在印度坐车给人让座,那些人往往一屁股坐下去,看都不看你一眼,极少听到对方说谢谢,有些人经历几次这种情况之后,就再不给人让座了。这是“化缘”泛滥透支了人们的同情心。当然,总的来说,“化缘”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致命的伤害,印度也没有因为“化缘”文化的兴盛而止步不前,多数人还是在努力追求现世的快乐生活。
文化的差异性真是奇妙得很,在对待“化缘”的态度上,中国与印度截然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鄙夷情绪,哪怕你从事的是高尚的出世修道大业。在国人的理念中,勤劳致富光荣高尚,化缘乞讨低三下四。早期的中国人甚至鄙视智力的教化,认为勤劳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上,因此佛教传来中国之前,东土只有隐士而没有僧侣。即便辛勤如孔子者,在当时还是被人嘲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古代那些不愿混迹社会的人,宁愿自食其力,隐迹山林,也不愿乞讨在人间,这就是“化缘”一直在中土难以风行的原因。
当初,汉明帝刘庄先生大老远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这是佛教传播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人家是出家人,在西方是托体“化缘”的,连伟大的佛陀都是这样生活,但明帝连问也没问,就把二位大德给塞进了鸿胪寺——即便知道,估计他也不会同意“化缘”在中国延续,我堂堂皇帝的客人,怎么能向平民百姓乞讨呢?——鸿胪寺是什么地方?汉代皇家招待客人的地方,相当于今天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从此佛教就由印度的“散养”就成了中国的“圈养”(中国佛教道场的“寺”就由此而来)。也就是说,在文化差异性的背景下,佛教一到中国就被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虽说初传中国的佛教已被“圈养”,但好在是皇家供养,多少还有点儿“化缘”的痕迹。到了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家人也要自力更生搞创业,耕田犁地,春种秋收。后来这个清规被历代王朝定为天下禅林必须奉行的管理条例,于是中国佛教僧侣的生活彻底与印度模式决裂。
明代的朱元璋少年时曾在寺院做过几天小沙弥,深知佛教教化的威力,当了皇帝之后,便制定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寺院管理制度,将天下僧人赶进山林封闭起来,与社会大众相隔绝,以维护他的万世皇统,这一下“圈养”进一步成了“笼养”。当代佛教虽然摆脱了“笼养”,可是依然在“圈养”之中。“圈养”与“笼养”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但是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也形成了后代佛教封闭内敛的性格特征,至今难以完全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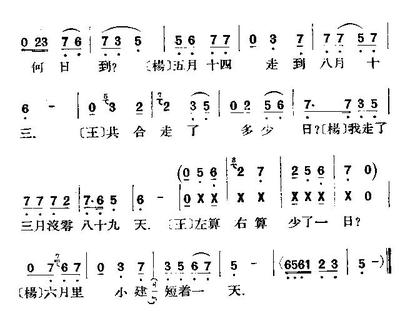
给我卢比--化缘僧伸出手说 这哥俩守株待兔等待人们送钱来!
在中国,上层社会不支持“化缘”,佛教徒也不认可“化缘”。有不少古代的祖师大德反感“化缘”的生活方式,个别甚至主张“饿死不化缘”,他们还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民间更是看不起“化缘”,一个具有十分强烈贬义色彩的名词——“叫化子”,常常被用于“化缘”者身上,某些从内心深处厌恶“化缘”的人常常抵制甚至人身伤害“化缘”的人。当代社会,就连僧尼道士都很讨厌别人说他们“化缘”,因为真正的出家人的确不会在外面“化缘”(那是有失尊荣的行为)。几年前,有一个出家朋友出门坐火车,却因与人打架被带到了警察局。这是个十分优秀的出家人,平时腼腆到连句粗话都不会讲,怎么会与人打架呢?后来才知道,被打的那个人在车上一直戏问他是不是出来“化缘”的,他觉得这个人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忍无可忍揍了他一顿。连说一说都敏感到这种程度,看来“化缘”在中国真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唐代以前中国几乎很少有假僧道,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假冒僧道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当代社会尤为严重,防不胜防,不少人曾经受骗上当。这是因为对“化缘”的强烈反感与抵制,加之“圈养”式的宗教管理政策,使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极少接触到真正的出家人,这才造成了假冒者的盛行。而且,在中国的宗教历史上,附佛外道以及打着道教旗号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以后更多情况下会打着西方某种宗教的旗号发展地下组织,现在已经初现规模),屡禁不止,这也与主政者对待“化缘”的不合理态度有很大关系。近几年,常有人批评中国社会富裕的人很多,肯捐助者却十分稀少,慈善事业一直不怎么兴盛,究其本源,也与我们“化缘”文化的缺失有一定关系。
开放“化缘”,未必人人都去“化缘”;封堵“化缘”,却“化缘”猖獗。看来,“化缘”所涉及的不仅只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了。
贫民区里的简陋神庙 相信吗?它也在化缘——饭店门口等人给食物的小驴子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