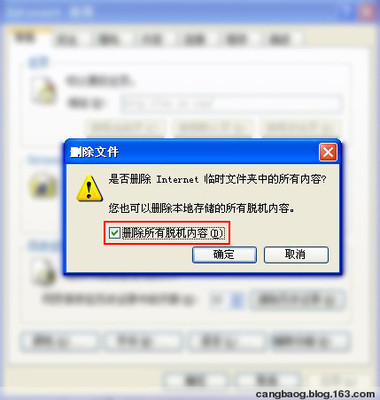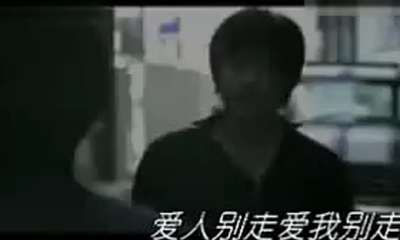班长叫喜银贵,宁夏西吉人,一米七二,长得精廋,一脸严肃,总是心思重重的样子。他很少笑,在偶尔高兴作笑时两腮内陷,使本来就精瘦的脸显得更加无肉。我与同是新兵的老乡曾研究过班长脸上无肉的原因,可能是不猪肉的缘故。班长是回民,按风俗习惯,回民是不吃猪肉的。
我未当兵时曾听叔叔常说的一句相面的话“脸上无肉,做事阴毒”。当见到班长第一眼时,这句话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我心底暗自思忖:“他不会是阴毒之人吧?”后来通过我与班长的相处,我推翻了叔叔那句相人的老话。我在班长手下当兵的时间不到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他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十六年来,我始终想念着他,他的样子时不时就出现在我的脑际。我知道,如果我当兵时的第一任班长不是他,我的人生不会是这样,虽然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可骄之处,但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我知道我这生再也没有与他相见的机会了,他只会偶尔出现在我的回部队的梦中。
一
我到了部队第三天,全班七名新兵到齐了,连队要求在全团新兵开训动员大会前,给每个新兵理一次发。班长拿着一把银白发亮的手推剪说:”谁第一个来?”全班新兵都往后缩,我半信半疑:“班长,你还会理发?”班长说:“小菜一碟。”班内其它新兵都能看出班长最喜欢我,就一致让我先理,不由分说将一张白床单围在我的脖子上。我不放心班长的理发技艺,忙叫人给我递来一面镜子盯着。班长第一剪下去“咔吱咔吱”一推,我就知道不好,连忙叫停,一摸,剪过的地方能摸到极短的发茬,一照,才知道上了班长的当。班长根本就不会理发。我一把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床单说:“不理了,这就是你的小菜一碟呀!”同班的其它新兵哈哈大笑。班长也笑着说:“第一下没有掌握好力道,我保证给你修好,绝对不会难看。”
我到了部队第三天,全班七名新兵到齐了,连队要求在全团新兵开训动员大会前,给每个新兵理一次发。班长拿着一把银白发亮的手推剪说:”谁第一个来?”全班新兵都往后缩,我半信半疑:“班长,你还会理发?”班长说:“小菜一碟。”班内其它新兵都能看出班长最喜欢我,就一致让我先理,不由分说将一张白床单围在我的脖子上。我不放心班长的理发技艺,忙叫人给我递来一面镜子盯着。班长第一剪下去“咔吱咔吱”一推,我就知道不好,连忙叫停,一摸,剪过的地方能摸到极短的发茬,一照,才知道上了班长的当。班长根本就不会理发。我一把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床单说:“不理了,这就是你的小菜一碟呀!”同班的其它新兵哈哈大笑。班长也笑着说:“第一下没有掌握好力道,我保证给你修好,绝对不会难看。 ”
在同班新兵的劝说下,我重新坐到凳子上。班长由长至短的修来理去,怎么也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成了花一块白一块是我有生以来认为最难看的发型。虽然知道了班长不会理发,但其它新兵也不敢反抗,只好任其修理了。班里的七名新兵理了发谁看谁也不象谁,班长看到自己的“得意”之作,忍不住嘿嘿直笑,笑得很得意。也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当班长,第一次给人理发,第一次有着自己的“杰作”,无论好坏,当然要自我欣赏了。其实班长根本不会理发,是拿我们几个练习手艺。连长见了班长的杰作也骂他:“喜回子你他娘的咋回事?给几个新兵理的什么发?狗啃似的。”
二
新兵训练结束了,连队依据每一个新兵在训练中的表现进行了专业分工。当班长对我说没能将我留在他身边而是在指挥排学电台报务时,我急得哭了。原来连队指挥排长早就看好了我了,在新兵下班展开专业训练前就在连长面前点了我的名。班长恳求高个子连长将我留在他身边时,连长生气地说:“你这个喜回子是怎么回事,全连一盘棋,好的兵优先考虑指挥排,都象你这样留下自己带的好兵,连队其它工作还干不干了?”
我见班长从连长那儿回来耷拉着脑袋苦着个瘦脸就知道情况不妙。班长还劝我说炮班最苦最累,说在指挥排工作轻松。我拉着班长哭起来。我觉得自己长这么大,最关心自己的人除了妈妈就是班长。我早上不喜欢吃馒头总是饿着肚子参加训练,一到十一点就受不了,班长总是从连队后勤弄回一些压缩饼干、午餐肉和撕开即食的军用快餐给我;班长在我不开心不高兴想家的时候总是给我讲故事陪我开心;班长在休息日见我不找老乡不窜门就带我上街;班长睡觉最晚经常打着手电给我们摆放鞋子衣物;班长经常半夜为我们盖蹬开的被子;班长在武装越野考核时怕我跑不动总是将我的枪背在自己身上……我哭得让班长泪花直闪,也将隔壁连队唯一上过战场威信极高说话最管用的老班长杨根思引了过来,老班长问清情况后就去找了连了,连队才同意我留在班长身边。
班长在全班七名新兵是最喜欢我,在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期间,他打过别人,但没有打过我一次。后来下了班跟他在炮班当炮手,感情更是加深。记得有次他因某事批评了我几句,我不高兴,有意在一个休息天没有将他泡在盆中的胶鞋清洗出来。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我知道,在同班战士的印象中,给班长洗衣物就是我的活计,让他们产生这样印象责任主要在我,是我最先抢着为班长洗衣物的,洗得多了,其它战士就司空见惯,认为给班长洗衣服就是我的专利,若我不为班长洗,就是放上一天其它战士也不会管的。
班长下午外出回来,见他的那双胶鞋还泡在水中,本来就有民族特色的脸显得更加长而冷冰了。晚上讲评时,他借其它事情发难,挨个儿一人一记响亮耳光。随着从右至左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澈流畅的“叭叭”声,我在心里也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六……”的同时,暗咬双齿紧绷腮肌准承接“七”。我在班内个子最高,从低至高一人一记,打到我这儿时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可班长只是挥了一下手并没有打下去。后来我想,也许多他在空中挥的一下手势是因为惯性,也许是因为对我下不了手。
三
我见班长从连长那儿回来耷拉着脑袋苦着个瘦脸就知道情况不妙。班长还劝我说炮班最苦最累,说在指挥排工作轻松。我拉着班长哭起来。我觉得自己长这么大,最关心自己的人除了妈妈就是班长。我早上不喜欢吃馒头总是饿着肚子参加训练,一到十一点就受不了,班长总是从连队后勤弄回一些压缩饼干、午餐肉和撕开即食的军用快餐给我;班长在我不开心不高兴想家的时候总是给我讲故事陪我开心;班长在休息日见我不找老乡不窜门就带我上街;班长睡觉最晚经常打着手电给我们摆放鞋子衣物;班长经常半夜为我们盖蹬开的被子;班长在武装越野考核时怕我跑不动总是将我的枪背在自己身上……我哭得让班长泪花直闪,也将隔壁连队唯一上过战场威信极高说话最管用的老班长杨根思引了过来,老班长问清情况后就去找了连了,连队才同意我留在班长身边。
在炮班加班长在内只有六人,只有我不害怕班长。班长是回民,多数时间不在饭堂吃饭,班里其它的人每次吃完饭后谁都不敢先回班,总是要等我一起回去才感到安全。每天早上打扫卫生的时间,每个人都得找活干,擦桌子椅子窗户玻璃,我曾笑一个甘肃兵将开水瓶的朔塑料盖抱在怀中擦了五六分钟,那甘肃兵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活可干,不找点事情让手头忙着,班长见我闲着还不得骂我呀!"其实班内本来就很简陋,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但班长就是不让每一个人闲着,只要发现谁找不到事做就骂没眼色。我有时在班长面前解释几句,班长就:"屁的胡子-----"。我的同班老乡在背后经常学班长骂"屁的胡了",他总是笑着问我:"我就觉得纳闷,屁怎么会长胡子?"
四
班长因是回民,很少与我们一起上桌吃饭,少了班长厉眼在餐桌上的扫视,我们吃饭的心情比其它班同年兵来说自在多了。一天连队早餐时,班长让我将前天晚上没吃完的饺子用汤浸泡后端回他吃,我在饭堂看着班长的饺子想起了在连队流传的一句话"一个回民是假回民,二个回民是傻回民,三个回民是真回民。"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于是将筷子伸向给班长泡好的饺子,吃第一个不象羊肉,再吃一个不象猪肉,直到吃第三个,细细品味之后,着实让我吃惊。曾有战士将猪骨头丢在回民家门口发生过民族纠纷,部队经常进行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的教育。我有时去回民家中都不敢随便坐,一个战士因坐了回民睡觉的炕,让人给轰了出来。我将饺子端了回去后,班长将瘦的脸拉得更长:"怎么少了?谁吃的?"我吓得没敢承认,心里直说,"真历害,少了三个饺子也知道。"
班长曾从外面背回一包苹果放在床铺下面的坑洞内,全班只有我一人知道铺下面的坑内有苹果,班长对我说,要是想吃了,自己拿。因为饺子事情,我也不敢多拿,我问班长从哪儿弄来的苹果时,班长总是神秘的嘿嘿地笑。直到有一天班长让我提了一包新旧不一的军装,一起去几公里外的劳改农场与看苹果园的宽管犯人换苹果时,我才明白了前几天班长的老乡"杨司令"在连队扯着嗓子的叫唤:"谁收了我的衣服?"
"杨司令"原名叫杨生虎,也是一个回民,在连队原饲养员复员后被连队派去养殖场喂猪放羊。部队战士们将喂猪的饲养员叫"猪司令,"放羊的叫"羊司令",杨生虎姓杨,老兵们都叫他"杨司令"。他一人住在离连队约七十米的养殖场,平时洗过后的衣服就晒在自己住的地方,一天他因事出去了半天,等他回来时发现自己才洗过一次的一套军装不见了。在连队丢东西的事情是极少发生的,如是他就在连队房前屋后扯着破锣嗓子叫唤:"谁将我的衣服收走了?"后来连长听到了他的叫喊只一句话就让"杨司令"不再吭声了,连长说:"衣服丢了你能喊啥?多和老百姓换一只羊不就回来了!"连长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因他听战士们说"杨司令"动不动就将连队的母羊换公羊,肥羊换瘦羊,因连队到多少只公羊,多少只瘦羊,除了"杨司令"再没有人知道。
五
其实班长比我只是早当两年兵,随着我当兵日子的增加,缩小了与班长在军事上的差距,与班长关系密切多了,在训练时,我总是忍不住纠正班长在组织指挥训练中的失误。班长爱面子,不肯承认自己不如一个新兵,只要我提建议,总是换来一句:"屁的胡子?"
连队有次组织没有实弹的协同训练,班里的压弹手将一发教练弹压在输弹线上,连长拖长声音下达"预备-----放"的口令时,包括班长在内的八位炮班班长都在大声重复口令。班长手中的小红旗猛地向下一挥"放!"短暂停顿后,班长发现我脚下的击发器没有踩下去,班长吼道:"叫你放你没听到?"我说:"班长,不能放,空击发。""叫你放你就…"班长说还没说完,我脚掌发力将击发器踩了下去,处于压缩状态拇指粗的推进簧闪电般地将压着教练弹的炮闩推到炮膛,"咣"的一声铁碰铁的脆响将班长吓得往后一跳。
恢复神态的班长嘿嘿地笑着说:"对对,我叫你放你就放。"谁知他说这话时,连长见在他强调只能重复口令,不许做击发动作的前提下,仍然发生空击发现象,就走过来想问为什么,他听见了班长对我说"我叫你放你就放"这句话时,不禁火了:"你这个喜回子,你叫他放他就放,我叫你不放你为什么不听?你不知道空击发损害兵器吗?。
"班长叫放的结果是将这发教练弹卡在膛内,我们全班人一中午没有休息,顶着一天中最毒的日头,接了八米长的杆子连捅带橇才将这发教练弹弄出来。
六
连队协同训练结束后就开赴贺兰山脚下的靶场进行实弹打靶,班长当兵两年也未曾参加过实弹射击,在连队有的战士连打枪都害怕,更不用说打炮了。在实弹射击前,班长也很紧张,我坐在炮位上,双手直打颤,好在我与其它兵不同,什么时候发炮,掌握在我的右脚掌。全连一级实弹准备对空搜索射击目标时,班长机械地重复连长的命令。随着命令压弹手将金黄色的炮弹压在输弹线上,整个射击阵地除了空中传来飞机声音和由上至下的命令声音外,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跳声。我既兴奋有紧张,在高低射手的配合下转动方向机轮,使炮管始终指向目标,当听到班长"放"的命令时,我猛地一脚踩下了击发器,随着震耳欲聋连大地也颤抖的连声巨响,我感到了耳朵发涨,不由得张大嘴巴。当几发炮弹打完阵地上硝烟与灰尘消尽后,我仍然张大嘴巴保持僵硬的坐姿,从震撼中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踩下击发器后没有按要求继续动作,第一发炮弹出膛后,我只是呆呆地坐着数炮响了,第一次射击完毕,我口中进了不少沙土。
我回过神来看班长,只见他拿着退弹钩在数弹壳:"怎么少一个弹壳?"我坐在炮位上偏过身子帮着清点落在右侧的炮弹壳,也发现少了一个,我前探身子往炮膛一看:"还有一个在炮膛,在冒烟呢!"班长一看,吓得往后就跑"快,要炸了。"全班唯一站在炮盘上操作的压弹手一听,一个箭步就窜下炮位跑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它战士都没敢动,都紧缩着身体,尽量藏在可以防护的铁板后面,以最大的角度来防止炮弹爆炸后弹片的杀伤。
我等了好久炮弹仍在冒烟不爆炸,才明白是射击过后自动退回在输弹线上的最后一发弹壳,那烟是从弹壳的口部飘出来的余烟。我转头对躲在炮后的班长说:"班长,是弹壳。"班长才小心奕奕地用手中的退弹钩在冒烟的弹壳上敲了两下,听到弹壳发出清脆的声音后,才用退弹钩将它钩了出来嘿嘿地笑道:"吓死我一大跳!"他的话音未落,我说:“班长,是吓你一跳,吓死了就跳不成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