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指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本人结合工作,在学习当代史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撰写了这篇学习札记,请各位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二、“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 作为党指导文艺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双百”方针是经过多次酝酿、反复论证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地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这一题词实际上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尚未涉及整个文艺界、科学界。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工作组织三个委员会。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建议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陈伯达传达了这个精神。另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出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毛回答:“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又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2)如何编写党史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苏联曾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党史的定本。毛泽东虽然对该书作过较高的评价,但他不赞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表示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可见,毛泽东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反对以个人是非为是非。1955年底,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论。当时,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是否应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1956年2月,中央在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在会上向中央报告了有关遗传学、医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意见。陆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4)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反对少数人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指示》还没有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1956年4月中旬,毛泽东看到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的一份谈话纪要,哈格尔认为,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苏联科学(如生物学家李森科的学说)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认为每句话都是神圣的。这份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批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此件给他一阅。”(5)此后,毛泽东曾在一些讲话中将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诫大家。有个单位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毛泽东说:“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长,让恩格斯当中宣部副部长,再加一个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6)中国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准绳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渐渐形成了以马、恩、列、斯及毛的言论为是非标准的教条主义学风。上述例子与其说体现了当时毛泽东个人胸怀之博大、头脑之清醒,不如说是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党寻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围绕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展开,强调了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4月27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认为,对于学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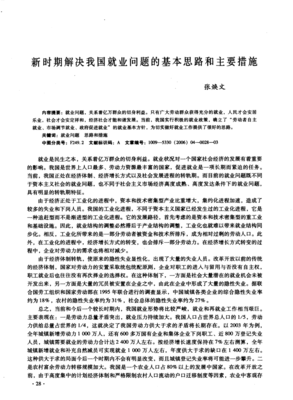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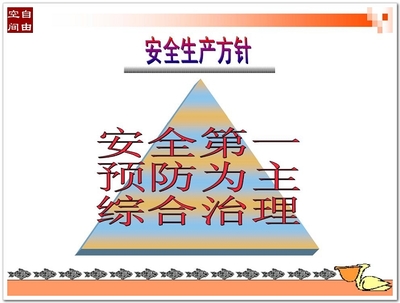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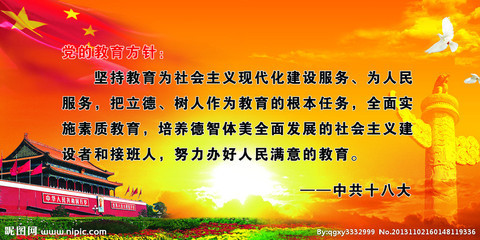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