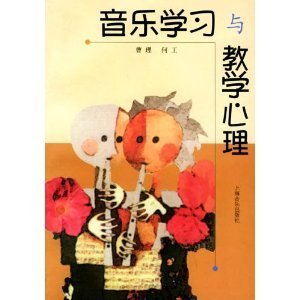《灵山》与小说创作
——高行健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会上的讲话
这个阶段,原来的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像今天这样的讲话本应该好好准备,但是我实在抱歉,讲稿也没有,只能比较随便、比较轻松跟大家讨论、交谈一下我自己的写作。
我想以《灵山》的写作过程来谈谈我对小说的看法,以及怎么去找寻一种新的小说的表述方式。
《灵山》写作的源起
《灵山》的写作,前后写了七年。我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构思《灵山》的,当时我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个小册子并非想要作什么理论的建树,只是表达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那时我写的小说到处发表不了,收到过厚厚一叠子退稿信,说这个作者还不会写小说,还缺乏驾御人物的能力,情节欠提炼,主题不够鲜明,思想晦涩,诸如此类。这样的退稿信相当多,所以就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小说?小说有哪些不同的写法?
一九八O年底,我开始写小说,一篇小文章谈一个问题。当时没想到广州《随笔》主编黄伟经对此挺有兴趣,他说:“你赶紧写吧,我给你出本书!”在他催促之下,我一天口授一篇,对着录音机。很快书就出版了,也就惹了麻烦。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甚至没有谈到意识形态,也没有谈到什么哲学问题,仅仅谈了小说的形式、小说的技巧。我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写小说,所以解释一下别人看不懂的小说,或者觉得没意思的小说。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一场大辩论,究竟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辩论。当时中国的文艺界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来找我,他说你这些主张现在争论得这么厉害,能不能就这些主张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可以预支你稿费,我立刻答应了,就是两百块钱稿费。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什么时候交稿不知道。再一个,我说,不同意删节,拿了你两百块钱当然一定交稿,但是如果这个稿子不能发表的话,我也不负责,反正我已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在这么一位热心朋友的许诺和期待下,我认真考虑写一部长篇小说,应当充分实现我关于小说的主张,这就是《灵山》的开始。先是由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小册子,之后又因为我的那个戏《车站》,惹来了许多麻烦,我乾脆离开北京了。
离开北京除了躲避检查,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想写这部以中国的南方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想实地考察一下。种种原因,加上当时我身体不好,被误诊为癌症,这一切都凑在一起,促使我走上了探索《灵山》的路。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去哪里,也就无所谓,既然癌症——死刑都已判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阴影消失,拍了片子,医生诊断,最后结果是癌症不存在。但当时既已出走,那就一直走下去吧!
浪迹长江,思索文化
我带了两百块钱预支的稿费,自己还有点积蓄,走到哪里算哪里。那是真正的流浪,在长江流域就走了三次。最长的一次五个月,走了一万五千公里,当然不是都走,有坐车,有拦车,在公路上拦汽车、拖拉机之类,以及租自行车和步行。全部算起来——我没有算过三次旅行到底有多长,但是有一次旅行我是计算过的,从哪里到哪里,我有地图,那是一万五千公里。这一趟比较有计划,我事先做了很多准备,走了七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从长江上游到东海之滨,各种生态都见过,其中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同时,我也做了认真的历史研究,把《史记》和《水经注》通读了一遍,甚至找古地图来查考《水经注》。我还相当认真研究过《山海经》。在我看来,《山海经》其实是一部古地理书。
这样,我就把长江流域的古历史、古地理做 了一番详细研究。当时我还冲破许多限制,利用作家证件,到内部图书馆查阅材料,也看了很多被查禁的歪门邪道和道教的书,以及很多佛经。
同时,我又访问了差不多一百位专家学者,从古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到考古学家。我直接去了很多考古点,印证了很多看法,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关于长江文化的看法:从新石器时代起,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大区域文化。这些看法后来同考古学家们讨论,他们觉得言之有理。
当时长江流域的考古研究,专家们一做十年、十几年,就在一个考古发掘点上,甚至还没有写成报告,还在学术保密中。而我走了许多地方,看到他们出土的文物,到文物的发掘点跟考古学家作了很多讨论,又去别的地方详加比较,进而发现这个大区域的一些文化联系。比方说,有一种出土的陶器,器皿的底端有几何的符号,我认为是中国文化起源最早出现的抽象符号,有的是小孔点,有的是四方形,有的是三角形,这种组合不只是在一个考古点上发现的,从长江下游到中上游,都有这种符号。当时考古学者互相还不通气,只在某些刊物上有所反映。我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由于水路的沟通,人已有相当强的航行能力。我们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类的能力。实际上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说离现在差不多七千年到五千年前,航行的能力就已经是相当强了,所以这个文化可以变成大区域文化,因为这一类符号和这一类器皿的形状,不仅是在一个地方出现,而且是从上游到中下游不断出现。我认为《山海经》所反映的故事主要是中国古代长江流域的神话遗存。
沉浸自然,顿获开悟
我讲这些,是说《灵山》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中国文化背景。简单称之为寻根我不太赞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寻根作家,但我对中国历史确实有很大的兴趣。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只是帝王史、权力史,而忽略了文化的历史。当时我甚至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任务:如果我在中国待下去不能创作的话,没准我将来会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因此,《灵山》的背景,还有一个历史研究的兴趣,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兴趣在里头。
建构这部小说时,我发现要表达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用讲故事的办法是完全不可能的,要另找小说的形式,也就是说,提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小说的形式服从于什么?换句话说,文学又是什么?你在小说中到底要写什么?
我长时间一人独自在外,特别喜欢去边远的地区,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面对自然,在那些大森林或深山里独自行走,沉浸在跟自然的对话里。自然的景色跟音乐一样令人触动。旅行中我总在思考,总在跟内心的我说话,久而久之就发觉说话的对象是你,而不是我。也就是说,跟自己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自我就投射为你而变成一个虚拟的对象,谈话的对手。
我突然开悟了,小说的结构可以是“我”与“你”,就是人称的结构。第一人称就是“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漫游者,见到的是真人真事。《灵山》里头有很多实录,很多真人真事,这是“我”在现实中的旅行。同时又有一个神游者,就是“你”在作一个精神的旅行,“你”在和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这个“你”产生于同一个人。

因为写作这部小说,我又发现一个大作品的情节不是它赖以建构的唯一根据,可以另找一种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人的内在,心理层次。这部长篇小说,乃是以心理结构来代替情节,以人称代替人物。这样的话,这部小说就无法归类,也可以说在小说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小说。
既然已经走得这么远,那么不如继续往前去。我不仅想把它写成一个心理的作品,还想把自己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质疑写进去,这些质疑还包括对语言的质疑。语言的实现总是要通过一个主体,就是谁在思想?谁在说话?那主语总是“我”。可是“我”在作这种思考的时候,这个“我”也值得怀疑。“我”是如此不确定,如此任性,如此难以捉摸,因此“我”就不仅仅是一个主语的问题,语言学的问题,或者语法的问题,“我”同时当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质疑尼采,质疑自我
中国大陆当时很风行尼采哲学。尼采哲学一直被封闭,到那时突然开禁,人们读到尼采,疯了,有很多“新尼采”纷纷出现,动辄自比上帝,这也跟刚刚过去的那一个世纪人们不断地犯过的这个毛病有关,我管它叫发狂。我写过一篇文章——《个人癫狂与国家迷信》,人们对国家迷信,制造国家神话以外,个人也癫狂。都以为自己是造物主,上帝已死,个人就成了上帝,就以上帝的名义说话。我认为人不能那么狂妄,自称为超人,像尼采一样。尼采是神经病人,病理学上确实是一个神经病人,但是一个世纪以来把这个神经病人当成一个最大的英雄,以为他说出了这个世纪的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尼采是一个思想家,尼采的哲学可作具体研究,但把尼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则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个病痛,这种病痛后来又和革命的乌托邦病痛联系在一起。
从对主语的质疑,导致对尼采哲学的质疑,导致对个人的价值判断的质疑,因此,《灵山》就变成了一部不断质疑的书。
我又发现,在质疑的过程中,并不需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不需要采取一种颠覆者的态度。颠覆很时髦,暴力革命的颠覆纷纷破产,艺术上的颠覆并没有破产,至今也没有,人们纷纷自认是艺术上的颠覆者,不断反艺术,一次又一次反,反到什么都没有了,艺术变成一个命名,一种思辩。这背后也是把个人当作造物主,当作上帝,极端的自我膨胀。文化为什么要颠覆掉?一个人,算你能写出一点新鲜的东西来,写就是了,前人是打不倒的。前人已经在那里,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为什么要打倒呢?打倒就是发狂。如果你确有可说,你就说;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不必通过否认前人来确立自己。
在写作过程中,谦虚是重要的,谦虚倒不是品德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个人是很微弱的,个人究竟能做什么事情?包括那些号称为英雄、要改变世界的人,究其实,往往不是病人就是疯子。你要以文学家的眼光去看,他们是很可怜的,并非是什么伟大的英雄,如果人们有自嘲的能力,倒较为健康。我对这自我既在质疑又在嘲弄,有时候就玩世不恭,但是我以为玩世不恭比狂妄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对自我也采取这种调侃的态度。
《灵山》这本书的结构和形式,就是这么出现了,然后就这么写下去。很多的章节,而且写得相当随意。
聆听音乐,自言自语
我在家中有一个写作习惯:一遥听着音乐,一边录音,那就写得更加灵活。我不是坐那儿去费脑筋思索,我觉得那样的语言很可能是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传达活生生的感觉。
我写作时喜欢这么说话,边听音乐边录音,最好不是在灯光照耀下,最好是在暗中,甚至灯都没有,只有录音机的红点在闪动,听着音乐沉浸其中。
所以,这部小说又是一个长篇的自白,或者叫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又找到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有时候是“你”,而“你”毕竟是一个男人,“你”还需要一个女性来对话,创造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她”。这个对手的“她”,也是以人称来代替人物,这个“她”可以是许许多多的女人,也可以是一个女人的多重的变奏,女人的各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面貌,都在一个人称代词“她”之下,和“你”进行对话,也可以和“我”。“你”和“我”也可以是同一个人物,进行对话,而这对话的“我”与“你”又可以界定为一个男性的“他”。“他”也出于“我”的思考,或者说是自我意识升华后的中性的眼睛,在自我观照的时候就是“他”。所以这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人称,“你”、“我”、“他”都可以成为这本书的主人公,他们都建立对手,进行对话。
《灵山》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内心独白,诉诸假的对话,或诉诸内心的对话,实际上是独白,本质上它是一个长篇的独白。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就这么说一下。现在我们回到小说:小说是什么?
街头巷议皆小说也
什么都可以是小说。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现,中国古已有之。如果我们查一下旧版的《辞海》(不是新版的《辞海》,新版的《辞海》我极不喜欢,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条目,而且把老的语汇也加以意识形态化),就会知道,它解释“小说”“街头巷议皆小说也”,街头巷议、道听途说、笔记、杂录、志人、志怪,中国古代的各种寓言、游记、笔记,都是小说,所有不登大雅之堂,所有不是作为教化,跟国家没有关系,跟帝王权力没有关系的这些闲杂人等的琐碎议论,皆小说也。这是很博大、很精彩的对小说的看法!
在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里,诗文有很崇高的地位,小说则是下品、下等,不入大雅之堂。可是现在看来,其实最丰富的还是小说,对社会生活、对历史、对人生最充分的表述,其实还在小说里。所以我认为小说不是下品,不是文学中的下品,它是一种极丰富、极有表现力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如此不固定,如此灵活,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可以像揉面一样,爱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但它还是面,还是文学,还是有营养的,它并非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以为小说没有写完。人们一再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其实这判断也是一种狂妄,也有一种颠覆者的味道,一种艺术革命的味道。我远离这些革命和颠覆,回到一种比较平常、平和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看待人,看待自己。小说没有写完,大有可为,只要你确实有可说的,确实找到你要诉说的东西,找出新鲜的小说形式,就可大有作为。我自己就不断在找,我想若干年后当我也变成骨灰的时候,别人还会继续下去。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长河,艺术史也差不多如此。谢谢大家。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〇一年三月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