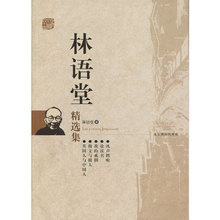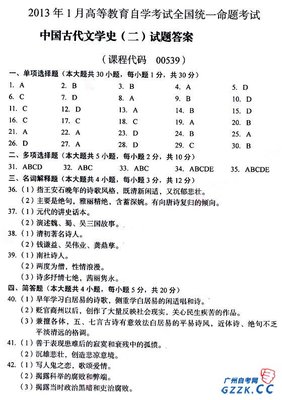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献保护研究
序
人类社会有了语言,才会有文字,有了文字才会有文献,文字生而文明始,文献生而文明兴,是故“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然而,迄今为止语言的产生仍然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文字的产生则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得到确证,因此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伊始的最准确标志,而文献的产生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里程碑。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从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原始陶文到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献,汉字的使用和文献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自殷商甲骨文献兴起以后,中华文献的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素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著称于世,而四大发明之中有两大发明为文献的生产制作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是中华文献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而且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里程碑。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华文献发展史最能代表中华文明发展史。
文明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传承,而文化的传承取决于文化的生态环境。原生态环境中的文化发展,或生或灭,或盛或衰,自然而然,这是文化生命周期的自然过程。但是,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发展的原生态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外在干预甚至破坏,以致文化的传承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始终是一个困扰文明存亡的问题。中华民族之所以拥有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其要在草根民众的细胞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无论是外强的入侵,还是统治的专制,只要草根民众没有被彻底消灭,即使传统文化一时被湮灭,草根民众总是能自然而然地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表达、修复和传递传统文化的生命密码,并在适时的环境中繁衍传统文化。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文化力量,是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命脉。人类文明史已反复证明:文化的传承与繁衍归功于草根民众的文化自觉与自主,而文化的停滞与灭绝则归因于统治者的文化昏庸与专制。
在中国文献发展史上不断地呈现着这样一种文献聚散的历史循环:一个朝代建立后,统治者或早或迟地会下诏广泛征集民间遗书,以建立官府藏书,彰显其文化盛世,然后或多或少地禁绝文献,以图思想之统一与江山之稳固。一个朝代灭亡时,官府藏书或毁于兵燹战火,或弃之市井,散佚殆尽。新旧朝代更迭,文献聚散无常,如此循环往复,倘若没有草根民众的珍惜呵护,中国的古代文献早已荡然无存。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迄今十之八九不存,所亡者大多归因于统治者,所存者主要归功于草根民众。即使是今日的各类图书馆,其所藏古籍十之八九亦来源于草根民众的世代收藏。
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原典是文化的遗传因子,是构成文化基因组的一个特定的且不可替代的DNA序列。在遗传学上,基因能够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可以通过人工分离和修饰后导入到目的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造生物,制造出新的转基因生物。然而,在文化学上,作为文化遗传因子,原典虽然也能通过复制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但是任何复制都是原典及其文化基因序列的异化,不再具有原典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因为原典本身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原典在流传过程中还附着了大量的文化因子,并因此成为由原典流传所繁衍的特定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如果没有原典,那么由原典繁衍的文化生命周期也就走到了尽头。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近千年的流传中,从皇宫到民间,再从民间到皇宫,最后辗转归公,一个又一个的题签、序跋、钤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且不断延续的文化生命体,不论明代画家仇英的仿本有多么逼真,也不论清宫画院本的画技有多么高超,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原件相比较,始终有着天壤之别。各种各样的《清明上河图》印刷品或者数字化产品,不论有多么出神入化形象逼真,也不论多么唾手可得,其文化价值始终不及真迹原件的九牛之毛,人们或者熟视无睹,或者弃之如敝履;而每一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原件的展览都会吸引无数一睹为快的民众。这就是原典作为文化遗传因子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因此,保存和保护古籍即是保护中华文化,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
在以内容为王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图书馆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是以珍秘为守,将古籍束之高阁,在保存与保护上无所--作为,任由纸张老化或者虫蛀鼠啮,以致古籍的保存现状每况愈下,令人堪忧。二是一味强调文献的开发利用,不加甄别地对古籍进行数字化,甚至打着“破坏性抢救”的旗号对濒危古籍进行不可逆转的数字化抢救,以致大量的古籍和民国文献被破坏殆尽。究其原因,一则古籍保护的传统与价值观严重断裂,不再普遍存在,二则古籍保护的人才极度匮乏,三则传统的古籍修复技艺萎靡不振,现代化的古籍修复技术应用极少,三者兼具,实为中华古籍保护与传承之大不幸。
更为独特的是,我国图书馆界基本上没有西文古籍保存与保护的观念,对源于西方的现代书籍的保存与保护亦鲜有专门研究,以致不少珍贵的西文古籍无人辨识,大量破损的现代书籍亦无修复之良策。这固然有中文古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西文古籍的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语言的障碍和西文古籍知识的匮乏,以致我国图书馆界几乎没有西文古籍整理与保护的专门人才。
事业的继承与弘扬全在得人,人才的延揽与培养关乎一项事业的兴废。
为了赓续古籍整理与修复事业,笔者于2001年选派2人赴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技术3个月,其后利用美国岭南基金会中山大学图书馆项目特别派遣林明于2002年8月至2003年7月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中心(School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Austin)访问进修一年,专门学习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技术。该中心在美国文献保护修复教育机构中排名第一,而林明则为国内第一个被派往美国学习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图书馆人。这在十年前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国内图书馆界派遣出国访问进修的一直是学习现代化技术与图书馆管理,学习西文古籍整理的从来就没有,专门学习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的就更是亘古未有。2003年8月,林明回国以后,笔者每次在向同行介绍林明的赴美学习主题时总会获得狐疑甚至不屑的表情回应。笔者自然并不介意,因为没有几个同行懂得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对于中国图书馆界的作用与意义。
在派员赴海内外学习中西文古籍修复与保护技术的同时,笔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延揽古籍人才。
2003年3月,中山大学图书馆高薪聘请辽宁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韩锡铎研究馆员、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原副主任潘美娣副研究馆员来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担任特聘专家。韩锡铎先生为国内著名的古籍整理专家,潘美娣女士则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籍修复专家,两位专家均刚从各自的工作单位退休,正处在学问、技术与经验的巅峰期,十分适合担当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修复的学科带头人。他们的热诚支持与帮助,顷刻弥补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修复学科带头人的空白,令人倍感欣慰。2006年,笔者又特别聘请故宫博物院的碑帖整理专家施安昌研究馆员到馆工作。韩锡铎先生因为健康原因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6年后返回家乡颐养天年,施安昌先生因工作原因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两年,潘美娣女士则一直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担任特聘专家,迄今已经9年。
2010年春,承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的大力支持,笔者得以十分荣幸地聘请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室主任、国际著名的中文古籍整理专家沈津先生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特聘专家,作为古籍整理的学科带头人,率领年轻的古籍整理团队全面开展各项古籍整理工作。中山大学图书馆拥有沈津先生和潘美娣女士这样世界顶尖的专家担任学科与事业带头人,假以时日,在他们的“传、帮、带”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与修复必将成就一番事业。
有了学科带头人,还必须有一支专业队伍。为此,经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历史文献学专家陈永正先生推荐,笔者请求学校启动特殊专业技术人才招聘程序,聘请没有大学学历且在广州字画装裱界小有名气的技工李景文先生到馆工作。其后,又相继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古籍修复专业和南京艺术学院古籍修复专业招聘多名毕业生,加上从馆内调配的相关人员,组成了一支十余人的古籍修复队伍,这在国内图书馆界十分罕见,在举国图书馆界沉醉于图书馆数字化与网络化的时代更是不可思议。
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与保护高级专门人才,自2005年起,笔者开始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招收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迄今已有4位学生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5年,笔者第二次出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主任以后,对原有的文献保护课程进行改革,从2006年起聘请中山大学图书馆林明担任资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本科生课程“文献保护技术学”的主讲教师,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迄今已经六载,该课程亦发展成为中山大学的重点建设课程,专用教材亦编写完毕,即将付梓出版。
与此同时,2003年3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古籍修复实验室,开始馆藏古籍的修复工作。起初,古籍修复实验室只有50平方米,2004年11月,总馆馆舍改扩建完工后,古籍修复实验室的面积扩大到120平方米,2007年扩大到220平方米,2008年再扩大到300平方米,200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450平方米,已经建设成为设备设施齐全、技术力量较为雄厚、集中文古籍、西文古籍修复、碑帖修复、字画装裱、人员培训、教学实习、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为一体功能较为完善的古籍修复实验机构。实验室目前拥有在职修复人员11名,其中,副研究馆员2名,馆员3名,助理馆员1名、管理员4名、工人1名;博士1人、硕士2人、学士4人、大专1人、中专2人。这样一支年龄结构、学位结构、专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团队在全国并不多见。
在延揽高级人才,培养专门人才,着力建设古籍修复实验室的同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积极推进古籍修复与保护方面的海内外交流与合作。
2004年12月,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中心的三位古籍保护与修复专家来中山大学访问讲学,举办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30余人参加了研讨班。是为我国图书馆界第一次举办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
2006年5月9-12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成功举办2006文献保护与修复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15个省市自治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教学研究单位的70位修复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参加会议,与会者发表论文53篇。
2007年5月,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建立古籍保护与修复合作关系。2008年1月中山大学图书馆选派肖晓梅赴香港大学图书馆进行两周的古籍保护与修复访问交流。2008年3月,香港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修复专家黎振英先生应邀回访,其间,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中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并邀请国家图书馆杜伟生先生、南京大学图书馆邱晓刚先生联合主讲,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人员30余人参加。
2008年7月-9月,中山大学图书馆承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2008年,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定期邀请德国文献保护与修复专家来馆访问讲学。2008年11月9-12日,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大学与国家图书馆文献保护与修复部主Mr.Reinhard Feldmann、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部主任Dr. ThomasStaecker应邀前来中山大学图书馆访问讲学,举办古籍保护修复与数字化专题报告会。
2009年5月16-24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派遣林明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专门考察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及其管理与运作情况。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合作,共同举办为期两周的“首届全国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技术培训班”,由两名德国专家和林明副馆长共同主讲。
2010年5月25日至8月6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承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十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2010年6月27日至7月8日,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联合举办为期两周的“第二期全国西方文献修复实技术培训班”,邀请德国资深修复专家MonikaSchneidereit-Gast女士主讲,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16位修复人员参加了培训和研讨。
2011年11月,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联合举办为期两周的“第一期全国西文文献修复技术高级研修班”,特邀请德国索林根纸张修复工作坊创办人、资深文献修复师MonikaSchneidereit-Gast女士主讲西文古籍和精平装书的修复技术,重点开展中世纪图书样本的制作、纸张修复、精装图书装帧修复的实操培训。来自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14名学员参加培训。
这一系列的古籍修复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为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培养了一批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特别是西文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而且在中国图书馆界搭建了独一无二的中外文献保护与修复交流与合作平台。
笔者于1998年出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1999年从美国回国以后旋即开始谋划中山大学古籍整理与保护事业,十余年来不遗余力,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更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在图书馆界普遍热衷于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的新世纪初年的确非常另类,令人费解。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一是统一部署,从2007年开始,用3到5年时间,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二是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三是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批古籍书库的标准化建设,改善古籍的存藏环境;四是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五是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特别是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建设中华古籍保护网,完成“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争取开展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于是,笔者当初的固执己见变成了一种远见卓识,多年的坚持不懈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3月17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中山大学图书馆名至实归,成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9年12月,文化部公布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12个)名单,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赫然在列,成为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唯一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林明的著作《中国古代文献保护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土壤、气候和氛围中产生的一项研究成果。2003年7月,林明完成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中心(School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Austin)的一年学习任务回国后,一直在协助笔者开展古籍整理与修复事业,特别是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实验室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建设、人才培训、海内外古籍保护与修复的交流与合作。2005年9月,林明再次考到笔者门下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古籍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与技术。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和深入实践,林明出色地完成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著作,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国古籍保护与修复的人才一直比较匮乏,专门的著述也不多,主要的专门著述基本上产生于近30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档案保护著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少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和图书馆学专业都开设了文献保护学的专业课程,其中档案学专业更是以档案保护为专业核心课程,因此在油印教材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或者教材,例如:刘家真的《文献保护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良城、杨继波的《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方法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冯乐耘的《中国档案修裱技术》(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刘家真的《文献遗产保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仇壮丽的《中国档案保护史论》(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年)、周耀林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这类著述比较侧重档案保护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在档案修复的技艺上尚有提升的空间。
第二类是书画装裱著述。书画装裱是中国的传统技艺,历史上产生过不少相关著述,近30多年来,书画教育、收藏与研究界亦涌现了一批专门著述,例如:汤麟的《装裱艺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冯鹏生的《中国书画装裱概说》(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的《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杨正旗的《书画装裱》(济南:山东人民出版,1980年)、邱陵的《书籍装帧艺术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杜子熊的《书画装潢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王以坤的《书画装潢沿革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杨正旗的《中国书画装裱大全》(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杨永德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李明君的《历代书籍装帧艺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等等。这些著述比较侧重书画和书籍的装裱艺术,在书画和书籍的修复技艺上尚可深入。
第三类是古籍修复著述。古籍修复是中国的传统技艺,与书画装裱不同的是,历史上专门论述古籍修复著述甚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系统的著述,例如:肖振堂、丁瑜的《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潘美娣的《古籍装帧与修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賽虹的《古籍修复技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童芷珍的《古文献的形制和装修技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杜伟生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苏品红的《文献研究与文献保护》(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这类著述比较侧重古籍修复的技艺,但古籍保护的理论与技术上阐发不足。
上述三类著述各有千秋,是我国古代文献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尽管如此,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古代文献保护与修复思想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系统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林明以独特的视野,在系统总结古代文献受损的载体因素、环境因素、生物因素、灾害因素、人为因素的基础上,从文献制作的防护到文献收藏的防护,再从文献利用的保护到文献破损的修复,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文献保护的思想理论与技术方法。这种建立在文献生命周期上的理论框架,既清晰地揭示了我国古代文献保护与修复思想理论与技术方法的产生与发展,又突出了我国数千年来以预防为主,以修补为辅,防治结合的古代文献保护优良传统,是一种颇值得肯定的学术创新,对于当前的古代文献保护与修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今,我国正值百年不遇的古籍整理与保护盛世,这本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这是学人之幸,学术之幸、古代文献保护与传承之幸,可喜可贺。
是为序。
程焕文
2012年3月4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参考阅读:《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丛书总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