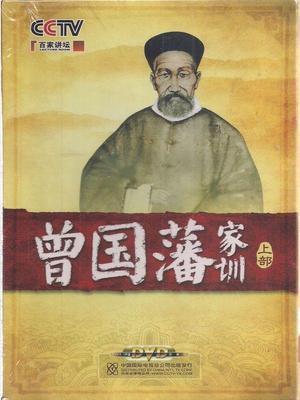诗国大儒,诗圣杜甫
文/莫砺锋
中国是诗歌之国,历代诗人成千上万,而惟有杜甫一人得到“诗圣”称号。古今贤者为什么只将“诗圣”的桂冠托与杜甫?这要从诗圣的由来说起。最早提出“诗圣”是明人费宏,他在《题蜀江图》中说:“杜从夔府称诗圣。”稍晚的胡应麟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18中说:“拾遗素称诗圣,又称集大成。”到明末王嗣奭,则在《梦杜少陵作》中说:“青莲号诗仙,我公号诗圣。”其实早在北宋,苏轼就称杜诗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南宋的杨万里则称杜甫为“圣于诗者”(《江西宗派诗序》)可以说,诗圣之称是宋人首先提出的。那么,宋人缘何称杜甫为诗圣呢?
大概说来,宋人推崇杜甫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路线进行的。先看道德判断。北宋后期,士人在政治上分成新旧两党,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新党旧党都非常推崇杜甫。旧党大将苏轼极为尊杜,尤其肯定杜甫忠君爱国:“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当然,宋人崇杜不仅仅着眼于忠君,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新党首领王安石对杜甫非常尊敬,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详细叙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种种言行,然后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而旧党的黄庭坚也咏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老杜浣花溪图引》)
到了南宋朱熹,则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历史人物并称为“五君子”。这“五君子”中除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一生之中在政治方面都有很多建树,或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惟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内容,因为他根本不曾得到过机会。他想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除了在肃宗的朝廷里偶然地仗义直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杜甫始终默默无闻,很多时候甚至处于民间。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尊崇?为什么在朱熹看来,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杜甫可以与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儒并列?关键在于他们五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以道德论、以人格论,都有重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是这样讲的:“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意思就是,这五人都是光明正大、磊落畅达之人,足可以作为儒家人格的楷模典范。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一种文化的评价。由此可见,宋人高度认可杜甫的人格价值,高度评价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故而认为杜甫在道德上已经达到圣贤境界。
再看审美判断。宋代诗人对杜诗的艺术成就评价极高,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陈辅之诗话》)。苏轼甚至认为,李白诗集中有伪作,是因为艺术不够精炼,让伪作得以鱼目混珠。转而评价杜甫说:“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书李白集》)宋人非常热衷于讨论杜诗艺术,以至于有人声称“怕老杜诗”。(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见宋人认为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造诣已经登峰造极,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宋代诗人在唐代诗人当中选择最具典范意义的楷模时,最终在道德判断、审美判断两方面瞩目于杜甫,由此确立了杜甫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典范地位。
宋人这一选择是否合理呢?杜甫在道德情操、诗歌造诣两方面是否达到了超凡入圣的程度呢?我们先看杜甫的道德情操。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他非常崇敬其十三代祖杜预,可说是念念不忘。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不但功业彪炳,而且曾为儒家经典《左传》作注,其注本收入了《十三经注疏》。杜甫自幼习染儒家思想,并终生服膺儒学,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偶尔发牢骚,他也说“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那是极端悲愤中的牢骚话,事实上杜甫遵循儒家思想已经达到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堪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
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凤凰自比:“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见志,诗中那只“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的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
杜甫不但服膺儒学,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在儒学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儒学史有过两大高峰:汉学与宋学。唐代夹在两个高峰之间,处于低谷,前不能比汉,后不能比宋。那么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滞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家代表人物?钱穆有个观点,唐代有两位重要的儒家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
提起唐代儒学,就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虽然是极重要的注本,但是其中的观念、义理,基本都来自汉儒,在学理上缺少新意。甚至可以说,唐代由于《五经正义》,有了对经典的权威解说,儒学基本上停滞了。
但是杜甫不然,杜甫用他全部的生命,用一生的践行,丰富、充实了儒学本身。儒学原是一种实践哲学,它重视身体力行甚至超过学理建树。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年富力强时都不忙着著书立说,而是奔走天下,要让仁义之道落实于天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路行不通了,年纪也大了,才回过头来发奋著述,传于后世。儒学最重视躬行践履,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最本色地承担着儒家精神,充实着儒学价值。
儒家重视仁爱思想,主张行仁政于天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孟子·离娄下》而仁政的最低限度是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用诗歌表达出:“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
儒家谴责贫富不均,“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更对这种现象严厉批判。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指控贫富不均的佳作甚多,而大家最推崇的仍然是杜甫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强调维护民族尊严,捍卫民族利益,坚决反对侵略。杜甫亦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安史之乱以后,叛军很快占领长安,众多官员纷纷投降,变节做了安史伪王朝的伪官。其中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未能免。惟独杜甫,惟独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小官职的杜甫,坚守着气节。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越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杜甫这一举动,在当时凤毛麟角。他对叛军始终以“胡”称之,如“群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逆胡冥寞随烟烬”(《复愁》),等等。在《北征》中,一连四句有三个“胡”字:“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真是骂不绝口,表示了诗人对叛军的无比仇恨。
儒学重视修身养性,特别崇扬天命、仁心、大丈夫精神、君子人格,始终相信高度文明的社会,其基础应该是有道德自觉的文明个体。以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为例,历代士大夫当中,谁身上显著体现了这种精神?杜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这里特别要注意杜甫的身份,历代仁人志士为数不少,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但是这张名单上,大多是取得了重要政治建树的人物。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担起天下有道的责任,从而彰显儒者风范。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个平民,他经常称自己为“杜陵布衣”,在诗中自陈“杜陵有布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布衣也好,野老也好,都是一介布衣,平民百姓。而杜甫正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负起了儒家推崇的典范人格。
诸葛亮、范仲淹等先贤,地位太高,距离普通人太远。普通人一辈子没有机会,于建功立业当中展现人格境界。一个普通人,过了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呢?能实现,杜甫就是典范。杜甫不仅对儒家的道德准则身体力行,还用他的行为阐释出那些准则如何涵义丰富,如何平易可行。
杜甫满怀仁爱之心,扩大充实以至于忧国忧民。他首先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进而把仁爱之心扩展,能够爱其他民族的人民。盛唐边境战争频发,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确定由唐帝国发动,是非正义的战争。南诏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盛唐时候出兵讨伐。从《新唐书》、《旧唐书》看,从《资治通鉴》看,都可以确定那场战争错在唐,屈在唐。唐大举进攻南诏多次失败,甚至全军覆没。
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一种非理性的、狂躁的爱国热情,鼓吹定要攻打南诏,非要把它打败!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写诗讨伐南诏。惟独杜甫,清醒地看到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清醒地看到人民的生活受到破坏。所以,他写出了著名的《兵车行》。这样的诗,当时其他诗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写。原因就是杜甫深具仁爱,懂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仁爱之心应当及于他们,与他们和平相处。
“仁者爱人”是儒学的根本,“民胞物与”亦是儒家的胜境。杜甫的恻隐同情之心,还推广到了动物,推广到宇宙中一切生命。杜甫无数次描写动物、植物,满怀爱怜之情。马、鹰、松树等等,或美丽、或雄壮,引起审美愉悦和崇高感。即使是一些细微弱小的、不那么美好的东西,杜甫写到它们也充满爱心。看到江上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被困在网中,他很同情:“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在成都时,他曾写诗咏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后代很多注家都说,这一组诗象征着饱受战乱之苦、又面临苛捐杂税的劳动人民。
杜甫还有很多诗并没有这样的象征意义,而是直接关注那些细小的生命本身。乘船从河上过,见一群小鹅在游,他作诗说“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此诗最后两句,诗人喃喃地问那些小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舟前小鹅儿》)对弱小生命的深切同情,对小鹅的呵护之意,令人感动。把仁爱之心由人类推广到一般生物,这是儒学自身的展开。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早已融于杜甫的诗篇。
杜甫至为贴切地阐释了儒家仁爱如何平易可行。中国的仁爱精神与西方的博爱精神貌同而神异。西方的博爱精神最初的来源于宗教,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追问它的起源,一是服从于神灵的诫命,是神灵要大家博爱。二是原罪救赎,洗脱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而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一切的仁义道德都从内心自然生发出来。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更自然,更符合人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的诗篇、杜甫的行为,很好的阐释了这种伦理观念。
杜甫去奉先县探亲时,家中最小的儿子因为挨饿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业徒”(指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戍守边疆的战士,他们遭受痛苦更甚。所以杜甫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杜甫居住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漏下来,他彻夜不得安眠,床被都是潮湿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所期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牢固的、安稳的茅屋,作为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杜甫将仁爱之心由近及远推广开去。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元年在同谷写的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当时杜甫从甘肃天水向四川成都逃亡,他的生活已经无以维系,于是想逃往成都。途经同谷(今甘肃成县),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写了这一组诗,共七首。
且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有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写到他的家人,岁暮天寒,全家都没有饭吃。为了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植物块根,想借此给家人充饥。可惜大雪封山,什么也没有挖到,诗人空着手回到家。而家里“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家老小都饿得靠在墙壁上呻吟,话都说不动。
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杜甫有四个弟弟,其中幼弟杜占一生跟随在诗人身边,所以诗人格外想念离散各地的三个弟弟。第四首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想到他有个已经守寡,独自拖着三个幼小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第五、第六、第七首都是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思考的过程,他感情的流向,也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符合人类的本性,最切实、最自然。在这个方面,杜甫十分贴切地阐释了儒家精神。
从以上看,杜甫是典型的儒家,儒家的典型。称他为唐代大儒,决非过誉。正因为如此,杜诗展现出崇高的人格境界,蕴涵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读杜诗,在获得丰厚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了重大的精神启迪。这种精神启迪伴随着感动而来,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沁入读者心肺,悄无声息却沦肌浃髓。从杜甫开始,儒家诗教的积极精神真正成为古典诗歌的指导原则。杜甫以后的优秀诗人,几乎都遵循他开创的关注现实、干济政治的创作宗旨,成为古典诗歌史的主导倾向。
更重要的是,杜甫的人格境界对后人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我们举两个著名的例子。
先看文天祥。南宋政权灭亡两年半之后,文天祥依然誓死不降,最后在北京的柴市口英勇就义。文天祥以自己的行为夯实了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他在《正气歌》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可见正是古人的道德光辉激励着他。文天祥的精神源头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儒学典籍承载的孔孟之道。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上面发现一段铭文:“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外,文天祥还有一个精神源头就是杜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两百首集杜诗(集杜诗,就是从杜甫的诗篇抽出诗句,重新组装成诗作),文天祥缩写200首集杜诗都是五言绝句。他写了一首序,交代自己写集杜诗的原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就是凡是我心中想说的话,杜甫已经帮我先说了。“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之诗也。”天天读它们,好像就是我写的诗,都忘掉这是杜甫的诗。下面又说,“余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自从国家动荡以来,我个人的遭遇、国家的遭遇,全部都体现在这些诗句中。可见杜诗是鼓励文天祥坚持民族气节的另一精神源头,“临大节”之时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
我们再看另一个深受杜甫影响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苏东坡有一次创作书法作品写了两首杜诗,诗题是《屏迹》,“屏迹”就是把行迹隐藏起来,隐居的意思。这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共三首,苏东坡手书后面两首。写完以后,苏东坡加上一段跋,这段话很是风趣,他说:“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苏东坡又解释说:“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之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意思是说,所有庄稼都起源于神农、后稷,但是今天家家都在种植,农民们种了粮食放在仓库,假如没得到主人同意就去拿,人家说你是偷盗,而被盗的农民就是失主。但是,如果要考察源头,这些庄稼本是神农和后稷的。苏东坡硬是说,按照这个道理,这两首《屏迹》诗每一句都是我生活的实录,写的就是我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的诗,杜甫也不能禁止我拥有!话虽风趣,却见出杜诗不仅临大节时能够振奋意志,平常生活中亦能感发情趣。如此影响后世读者。
杜甫所以能登上古典诗歌艺术的高峰成为诗圣,与其家庭背景密切有关。杜甫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对唐代律诗格律的确立作出过重要贡献。杜甫对祖父的诗歌成就非常自豪,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又对其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诗歌是杜甫的家学传统,这是杜甫登上诗歌艺术高峰的有利条件。当然,杜甫成为诗圣还有更重要的条件,大致可以分成两点,一是时代的因素,二是个人的因素。
先看时代因素。杜甫的一生,适逢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代,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代。唐玄宗统治前期,也就是开元年间,共二十九年。那时玄宗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贤臣辅弼,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史称开元盛世。玄宗统治的后期是天宝年间,共十五年。从开元末年开始,唐玄宗逐渐萌发骄侈淫逸之心,贪图享受不理国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乘机弄权,政治日趋黑暗,国势逐渐衰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直到八年之后,安史之乱才算基本平定,但是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这个时期总长约五十年,从公元713年到763年,而杜甫的生活年代是从712到770年,两者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杜甫的一生,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大变动时代。杜甫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直到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杜甫成年以后,目睹天宝年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亲身遭遇安史之乱。杜甫最早从盛唐诗人的浪漫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又亲身经历安史之乱造成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写出了《三吏》、《三别》。可以说,正因杜甫经历了开元盛世,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才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并始终希望实现这个理想。正因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社会,他才对社会种种弊端看得清清楚楚,写出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写实诗歌。时代的急风骤雨在杜甫心头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杜诗中充满了哀伤愤怨、激昂慷慨。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本质正是内心抑扬起伏的情感波澜。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用这句话来解释杜甫与其时代的关系,是再确切不过。
杜甫的一生,在诗歌史上适逢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代。人们公认天宝末年是唐诗的转折点,清人叶燮和今人闻一多等甚至认为天宝末年也是整个古典诗歌史的一个分水岭。天宝末年杜甫45岁,几乎是他三十年诗歌创作生涯的中点。杜甫上与李白等人同属盛唐诗人群体,下为元白等中唐诗人的先驱。从汉魏六朝到盛唐,诗歌创作的实绩已有丰富的积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繁盛局面。杜甫此时崛起于诗坛,以集大成的姿态对前代诗人留下的遗产全面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举个例子:七言律诗的形式在杜甫之前已基本定形,但一则平仄常有失粘之病,二则题材多局限于应制之类,正是杜甫从格律的精严化与题材的丰富化两个角度对七律进行了改进,才使它达到与五律等诗体同样高的水准。更重要的则是杜甫在题材内容上为唐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盛唐诗人各有题材特点,如王、孟多咏山水田园,高、岑多写边塞生活。李白主要是抒写其内心情思,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够全面。杜甫则不然,几乎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所有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杜诗中的外部世界与诗人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所以被后人评为“地负海涵”。如果说盛唐诗歌以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为主,那么杜甫的诗开始转向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也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从唐诗的发展史来看,杜甫正是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宋人颂扬杜甫是集大成者,其意义既在于总结前代,也在于开启后代。

杜甫所处的时代在社会学、文学两个维度上都是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呼唤伟大诗人的时代,杜甫就是应运而生的伟大诗人。当然,生逢其时只是成就诗圣的外部条件,杜甫本人的人品和才具是更重要的内因。杜甫的才具,就是他在诗歌写作上的天赋和努力。他具有过人的天才,七岁就能写诗,开口咏凤凰。六岁时观看公孙大娘的舞蹈,留下的印象竟至老不衰。杜甫有过人的学力,他熟读经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如果说杜甫是诗国中的凤凰,天赋和学力就是这只凤凰的一对翅膀。况且杜甫对诗歌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进行创作,他把诗歌创作看作毕生的事业。无论是在携带一家老小逃避战乱时,还是在蜀道上濒于绝境时,杜甫都没有停止写诗。试想一般人遇到那种处境,谁还有心思写诗?杜甫却坚持不懈地写。杜甫是个早熟的诗人,他进入长安以前就写出了《望岳》那样的名篇。但是他对诗歌艺术的追求是精益求精,百般探索,不但希望超越前人,而且不停地超越自我。李白的创作,在艺术水准上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杜甫却不一样,从长安十年,到成都五载,再到夔州时期、湖湘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艺术风貌。杜甫对诗歌艺术的艰苦探索,只能用呕心沥血这个词才能形容。
现存杜诗共有一千四百余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自南宋以来,学界就有“千家注杜”的说法。杜诗拥有的注本之多,历代学者在杜诗研究上投入的力量之大,在古典诗歌史上独一无二。那么,杜诗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杜诗是安史之乱前后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画卷,是用韵语的形式写成的一代历史,后人称之为“诗史”。“诗史”的说法,始于晚唐孟启的《本事诗》,宋人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中予以采用后,广为流传。当然也有人反对,例如清初的王夫之,他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诗绎》)诗是诗,史是史,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就像嘴巴与眼睛一样。王夫之的话历史上影响很大。但是,虽然诗歌和历史是两种学问,两者之间并非就没有交叉点,仍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即使他用作比喻的两种感官,钱钟书先生的名文《论通感》就介绍过,不同的感觉器官产生的各种感觉之间存在着通感,可以互相沟通。更何况比喻并不是论证。所以诗跟史可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范本,就是杜诗。一部杜诗就证明了“诗史”的存在。
为什么说“诗史”完全可能呢?首先,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记录。历史的进程当中,物质形态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留存下来的就是记录,是集体的记忆。就这个功能来说,文学、诗歌,尤其是像杜诗这样的作品,当然具有这种功能。其实即使王夫之本人,也不知不觉地承认过杜诗的这个功能,他在自己的一部著名史论《读〈通鉴〉论》卷23中,就提到了杜诗。他说:“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这段话评论的是,唐政府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向少数民族借兵,首先向回纥,后来又向吐蕃借兵。借兵以后没想到请客容易送客难,借来的军队眼见中原区的富庶,赖着不走了。后来成为唐帝国的心腹之患,反复地骚扰唐政府。王夫之是史学家、政治家,他对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和感想。他在这里引了杜甫的诗,所谓“拟绝天骄”,出自《诸将五首》之二:“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唐政府本来提防着少数民族,怕他们侵略我们的地方,但是迫于无奈向他们借兵,把戒备之心都丢掉了。“花门萧瑟”出自《留花门》,“花门”是回纥的别称——“花门堡”,诗里说:“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虽然借兵对唐政府暂时有利,但是回纥乘机大肆抢掠,烧杀抢掠,关中一带被洗劫一空,原野萧瑟。王夫之这样引用杜诗 ,说明杜诗就有史学的记录功能,同时还有价值评判功能。怎么能说“诗史”说不成立呢?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说杜诗是“诗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诗是“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的最鲜明、最生动、最深刻的一种记录。看一个例子,“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数字:公元754年,唐帝国的人口总数是5288万,半个亿。到公元764年,“安史之乱”已经基本平定,这时唐帝国的总人口是1690万。十年之间,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凡是在并无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有如此大幅度的降低,它肯定发生了非常残酷的人祸。“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的一场大动乱。历史文献虽然可以提供一个具体的数字,但那仅仅是个冷冰冰的数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过程中的细节是什么样子?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多少创伤?这些情况,历史文献中间没有。从哪里能看到呢?从文学,从诗歌,从杜诗。关于安史之乱中人民的大量死亡,杜甫晚年在湖南写的《白马》诗中有这样一句:“丧乱死多门。”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人的死亡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太平时候,人们的死亡方式比较单一,老死了,病死了,等等。但是在战乱的时候,人会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死亡。关于安史之乱前后,人民各式各样非常态的死亡,记载得最详细、最生动的绝不是《资治通鉴》,也不是《新唐书》、《旧唐书》,而是杜诗。我们读杜甫的“三吏”、“三别”,读杜甫其它的诗,可以看到具体的描述。从这一点说,诗歌不但可以弥补历史,而且还有历史所不可取代的一种功能。
更重要的是,杜诗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而是在纪实中抒写内心的强烈感受。清代的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三朝”指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就是杜甫经历的历史时期。例如《北征》,当然是抒写杜甫自己的喜怒哀乐,写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写他对那个动乱时代的各种感受。但与此时,此诗也写到整个唐帝国的形势,唐军准备从叛军手中夺回长安,唐帝国向回纥借兵平叛等事件,以及诗人对形势的思考评论。认真读过《北征》,心中就有了那个时代的生动画面,也有了由那个时代产生的真切感受。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史学传统,清代的章学诚有一句名言“六经皆史”,其实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全部古代经典都是历史。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关键就在于历史是集体的记忆,铭刻在民族的心中,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和价值。这个道理其实很清楚:“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就是说,把思想用逻辑推理或理论体系来表达,不如记录历史事件的过程,在叙事中予以表达,更清楚,更容易理解,更容易体会。孔子整理《春秋》,就是认为政治、伦理方面的见解可以通过修史体现出来。通过对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记叙、评论和判断来体现思想。人们常说孔子修春秋的意义在于微言大义,通过对史实的记述表示其褒贬态度,杜诗与此非常相像。杜诗在记录历史事实时渗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后人可以借此了解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前进。就这一点来说,杜诗与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称杜诗为“诗史”。
先师程千帆先生到巩县拜谒杜甫陵墓后曾作诗抒感:
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
以诗为春秋,褒贬无不敢。
诗圣作诗史,江河万古流。
兹丘封马鬣,永与无同休。
杜甫其人是诗圣,其诗作则是诗史。这两者皆鲜明地体现出儒家风范。杜甫是名符其实的唐代大儒,诗国中的儒家圣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