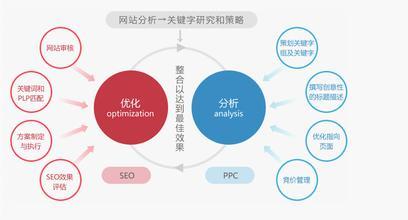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林希翎
吴昊
2009年9月19日,林希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55万右派份子(官方数字)中六个没有被改正者之一。林希翎用她悲凉、超俗、智慧和屈辱的一生为那个小得可怜的“右派分子分母”做了最后的“贡献”;中国只要有一个右派,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99.999%的右派改正了,只要还有0.001%不该正,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只是“扩大化”问题。这就是逻辑,某些人至今仍在坚守的逻辑。正确者永远正确,有理者永远有理。历史就是如此。那些遵命书写历史和党史的人,他们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按此逻辑书写历史和党史。“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永远变不了。林希翎——这个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用毛泽东的话说,她是“带者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林希翎小我一岁,她1954年、我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是法律系学生,我是新闻系学生。我们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俩不认识,不联系,不接触,但我的被划右派却与她有关系。整党之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次整党,是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我写大字报是想探讨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大字报的标题是“贵族化产生官僚化”,我认为物质生活脱离群众,就要产生官僚主义;文中也有为农民说话处:“合作化太快了,统购统销太死了,老百姓吃不饱。”大字报写好后,我没有往外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自由主义。可好,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王佩今和我同室,我对他说,“我写好了,交给组织上吧。”他说。“放那儿吧。”过了十几天,王佩今对我说:“你自己贴吧,人家都是自己贴的。”这样,我才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巧得很,上午贴出去,中午就是一场暴风雨,把我的大字报吹没了,很少有人看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同志们都说我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来,突然有一天,系里开大会,一个同学举着一份油印的材料上台说:“我们系有个吴元富(我的本名),是个漏网大右派,他的大字报登在了林希翎办的《广场》上。”从那以后,我的问题性质就升格了,成了敌我矛盾了。于是大字报、漫画都来了,连续的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我低头认罪为止。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到了林希翎手里呢?原来我们系有个叫韩洪棣的同学,他是林希翎的铁杆,是他把我的大字报抄录给林希翎的;若是没有韩洪棣——林希翎,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漏网右派”。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稍后,她在人大的发言和对她的辩论,全校举行了好几次大会,地点都是在海运仓礼堂;人大校舍当时有三处:西郊、铁一号、海运仓,我们新闻系在海运仓,所以这些大会我都参加了。当时我觉得,林的发言,言语犀利,尖酸刻薄,情绪偏激,但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正在倡导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解、有思想、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林希翎第一次发言后,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分成了支持她的和反对她的两派,支持的占多数。第一次辩论会报名发言的比例是26:8,支持26,反对8。发言的顺序是一对一,讲一个支持的,再讲一个反对的。会议由学生会主持,主持人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但因发言者情绪激动,双方都有不那么冷静,出现了挥舞拳头、高声吼叫的情况。作为学生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组织那样的大会,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开始两次是自由辩论,但后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因蛇出洞”的部署已经完成,可以明显感到,事情的性质真的起了“变化”。学生们傻乎乎的,不知道。后几次开会的时候,礼堂后面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并架起了摄影机,也有人时不时的到前面去摄影,有人说礼堂后面的陌生面孔是中宣部的,也有人说是总政的,还有人说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活跃气氛,多了一些肃穆和阴森。发言者支持林希翎的由多数变少数,由少数变个别,林希翎则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已经来临。
林希翎当时的发言,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她讲的有道理,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胆识,那样的表达能力,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林希翎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看过,但在2012年第三期《炎黄春秋》胡 治安的文章“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看到了人民大学党委22年后的“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依然认为林希翎是“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当年,我几次听林希翎发言,她对社会制度确有看法,有意见,但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民大学在反右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该校的《右派言论集》(后收回),当年林希翎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是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她的这种思想是出于期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谁又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是纯粹的社会之义了?社会主义还在探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在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封建社会的阴影,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完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国人民的信心所在。林希翎当年的思想,只能说明她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她抓住了克服“三害”的本质。林希翎说的社会制度,并非泛指,她说:“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三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制度不好,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她还具体的讲了“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官僚机构”等问题,林希翎的发言,半点看不出她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洁净的、火辣辣的,她爱我们的国家,也爱给她知识、使她成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很遗憾,人民大学党委反右的时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林希翎定为极右分子。22年后,在做“复查结论”的时候,他们仍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不给林希翎改正。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有些人就是不变。此外,林希翎还对胡风问题、肃反问题、民主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历史证明她是对的。和她有类似观点、发表类似言论的右派都得到改正了,就是不给她改正,就是叫她抱恨终生,就是叫她死不瞑目,这对当年一个22岁女大学生,公道吗?正常吗?可思议吗?事实让人承认,中国的“老左”确实厉害;他们即使不能左右全局了,但在个别地方,他们还是老大,还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老左”很会装孙子,常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们也是这样那样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卡着林希翎,至死不变就是证明。林希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儿子在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三个西红柿。在国外,她扫过大街,端过盘子,但没有背叛过她的祖国。在国内,她蹲了15年监狱。1957年,我离开学校时,她没有离开,留校做反面教员。当这个“教员”的滋味,可想而知。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前些时,她的亲属把他的部分遗骸迎葬了她的故土,在她的墓誌铭上有这样的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原来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她是死的很明白的。
回想当年,我在听林希翎发言的时候,就觉得她偏激,得理不让人。比如,她说“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尽管她解释说“有一部分帨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但仍然激怒了台下的一些党团员。比如,她听说有人要查她的历史,她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母亲带着我乞讨,我是在乞讨的路上参军的,当时我们母子俩的财产只有雨伞一把,你们查吧,屁都查不到!”听了,让人感到刺耳。
林希翎过激的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外界环境对她的影响和刺激有关。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林希翎本名程海果,为什么改成了林希翎呢?她是取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所以叫了林希翎。为什么要取这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呢?原来此前开展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林默涵、李希凡、蓝翎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林希翎这样做,是符合她的性格的。那时,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独立见解,加之她是年轻的女大学生,按现在说就是“美女作家”,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吴玉章校长还特批了一间房子,供她写作。林希翎因此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社会名流,如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张光年、侯镜如、邓拓、张黎群等,她说吴玉章、胡耀邦是她的后台,她比较傲气,好夸夸其谈,生活上也有些不够简点。学生没钱,她说她常和这些大人物要钱花,并说有时掏他们的口袋。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批评她的文章,题目是“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瘡——记青年作家林希翎”,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是非常尖刻的,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文章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标题是“加冕”,一个年轻的女人用双手把“青年作家”的桂冠举在头顶上,面目十分可憎。文中用了这样语言:“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吹嘘和欺骗”“东抄西节的拼凑了一篇草稿”“剽窃”“小小的欺骗”“更为肮脏的手法”“冒充”“毛孔眼儿里都冒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铜臭味”“七拼八凑、东抄西录,集烦琐、庸俗和错误的大成的东西”,文章的内容几乎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没有核对过的。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这样对待年轻人不妥,无益。可好在院子里碰到了系主任安冈同志,我向他说了我的意见。安冈同志说,你可以给中国青年报写个意见,后来我真的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但没回音。再后来,再听说胡耀邦同志批评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了挽回影响,请林希翎以该报特派记者身分到大西北采访。这件事情尽管有关方面在事后进行了补救,但在林希翎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被人说成是这样污秽,这样丑陋,这样无耻,这样不可救要,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大报上公开发表,她在心灵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做了补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事实和教训”的编辑部文章,作了检讨,但林希翎的情绪仍然不能平静,就像一个无辜的人被人打了黑枪,伤痛是永远的。
第二件:林希翎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不知法律系的党团组织出于什么考虑,自从林希翎在北大发言以后,她的活动,系里总会派人跟着她。她说:“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林希翎不管参加什么会,法律系都派两个人跟在她后面,在她讲话之后,跟着她的那个女人就会走到前台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每次皆如此。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对这种做法,都会感到反感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总有人在后面跟着呢?难道这不是一种耻辱吗?有一次她在会上说:“对于我,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安全的,我身后有尾巴跟着,他们就像特务一样,我的行踪,他们比你们清楚。”接着她会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被林希翎称为“尾巴”的那两个人,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是那个女的,穿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木雕脸,没有表情,似乎不会笑,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她走到前台,像留声机一样重复那几句话。我当时就很想不通,这两个人代表谁?行使的是什么使命?
到了六月中旬,各教研室、各系的右派不断被挖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每天就像丟了魂似的,四处申冤,我找过系领导,找过校党委,也找过北京市高校党委,都没用。6月13日,党支部通知我到铁一号开会,我一头雾水,不知开什么会。到那儿以后才知道,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章奇顺,章教过我的课,我对他印象尚好。林希翎也去了,当然还是那两个“尾巴”跟着。林希翎和章奇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章奇顺在课堂上讲过铁托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对人的关怀”,他例举中国的人民公社让女社员把奶水喂猪崽,说这是不人道的。林希翎同意章的说法,于是俩个人成了“臭味相投”。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林希翎走上台,那一天,她穿了一身洗得快成白色的旧军装,两个小辫系了两根白布条,她非常悲戚地说:“今天是林希翎事件一周年,我心里很难过。去年的今天,他们在人格上搞垮我,说我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今天她们又在政治上打倒我,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他们说的都是鬼话,我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国家,历史会证明,我林希翎是无辜的。”她谈了她的一些观点、看法、意见,经过这些天的辩论、批斗,她一点都没有变,对于章奇顺,她一句话也没说。她说完以后,跟着她的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女人照例走上台,照例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林希翎依然是不屑地看着他们一眼,依然回报了一声轻蔑的冷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林希翎,以后,听说她在宿舍里(她住的是单间——吴玉章批的)总是脱得光光的,同学中传说她是流氓,其实她是在反抗,每天都有人骚扰她,揪她,斗她,不厌其烦,她才脱得一丝不挂,把那些人拒之门外。再以后,听说她被判刑了,住监狱了,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胡耀邦说林希翎是“最勇敢最有才华的青年”,林希翎在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时,为耀邦题“八无八有”:
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 无仇无敌
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 有胆有识
有人说林希翎是在写她自己。
2012,5,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