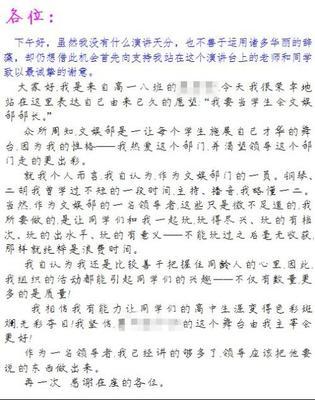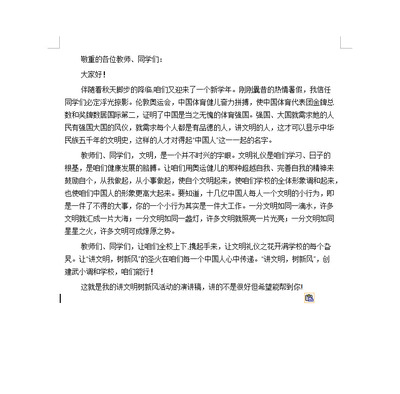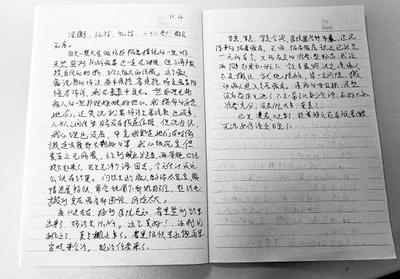第六章 怎样写诗
1.诗人,向你们的同行求艺
只有当你是一位最深沉、最忠诚、最富独创性的诗人的时候,只有当你已经充分了解被你弃之不顾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不管什么格式和韵律。
——伯特·麦泽
有人请我为刚起步的作家提一些有用的建议,年轻的诗人们,我只好现身说法了,因为诗是我最了解的艺术。老实说,让我来扮演一位充满智慧的年长的说教者,实在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我既不老也不睿智,而事实上连我本人也还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哩。要是真的可能,请让我和罗伯特·弗罗斯特,或约翰·克罗依·兰瑟姆,或W·H·奥登谈一谈,关于诗这门优美而艰难的艺术,我有多少问题要问他们呵。何况,那些前辈大师们留给后辈的箴言总是出其不意地涌上心头。不过没关系,我还是打算说两句,它们可能非常容易理解,听上去也几近是陈腔旧调了,而且还有人不断地在重复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经历,观察,反映和记忆,要努力将它们作好,因为它们将带给你全部生活的感受(亨利·詹姆斯语)。你的经历不必多么广,但是要深。想一想埃米莉·狄金森是怎样生活的吧!没有性,没有旅行,没有毒品,没有职业,也根本不求什么生活方式,可是却很少有几位美国人能像她那样生活得充实而认真。认真过你的生活吧,一个人是不能仅凭书本来写作的。
·阅读。话说回来,一个人又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来进行写作的。诗是来源于诗的,读写不分家,一个不懂得阅读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读历史书籍、小说、科学著作,读一切你喜欢的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诗。读书也同生活一样,要求深人,而不贪多。要读一流的书,如荷马的、维吉尔的、但丁的、莎士比亚的,还有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要坚持不懈地阅读。
·要反复修正自己写的东西。当然你不一定一辈子都不断地把自己写的东西改来改去,但是,严谨、生动而充满灵气的作品来自于你长期地坚持写作和重写,漫长的考验和失败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最早的想法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想法,而且诗歌又不是爵士乐,它并非总是即兴而作。事实上,最早的想法常常显得平庸和不集中,沿袭传统,而且也不大协调。大部分诗歌会要求打许多次草稿,有时可能是20次,还可能是50次呢。不要太容易满足。
以上是三条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你遵守起来不那么容易的话,可能你命中注定作不成诗人。不过我还想告诉你一些东西,尽管我的话可能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你必须学会写韵诗,不是“胡诌”的韵诗,而是真正的韵诗,完全符和节奏和韵律,或随便你怎么叫它们。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诗人们都是这么写诗的,而只是近几十年来非韵 体诗才开始流行,渐渐成为新的规范。如果硬要给这种新规范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它该叫做违反规范的规范吧。
在你打破规则之前,你应当先了解那些规则;在你寻求新颖的创意之前,你应当宣称你对前人的成就都已了然在心。这只需要最简单的诚实和谦虚就可以做到,否则你就还不够格把自己称作诗人。一位不能用韵文来写作的诗人就像一位不会画素描的画家,或者像一位不懂得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来工作的科学家。其实,一旦你已经掌握了这种本领,你一定会发现写韵诗将使你的诗句更加完美,它将开启你的思想,引你步人原先你从未想到过的境地。而且你终将明白许多诗人早已知道的道理,那就是自由体诗并不比韵诗更容易,而是要难得多,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写出好的自由体诗来。正如安德烈·纪德曾经说过的,艺术源于约束,而毁于过度的自由。
那么,你究竟怎样开始学习写格律诗呢?诗人们几乎都知道,一边读优秀的格律诗,一边尽力模仿它们的声音,这样就可以开始学习了。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准确地找出诗句中的音节数和正确的重音位置,你可能会用上你的手指头,不过不久你就可以通过耳朵来练习了。与此同时培养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是十分有用的,但不要忘记,一行抑扬顿挫的五音步诗最终听起来就该像是一行抑扬顿挫的五音步诗。就像你学习一首古老而熟悉的歌曲旋律,你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学习诗的韵律。
要谨慎对待你寻求的指导:因为许多老师对诗律知之甚少,当今大部分诗人也几乎一窍不通,而书本又极易误导,甚至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乔治·斯蒂沃特的《英诗技巧》是本好书;詹姆斯·麦考利的《诗法》也相当不错,篇幅不大但可能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德里克·亚特里奇的《英诗步韵》。
请记住,那些优秀的诗体学者虽然大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听诗,却往往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和韵律分析符号。一定要知道自己习从的都是优秀的典范。许多当代诗人也用所谓的格律来写诗,只是写的糟糕透了,很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来玩这套游戏。如果你跟从下面这些人来学习是绝不会错的,比如马洛维、赫尔博特、约翰森、弥尔顿、蒲伯、丁尼生或弗罗斯特,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出一百名。如果你想读一读你同时代诗人们的作品,我可以向你们推荐菲利浦·拉金、埃德加·鲍华斯、唐纳德·贾斯蒂斯、理查·韦尔伯、安东尼·海希特,还有新近著名的美国诗人亨利·库莱特,当然还有其他优秀的人物。
所有优秀的诗人组成了一个庞大而自由的群体。无论白天或黑夜,你随时都可以从中选出任何一位你喜欢的老师,向他求教。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作品来,都要大声朗读,不管是你的老师还是你自己的作品,亦竖耳倾听。听录音带可能也会有帮助。有些优秀的诗人,像弗罗斯特、拉金、贾斯蒂斯、韦尔伯、兰瑟姆等,他们本人朗读的诗也非常出色,多听听他们的录音或磁带可能大有收获。
一旦你牢记了诗歌的曲调,你将永世不忘,而且日后碰到它的任何变体你都能一下子识别出来。你最起码应该学会写五音步、四音步和三音步诗(诗的行数越多或越少写起来也就越加困难),各种风格的作品都要试着写,如严格符合抑扬格律的和格律松散的,按通用格律的和按叙事韵调的,押韵的对句,三行诗或四行诗,以及无韵诗或马马虎虎的十四行诗等。你越是能运用格律写诗,就越能更好地欣赏旧体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之亦然。
如果你真能听懂那些杰出的诗,并能或多或少洞悉诗人们的真正意图,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这些杰出的诗歌当初正是为寻找日后的知音而创作出来的。如果不坚持这样的训练,最终你对于用你的母语创作出来的诗歌的理解则可能是不全面的和不完美的,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甚至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男人或女人也是如此。毕竟,抑扬顿挫的诗歌,无论它的发明和发展,都是我们文化的荣耀之一)。
一旦你对以上的训练已经有了把握,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试着写自由律诗了。由于你已经学会了一些创作真正像诗句的方法,你就不会再像除了自由体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的人一样了。你一定会干得更好,而且你会真正体会到,就诗歌所能传达的各种魅力来说,自由体并不比韵诗更高明,无论是在表达情感、澄清思想、变幻节奏、勾划微妙的音调或在揭示深邃的意义方面,还是在把思想和情感有力地加以突出、调节、升华和紧密联系起来方面;特别是从错综复杂的神秘现象中揭示出深义方面,而这种能力惟诗歌独有。它能让我们感到那些词句的声音正是它想要说的东西;而正是这些声音深化、拓展。再现和暗示了那隐藏在声音背后的现实,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这种现实。正如亨利·库莱特曾写的那样,“格律就是思想,它是读者与作家亲善的基石。”
以上也只是韵律的部分功用。我不是叶芝,不过我还是要告诫你们:年轻的诗人们,请遵循他的年轻伙伴们的话吧,向你们的同行求艺。咏诵出最美的歌。
2.向隐藏在诗中的形式进军
用明智的方法将自己的心交给她,诗神就会来敲我们的门。
——格雷格·格拉兹纳
任何一名有抱负的诗人都喜爱读诗。每当你写诗的时候,有好一阵子,你的脑中一定储存着你最钟爱的诗人的作品,我这样想恐怕不会错吧。早在我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储存。我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而着迷,这得感谢我的教师。格拉姆斯夫人可能没那么出众,但她热爱诗歌,她曾教给我们一首非常伤感的诗,是由一名二战时的战斗机驾驶员写的。诗是这样开始的,“呵,我已滑过大地阴沉的边界,在如银翼般闪耀的云朵上飞舞。”至今我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全诗。
整个初高中时代我都把诗歌遗忘了,直到上大学的第一年,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与弗罗斯特又一次相会。“森林,她多么可爱,幽暗,深不可测”,布鲁勒教授在高高的讲台上低声吟诵,于是我记忆中的精彩诗句的储量又开始增加了,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接下来的15年中,其他诗人,比如里尔克。斯蒂文斯、惠特曼、叶芝、狄金森、奇耐尔、弥尔顿、罗斯克等人的作品越过弗罗斯特的诗句走进我的记忆。至今,它们依然像我读大四时看到的那样精美、新鲜,那时我才第一次读到《驻足在一片雪夜的林前》。
对读诗的喜爱应该是你想成为诗人的第一个动力。一首诗一旦你反复读吟,你就会渐渐地充分把握它。第二个动力应该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断地修改的欲望,这一点在你刚开始写诗时显得尤其重要。第三个动力就是对探索将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的痴迷,尤其在你已经掌握了某些技巧和知识之后,这种痴迷就更显得重要。
即便是一些大师也曾和技巧搏斗过,而且这种搏斗不仅限于诗人。查理·帕克尔,这位爵士乐史上颇有争议的最了不起的音乐家,就曾在坎萨斯城以最糟糕的萨克斯演奏家而著名。很显然,他的境况糟透了,以至恶名传出以后,他甚至连一家愿为他试演的地方都找不到。就这样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与他的同伴迪策·莱斯皮合作练习,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勤奋不辍,为后人留下许多经典之作。他曾说他每天要练11到15个小时。难怪他成熟后的独奏作品听起来让人觉得是如此轻盈而毫不费力,充满惊异和勃勃生机。炉火纯青的技巧终于可以使他充分地发挥出他的巨大才能,用以开创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音乐风格。他根本不必再分心去考虑某个音演奏得是否准确之类的问题。
诗人也许正同爵士音乐家们一样,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创造一种发自内心、充满智慧的音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刚开始你就要学会欣赏诗,因为几乎每一首诗的意义都是需要意会的,而不是像它的文字表面所显示的那层意思。为了创作意在言外而又能给人以启发的诗歌有许多种方法,其中最令初习者感到头疼的方法有三种,它们是:声音、音调和意象。
当我使用“声音”一词时.是指隐藏着的由诗句中的语汇和句法揭示出来的作品的品质。也许这样的定义听来有点晦涩难懂,其实不然。在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会无意识地从声音中得到愉悦。请看下面这个虚构的有关个人体验的例子:
圣诞节期间,我们一大家子人都相聚在我父母的家里。有人给我母亲带来了一个新宠物——一条三个月大的丹麦大狗,它一进屋就把我们家的躺椅撕去了一大块。我祖父正好是第一个目击罪案发生的现场人,他笑眯眯地说:“我想咱们得赶紧准备一个狗棚了。”接着我的小弟大卫走进来说,“这么说,它跟罗伏尔没什么两样,还没开午饭,它就先跳上桌偷吃了一口。”我的母亲直接冲狗发了话:“嗅,过来吧。你会干得比这还要出色的!”
这里,人们谈话的方式向我们透露了大量有关他们个性特征的信息。所以一首诗的诵读者(不一定是作者本人),他(她)的诵读方式听起来应该是真诚可信的。比如,在我的讲习班里有一名新手的诗是这样开始的,“布满青苔的河水越过碧绿的山峰滚滚向前……”,只要一听,声音的问题马上就蹦了出来。初习写诗的人常常爱选择极至或强烈的词语,以至听起来有点假。所以这位过于注重形式的诗人在念出‘怖满青苔的”河水之后就不该再以同样口气念出又一个形容词“碧绿的”,因此这里还存在一个前后不协调的问题。通过调整词语的重心,把注意力从形容词上挪开,这名学生重新写到“从绿色的山涧出来,河水被苔藻覆盖……”,这样听起来要朴实多了。声音听上去应该是灵动的,而不是矫揉造作的。
初习诗作时,新手们都会碰到些实际困难。我曾为自己的诗集写过一首9页纸的题头诗,名叫《来自铁轨那边》。在写作那首诗的日子里,我在300多页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诗稿。那真叫~种艰辛呵,特别是当我写到全诗的第四部分时,先前完成的草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几乎同时向我喊出一个声音——音调,你的音调出了问题。说起“音调”,当然我是指作品的整体气质和情绪。
刚开始的几行写得还可以,只有几个小地方需要改一改。下面就是后来出现在书中的那几行:
越过前人的井,
走下坚硬的台阶,还有
破碎的栏杆,半新不旧
坏了雕梁的旅店
我的兄弟——最后一名合法的房客
打开通往地下室的门
室内的空气中,他呼出的伏特加,还有
一丝灰蓝色的静溢。
他接通电视,用一截电线
一头连着小汽车的电瓶,还有
赠我的一杯啤酒。我只好
抬起头,朝后仰,一醉方休
20岁,那最初的热烈和被逐,
这最后一问有人居住的房子,还有
酒的芬芳和微光荧荧,像一幕
年华的内心……
到此为止,整体情调是怀旧的、质朴的,而且一切都十分自然地源于内心。它显得非常诚实。但是在接下来的诗句中,诗的发展选择了错误的转折。下面是最早出现在手稿中的样子:
扭曲的光柱和墙砖
在意识中沉沉升起,转眼
如幻如真,仿佛未来
曾经有一个高空建构——
太沉了,一种残暴而无形的力量,
我受不了,只好遗忘。
那记忆中的往是的魅力都上哪去了?看这些句子,“在意识中沉沉升起,转眼/如幻如真,仿佛未来/曾经有一个高空建构”,其中的音调是那么冷漠和让人费神,联系上下文来看,这几行就显得生硬且软弱无力。为了直辖市音调,我又重写了这一段——为了找回那种初我愚蠢地抛弃了的“感觉”:
我们死盯着电视
仿佛它会给我们带来转机,
即使墙砖和扭曲的光柱,带着
如未来般步步进逼。
天顶又一次呻吟,我倚近
那此伤感的小提琴。
有一个钟头了,像僵尸一般,我,和我的兄弟……
声音和音调合作,创造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一首诗,它来自可信的、人类生活的根本,而意象正是通过这类感觉使主题生动活跃起来的。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意象是他们作品中的绝对核心。诚然,某些伟大的作家非常善于在诗歌中运用有力的抽象表达,华莱士·斯蒂文斯就是因为这么做而被誉为一名现代派作家的。但是在大多数新手的作品中,思想和感情不是通过意象来转述,而是采用直接的抽象表述,效果往往显得虚假而平板,甚至可能把诗歌毁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说的“思想诉之于有形”,似乎是专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写诗新手们写下的。由于记住了威廉斯的话,一位年轻的诗人就把自己特别钟爱的一句诗“由于你的缺席,我怀着热望彻夜无眠”改为“你走了,街灯熄灭/那蓝白色的光芒掠过我的床前”。这一改将视觉和触觉融为一体,使诗句顿时生辉。诗是一种美的体验,而不是什么浅薄的哲学思想,也不是无聊琐事的堆砌。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意象是使作品生动起来的重要方法。正如诗人米勒·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让它如电影般一幕幕流过。”
意象、音调、声音,以及其他众多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经常在诗歌讲习班里被讲述。只是那里的老师应该既是优秀诗人,又是位好教师。如果你想尽快提高自己水平的话,讲习班是最佳的去处。那么接下来,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一名诗人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技巧,写的东西比那些成千上万的刊登在美国几百家文学杂志上的诗人们的作品毫不逊色,这之后又该怎么办呢?长久的学徒期已经满了,下一步呢?
简而言之,请延续你的自我约束吧。作为一名严肃的诗人,在已经通晓如何写出一首像样的诗之后,难道他不想走得更远,继续探求对诸种形式的理解吗?想想戈威·奇耐尔的早期作品,他曾受到50年代形式主义的深重影响(不过这些作品中有一些还是相当出色的);再看一看他的代表作《恶梦之书》,那些最基本最典型的体验,是如何通过支离破碎的自由韵律的诗行逐渐加以展现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黑暗、热烈的美国式的音乐。再想一想隐居在她父亲家中的狄金森,是如何运用智慧和孤独把教堂颂歌的魁力融人一般韵律风格之中的,使她那些短小有力的颂歌风格备爱青睐。还有查理·帕克尔,那些急促的变音的浪花一阵阵涌过,它们飞过了旋律本身,在那个几乎所有的精神支柱都分崩离析的时代,为无数沮丧的灵魂找回了一种新的尊严。
因为年轻,谁都可以开始,像丹尼斯·琼森说的那样,“如同从星星的炉膛里溅落的火花。”只要我们够运气,就像我在大四时经历的那样,能用明智的方法将自己的心交给她,诗神就会来敲我们的门。我们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经历是如此奇特,他们的生活始终听从人类之声丰富而神秘莫测的节奏的牵引,他们一生耕耘不辍,自学成才。
最后,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地知道我们是否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一首重要的诗。但是,这样的进程——阅读、起稿、迈向形式的完美,正是一条由雄心勃勃走向意味深长的人生之路,缺少任何一环都意味着对诗歌的愚弄。
3.诗的影像
一个灵感还不是一首真正的诗,但假如灵感真的来临,只要你肯下功夫,并且努力去创造一个相应的影像,灵感就一定能变成一首真正的诗。
——彼德·门克
近来在一些年轻的作家们中间,新形式主义这个词正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总的来说这不是件坏事。
然而新形式主义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与最主要的问题无关:写出来的诗到底好还是不好?写一首自由体诗或一首十四行诗本身既不是美德也不是罪过。关键是,它好吗?
我的理论是,每一首诗都应有一个宜人的影像,而诗人的工作就是去发现这个影像(我想影像这个词的含义可能有点接近古拉德·霍普金斯的术语“内景”这个词,他用来指一首诗所属的“类型”)。关于这些影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的,不过我相信有一些诗从头到尾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表现的方式,而另一些诗看起来像古代的六行诗之类的东西。一个诗人,在他(她)还在为一首诗打草稿的时候,就应该明确知道这首诗的总体倾向是什么。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地熟悉各种倾向。
以下是我为自己的诗集写的题头诗,名字叫《水纸》:
水纸光滑得像一只蜗牛,这位小牧师
饶恕着我们的罪过。他轻捻下颌的
胡须尖儿——阿不拉卡达不拉!又一份清白的纪录。
我们认识那些糊涂大脑
只要嗅一下那份纪录,很显然
被抹去的绝不仅仅是墨迹
啊想象力,它
能使一切改变……在我们军中,
我们的顶头中士剃完了胡子要喝酒,他使劲吸
直到我的老香袋里尽了最后一滴。
酒如水纸般在他的脑瓜里产生了效力
他好像已经滑过了海德伯格的大街
在寻找着那间依达霍一瓦兹镇上的老屋,
噢他原来生在那儿……如果我就是上帝
我将命令那张神圣的水纸
每隔七年就来把我们的错误清洗
我们犯了错所以就该送来顺受
可是七年啊,它真够长。所以我们大家都
有份儿抽空随处走走
就在一切都被错误地记下来之前
去看一眼我们当初诞生的老屋
在这首诗的最初几份手稿中,整篇只有一段,属于一种常规的(或叫不常规的也行)自由韵诗,差不多只有最后定稿的一半那么长。后来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有那么多顾忌,能写多长就写多长吧,一直到自己自然而然地停下来或精疲力尽为止。当我照着这样的想法干下去的时候,我开始考虑关于这首诗的最佳结构的问题。很显然,尽管那些句子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长,但却不必强求非常规则的押韵和格律变化,就是说不必用一大堆押韵或差不多押韵的词语来组织全诗,也不必让五步抑扬格的小马达躲在文字下面哒哒地响个不停。
紧接着我注意到这一句,“酒如水纸般在他的脑瓜里产生了效力”,它差不多正好在全诗的中间,所以我干脆让它孤立起来,自成一节。我喜欢那种事物因其自身的力量而独立其行(就像诗中的水纸占领的那一小声属于它的领地)。就这样,我将剩下来的句子和短语搬来调去,以上面的那一句为中心,各自以相同的行数向上或向下依次排开全诗的影像。
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一首影像很有趣的诗,两头大约各占十二行,紧紧夹住非常瘦弱的只有一句话的中间一小节。这样一来,整首诗读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也可能有些地方弄不大懂。接着我开始寻找第一个自然休止的地方,它出现在第三行的短语“又一份清白的纪录”后面,于是我就把以上的句子安排成一个三行小节(似乎真的是这样:又一份清白的纪录)。然后我就想以中间的那一行为界,两边各写出三段三行小节来。那应该是蛮不错的,可就是怎么也安排不起来。也许是这首诗本身不喜欢这样的三行分节法吧。
又过了一会儿,我认识到这是一首带有宗教倾向的诗。我开始紧盯着这些熟悉的白纸黑字发愣,看看自己究竟还会想到些什么,它们会将我引向何方(诗歌常常是意在言外的,而那些表面的事物不过是借以进人诗人心灵的依托)。当我发现我把“七”这个数字用了两遍之后,我毫不犹豫地为全诗确定了最终的对称影像——三/七/一/七/三,因为所有这些数字都有它们的宗教含义。维系这飘忽不定的思绪的要旨便是要发现一种影像,以使你的诗能最清晰最生动地在这种影像中表达它自己。很少几个读者会注意到你的苦心经营,就像没有人能用肉眼看到支撑你身体的脊梁一样,但是一旦你煞费苦心地做了,它就会特别重要,因为它支撑着你的诗。
这样做你便容易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工作该结束了。特别是一旦到了为影像做推敲的阶段,你会更有把握确定你的诗应该到此结束了。在写《水纸》的最后阶段,当我凝视着它的整体结构时,我注意到在第二小节(定稿)中的“改变”和“在我们军中”之间有一段想象的空间;而这想象空间也出现在第四小节中的“出生在那儿”和“如果我就是上帝”之间。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对全诗的每一小节进行了如此特别的划分,我是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这样一来我就创造了一种类似镜中幻象的效果,只是这边去掉两个词,那边加一些感叹,在这种一边七行一小节的形式中制造了4/3:3/4的对应。可是谁会在意呢?我自己在意。就像一个画家,他仔细打量着就要完成的画面,总觉得哪儿还有些不满意。最后他终于在画面的左下角抹上了一笔红色,然后满意地说,“这就对了!”尽管别人谁也不会在意它,但画家本人知道他已经完成了这幅作品。
我希望当你读《水纸》的时候,感到它十分自然。这一切正如叶芝所说的:
一行也许会占去我们太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因为它寄托着一瞬间的思想,
我们的东涂西改也许就只是枉费心机了。
也可以为诗的声音设定影像,从最开始的押头韵到结尾处一连串“受”、“够”、“都”、“走”、“误”、“屋”的运用。当然,其中有些东西在初稿中就已经出现了,但有许多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潜藏于诗中的声音清晰地勾画出来,我抛弃的东西就更多了。
我希望诗的声音听起来也是“真实的”,我以为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可是有些感受不得不因为要勾画声音的形象而被牺牲掉。举例来说,我的可怜的老中士确实很爱我的老香袋里的酒,这倒正合适,因为“老香袋”这个词和前面“想象力”这个词很般配。可是我实际上住在史万福特,而不是在海德伯格。而且我知道我的老中士是奥兰多人,而不是布瓦兹人。很显然,仅仅为了各种声音间的和谐,我才采用了海德伯格一依达霍一布瓦茨等地名的组合。“他好像已经滑过了史万福特的大街”可能与事实相符,但它放进诗里以后的声音听起来却有点别扭,以至阻隔思想表达的通畅。
另一个简单些的例子是下面一首诗:
打着绿绑腿的士兵们
维拉一史凡诺瓦,1987
爸爸和女儿行进在柏树间,
青苔把树干
朝北的一边
由黑染成了绿
就像打着绿绑腿的士兵们
噢他真想说
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剑
(多么自负,真像一个爸爸!)
噢她真想说
让我们家中见
(女儿她多么伤感!)
可音乐在脑中盘旋
他们仰起脸
左右左右大步向前
神气得就像任何仪仗队列
突然间大树也齐步向前
轰的一声颓然倒地
就像炮弹来自不远的前线
鸟儿飞散
如迷路的邮差
看白旗从堡中升起
他们扑地跪倒双膝
那就签约吧:
只要签约——管它是我的、你的
这首诗一开始在我脑中有好多个“影像”,后来我终于确定用对句的形式,一组接着一组肩并肩地写到底,正好暗示出诗中的两个人。一份早一点的草稿是这样的:
爸爸和女儿行进在笔直的柏树间/青苔在朝北的一边把树干染成了绿色/就像打着绿绑腿的士兵。/他想说,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剑吧。/而她想说,让我们家中见……采用对句的手法使全诗更集中,诸如括号的使用以及其他许多变动都只是为了使新的结构更醒目(比如增加了一些突出军事气氛的内容等)。
分歧永远是存在的。有些人崇尚“本能冲动”,他们很少重写(如爱伦·金斯堡),也有人喜欢“反复推敲以至优美”(如叶芝)。其实谁也没有错。有一些句子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这叫灵感;而另一些句子正是为了实践这灵感而反复推敲出来的,这叫辛劳。任何一首诗都是这两者的混合物。当然,一旦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多么希望能多多地得到那些“天赋”的诗句呵。金斯堡最早是从写布莱克风格的韵诗开始的,正如亚历山大·蒲伯所说:
诗艺之精巧来自推敲而非偶然,
正如善舞者之步履轻盈。
如果你属于那种一出手就能写出最好的句子而不需要任何改动的诗人,愿上帝祝福你。我也会嫉妒的。当然,这种情形在几乎每个人身上甚至包括我也偶有发生,就像一把牌摸了四张A。但是作为对作家们的忠告,我的诗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是需要重写的,此话绝无虚言。灵感还不是一首真正的诗,但假如灵感真的来临,只要你肯下功夫,并且努力去创造一个相应的影像,灵感就一定能变成一首真正的诗。
4.往日的噪音:来自童年记忆的诗
这样的诗歌能够提供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记忆本身,记忆只因它们自己的缘故而存在。
——琳达·帕斯顿
1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如思的记忆》,文中论及我对自己童年时代的评价,以及作为一名作家它又是怎样影响我的。如今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篇文章,当初我写的有关童年的那些诗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早已不复存在,一种快乐的怀旧感已被一种更现实、至少是更忧伤失落的情绪替代。这使我非常震惊,就让我从最新的诗集中的一首诗开始谈谈吧。
一支者歌
我们的童年多么忠诚,
在同一间屋子里它陪着我们渐渐长大
就像仆人在内里
放一点辣,又像牢房的守卫
手中的钥匙悦耳清脆
锁住你或把你关在门外你也没法。
我的生活照旧
年华一天天累起
正如门外的积雪,
而小把戏依然将我们守望
从镜子的深处
隔着桌子就在一张张新面孔里
不管它用什么样的声音,
不管它说怎样的语言
问题总是一样。
他们问“为什么你总把事情
搞糟?”他们说
“再这样我们就不再爱你。”
正如A·S·比亚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她自己的时候所说的:“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几乎一无是处。”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就晓得躺在摇床里尖叫个不停,原因是我被环绕在阳光里的尘埃颗粒吓住了,仿佛它们是一大堆昆虫正准备一窝一窝地过来咬我。到了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脸总是抽搐个不停,牙医担心我日后停不下来,要求我做一些口腔练习,可是我太难受了,没法完成医生的要求。我一直非常害怕,生怕会像那些有着各种不能自控的坏习惯的孩子们一样,被二年级的教师领出教室送回家。幸亏后来我的脸终于不跳了,这一点也是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大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孤独的一年,我成了一个没有人愿意跟我玩的孩子,一个公认的替罪羊,而四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度过了更加孤独的一年.天哪,我居然成了被全校为难的一员。我睡觉的卧室在黑暗的大厅走廊的尽头,所以我的心灵长期被阴影笼罩着,直到一位好心的心理医生来访,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