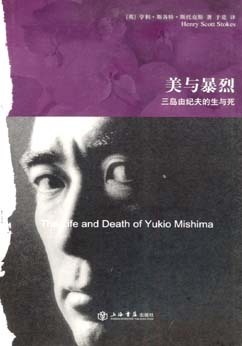吴钩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的轿子差不多已被淘汰,机动车又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城市都兴起一种新的代步工具——黄包车。今天在一些旅游景区,还有仿制的黄包车,供游客体验一把浪漫。而实际上,看过老舍小说《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当时黄包车夫的生活绝无浪漫可言,他们活在城市底层,地位卑贱,经济困顿,每日赚到的工钱通常不足以养家糊口。在1930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拉车的净收入月均不到9元,而每月的家庭支出需要16元,“竟日奔波,血汗所获,终难维持”。在1910年代的北京,黄包车夫的日收入约50至80枚铜元,而当时一户四口之家的生活费,每日要花费60枚铜元方可糊口。
民国的社会学者将国民生活水平划分为四个阶层:贫穷级,挣扎在温饱线以下;生存级,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舒适级,丰衣足食,有条件追求比较舒适的生活;奢侈级,过的就是“有钱,任性”的日子了。三十年代,伍锐麟通过对广州600名人力车夫生活景况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车夫的生活,可以说是介乎贫穷级与生存级之间。”
拉黄包车是苦力活,有体面的城里人都不会愿意从事这一行当。民国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人力车夫中鲜有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流入 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身无长技,基本上未受过像样的文化教育,除了出卖原始的体力,很难在城里找到职业门槛稍高一点的工作。极低的择业能力,使得他们只能从事拉黄包车之类的苦力,也使得他们在发现拉黄包车的效益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挺身出来抗争,包括发动车夫集体罢工,甚至采取铤而走险的激烈方式。
从民国黄包车夫抗争的对象来看,主要有两个,一是出租黄包的车行,一是比人力车先进的公共汽车与电力公交车。
黄包车夫由于收入低下,难有积蓄,多数人都无力自己购买黄包车,据民国社会学者言心哲的调查,南京1350 名人力车夫中,自备车者只有204 人,而且这些车多为旧车。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最大的人生理想便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但这个卑微的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当时很多车夫只能向车行租车。民国时期的城市,普遍都有黄包车行,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车行出资购置车辆,然后租给车夫,每月收取车租。那时候也有两班制的租车习惯:两人合租一车,一人拉早班,一人拉晚班。
黄包车行的出现,既给无力购车的车夫提供了拉车谋生的机会,同时也张开了吞食车夫血清钱的血盆大口:车夫往往要将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作为租金上缴车行。不过,那时候,车辆的保养、维修、牌照费都由车行负责,车行也不是暴利行业,据民国学者的调查,车行的实际得利一般仅为营业额的20%。而且,当时车行也没有搞垄断经营,只要车夫自己有钱购车,随时都可以单干。

但是,对于大多数只能靠向车行租车的车夫来说,占收入额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车租,确实构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所以,他们对车租极为敏感,车行若想增加租金,势必引发强烈反弹,如1926年,江苏无锡的42家人力车行决定增加车租,结果引起车夫罢工,愤怒的车夫还冲上街头,捣毁了车行的一百多辆黄包车,最后迫使无锡当局发出公告:“各车行应暂照现行价格收租,毋得骤增”。
如果说,黄包车夫要求车行不得擅增租金的诉求有其合理性,那么他们针对公交车竞争发起的抗议,多少就显得有些荒唐了。民国时期,当电车、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广泛引入中国城市之后,人力车行业就如今日在新媒体挑战下的平媒行业,开始进入消亡的倒计时。当时有一首竹枝词感叹黄包车夫的命运:“人力车夫六万名,沿街无处不居停。却因汽电来争胜,剥夺机穷一线生。”
为了生存,黄包车夫发起抗争,矛头对准新兴的汽电车公交业。1929年,北平的数千名车夫因为觉得“电车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人力车的客座,砸了许多人力车夫的‘饭碗’”,在一些政客的挑动下,砸了市内的有轨电车。1946年5月,汉口的公交车管理处开辟了从王家巷到三民路的短程路线,发车当天,有一个叫做孙昌清的黄包车夫跑到王家巷公共汽车站,挡在正要开动的汽车前,意思是,你们要发车,就从我身上辗过去吧。车站的车长出来与孙昌清理论,结果打了起来,“车夫用头一撞,把车长之门牙撞落一颗并撞歪一颗,车夫之头顶也被牙齿撞破一眼,彼此都流有血”。最后还是汉口的人力车业工会出面调解,公交车管理处同意取消新开辟的路线。黄包车夫胜利了,却是以城市公交车发展的延迟及市民出行的不便为代价。
试图以人力车阻挡汽电车滚滚而来的车轮,当然不足为训。但黄包车夫群体的命运,确实需要同情,车夫的困境,也需要有人关切。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机制,表现出了它的活力。
针对黄包车夫无力自购车的问题,当时的社会组织想到了成立合作社的办法:车夫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筹款购车,发给车夫使用,车夫每天缴纳车租抵偿车价,“俟车夫已偿回车价时,车便归该车夫所有”,以后就不必再纳租,每日拉车所得,悉归车夫自己。这一办法于1934年在南京开始实施,由江苏民众教育馆发起成立合作社,第一期筹集基金500元,征集社员40余人。社员可向合作社的信用部贷款购车,分210天还清借款后,车即归车夫所有。
针对车夫生活困顿的问题,上海公共租界率先在1934年创办了人力车夫互助会。互助会通过向社会募捐及向车夫收取会费的方式筹集资金,兴建学校、图书馆、诊疗所、洗浴室、饮茶室、寄宿舍等设施,免费向黄包车夫开放。这里,学校的意义尤其值得强调,因为车夫得到了教育与培训,提升了谋生的技能,以后不干拉车的苦力活了,另谋他职的机会会更大一些。互助会还向生活困苦的车夫提供发米、发钱、发衣服等救济,并为所有加入互助会的车夫提供团体保险、小额贷款与养老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成立后,社会反响良好,有一位市民还致信媒体,发出呼吁:“我们希望全国热心人士,参照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夫互助会的办法,在已经有人力车夫的城市,从事人力车夫生活的改善。”
针对黄包车夫处于社会弱势的问题,许多城市的黄包车夫都成立了自己的利益代言组织——人力车职业工会。当时黄包车行也有自己的利益代言组织——人力车租赁同业公会。职业工会与同业公会的出现,使劳资都有了利益表达、理性谈判的机制与平台,双方的分歧不致于轻易发展成激烈的冲突。比如1946年2月,武汉的人力车行违背与车夫订立的协定,单方面要求增加车租,车夫工会即跟车行交涉,最后经警察局调解,由人力车租赁同业公会掏出一大笔钱,代表车行向人力车夫赔偿。
今天看来,黄包车当然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行业。不过,当时社会为解决黄包车夫困境而创设的合作社、互助会、职业工会等组织机制,则可以为今天的社会治理创新与改革提供借鉴。任何社会都有可能产生种种问题,而健康的社会,则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