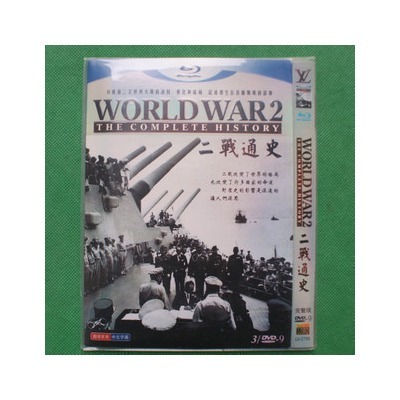1921年的中国
傅国涌
【按:此文应《中国经营报》之约而写,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九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年轻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旅行,足迹遍及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长沙、洛阳、汉口、九江、北京等地,一路走来,他不仅观光游玩,而且拜访各类名人,从前清遗老郑孝胥、文化怪人辜鸿铭、国学大师章太炎到倡导白话文的胡适、主张“青年中国”的李汉俊等人,这些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却在那个年头都生活得很从容,未来怎么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在与这些中国人的接触中,芥川龙之介有个体会,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必定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在游览江南一带期间,那股热情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减退。”
上海,章太炎在书房里挥动着留着长指甲的手对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很快成为共产党发起人的青年李汉俊告诉他: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国”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
他们的思路不同,对现实不满、求变的心态则是一致的。从以后的历史,我们看到,章太炎的预言没有言中,李汉俊预言的社会革命主导了未来的走向。自1919年以来,学生的政治热情被大大激发起来,学校里不仅思潮涌动,而且大大小小的学潮不断,学生被舆论视为“丘九”,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而受到注目。代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认为“五四”之后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
当时,因武昌女子师范学 校辞退倡导新文化的国文老师刘子通,陈碧兰和杨子烈等五个学生带头罢课而遭除名,她们不服,校方软硬兼施,湖北督军肖耀南甚至要逮捕她们,她们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团体和新闻界,控诉校长开除她们没有理由,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到各学校的学生会要求声援。武汉的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果女子师范学校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就举行总罢课。那时,各校都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全省学生联合会,加入总部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当局怕事情闹大,不敢轻易下手。陈碧兰她们则在女子师范发起罢课,以驱逐校长为目标,产生了罢课委员会,分宣传、组织、外交等部分,还组织了纠察队。她们到教育厅门前席地而坐,坐了一天一夜,包惠僧、陆沉等人带着水果、饼干、油条、豆浆等慰问她们。教育厅派人与她们谈判,她们的要求校长引咎辞职。接着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出来调解,她们坚持这个条件。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就是几个黄毛丫头逼得有权有势的校长毫无办法,只好辞职离开,而且在辞职书上写明“引咎辞职”四个字。断续将近一年的学潮,以校长下台告终。
北京更是学潮多发的中心地段,不光学生,教师也因为政府拖欠工资,一次次上街,向北洋政府请愿,这年6月3日北大等八校师生请愿时遭到军警殴打,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师生十几人受伤,被称为“六三惨劫”,当时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以《国务院军威下之教职员学生》、《教育界创痛中之呼号声》等为题,做了详细报道。一开始,北洋政府的态度还很强硬,到了7月12日,与政界、学界都有关系的一些名流范源濂、汪大燮、傅增湘等人出面调和,北洋政府派人慰问伤者,并正式向教职员学生代表道歉。
对当时发生的那些学潮只有作更细致、深入的了解,才能进行客观的评判。我想说的是,学生之所以动不动发起学潮,从一校、一地乃至全国的,是那个时代赋予了他们一定的空间和行动的勇气。从晚清到民国早期一脉相承,当时的主流媒体是不同背景的民间报纸,在上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有研究系背景的《时事新报》,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日报》,在北京,研究系背景的《晨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等,这些在影响很大的报纸都不是北洋政府所能操控的。北洋政府对媒体有打压,但是力度有限。新的报纸还在不断诞生,以陈布雷为主笔的《商报》年初在上海问世,老报人林白水与胡政之合办的《新社会报》3月1日于北京诞生,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那个时候,筹点钱就可以办报。陈公博回忆,他和谭平山等人到广东办了一份《群报》,只有维持三天的钱,所以他预言不出三天便要关门。后来得到另外的资助,继续办了下去。
史量才雄心勃勃,力图把《申报》办成世界性的报纸,他认为“独立之报纸乃人类幸福之所赖”。当年双十节前夕,记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哈定就给《申报》发来贺电:“《申报》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中国”。11月,英国报界的大老、《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访问《申报》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新闻,包括《申报》在内的报纸几乎都做了客观的报道,今天我们要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翻阅那个时代的《申报》、《晨报》等报纸是最直接的途径之一。
这一年,全国的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新闻界对北洋政府的那些旨在钳制言论的法律、法规极为痛恨。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给国务院发出这样一封信: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赫然以《不自由毋宁死》为题,其中声明:“民国三年袁世凯及民国八年安福部所新造的违背约法,侵犯人民自由之种种法令(如《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已经全国报界联合会决议,认为无效。并通知南北两政府,以后不得再用此等非法政令,侵犯人民约法上所许各种自由权利,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新闻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部分重要报纸几乎都参加其中,影响很大。这种庄严的宣告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代,拿枪的军阀还奈何不了这些拿笔的文人。青年学生受《新青年》、《新潮》的影响,自发创办的刊物至少在400种以上,遍及全国各地。有些刊物言论激烈,遭到查禁的事时有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1920年2月15日出版)发表《告军人》:
吾亲爱的军人呵!你们为了十数元的金钱,竟失了你们的天性,背了枪,拿了刀,只知道有命令、有长官,竟忘了你们的人格。我们不但不恨你们,实在可怜你们。……至于你们的官长呢,什么汽车呀,什么鱼肉海参呀,美妾呀,这种都是你我梦想不到的东西!到了打仗的时候,你们做枪炮下的鬼,你们的长官,还是快快乐乐的享他的幸福。
……还有一件事,我们替你们实在抱不平:像你们这样辛苦,这样忠厚,这样诚实,你们的长官还是当你们奴隶对待:你们若使稍不小心,他们总说你们违背长官命令,轻者拷打,重者伤命,丝毫亦不原谅的。咳!长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咳!我们可怜忠厚诚实的朋友们呵!你们精神这样不快乐;你们的生活这样不安全,为什么不大家连络起来,把你们长官的财产,均分一下呢?
这份北京发行的刊物,却是远在浙江的督军卢永祥首先发行,写信向北洋政府的内务部长举报,“此种谬妄之词,骇人听闻,似不可不防微杜渐,且军人知识简单,尤恐易为所动”。而内务部给国务院的公函只是说:“自应查禁,除分函教育部外,相应照录原件,函达贵部查照办理可也。”这样煽动军人起来反抗官长的文字,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查禁了事,没有大动干戈,抓人审判。观察那个时代时,不能不注意这样的案例。
不用说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梁启超代表的研究系,以及各有不同背景的军阀和其他政治势力。以中学生、师范生、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自发社团到处都是,湖南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原因而广为人知,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也在这一年破土而出,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这年7月在南京开了一次大会,23个的代表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在玄武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表决也比较含糊,实际上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这当中有些只是主张要研究主义。方东美说“今大会到会只二十三人,即大会表决要主义,亦不能算学会大家的意思。”在讨论是否应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最后讨论的结果是,直接加入现在政界者为狭义的政治活动,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为广义的政治活动。以“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付表决,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少年中国学会”是1918年发起的,完全是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结合,一直拖到1925年疾风暴雨的时代浪潮中才散伙,实在已经是一个奇迹,虽然裂痕早就出现。
三天半的南京大会是一个风向标,预示着一代“五四”青年将按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郑伯奇的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学会当中大约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直接从事于社会改造事业,以急进或缓进的革命来创造少年中国,一种是用间接的手段,通过教育学术等方面来创造少年中国。其实,最大的分歧不是来自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而是第一种趋向中不同的思想趋向,如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分野。当年9月20日,北大学生杨钟建给会员们写了一封信,“以后的少年中国学会,有主义也好,无主义也好,和衷共济、分工互助去创造少年中国也好,彼此分裂、分道扬镳去创造少年中国也好,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理想中的少年中国非以学术的基础不可的;到少年中国的路,非做路上应做的许多事情不可的;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大的事业,必须许多人来做,而这许多人非彼此十分了解不可的。”
这个学会的会员以大学生为主,一共有126人,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都是1890以后出生的,他们中既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的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周佛海(后加入国民党)、肖楚女、毛泽东等人,也有后来加入国民党的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等人,青年党的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中”会员。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那真是一个理想可以开花的年代,年轻人可以尽情地做梦的年代。
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年龄最大的周恩来也只有21岁。三十多年后,邓颖超接受历史学家王来棣的访问时回忆:
“觉悟社”没有头目制度,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式比较灵活、轻松。我们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阄代号。记得抓阄的那天,我们写了50个号码,放在盘子里,每人用筷子夹一个作为自己的代号,多余的是给后来入社的同志准备的。当时我们只有30来个人。我抓的是一号,恩来同志是五号。后来恩来同志曾用过“伍豪”,我用“逸号”作笔名。
刘清扬说自己抓到了二十五号,以后隐名时就叫“念五”。
我们看看这年元旦在湖南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熊瑾玎这些会员都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们在三天当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1、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2、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些问题都是是巴黎的会员蔡和森他们首先提出的,讨论结果是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方法问题讨论最久,其中十二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张),三人没有决定。着手的方法包括了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款及办夜校、书社、报纸、菜园等。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人数最多时达到70多人,最初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这些青年的思想转向,可以看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虽然也有分歧、有争论,但李汉俊对芥川龙之介所说的社会革命正在被部分青年所信奉,并转换成行动的力量。
1921年的中国还处于“五四”时代,年轻人办刊结社、意气风发,可以为了理想争得不可开交,可以尽情地设计美好社会的蓝图。在他们身后,联省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许多比他们年长的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军阀、地方精英都卷入其中。张东荪、章太炎、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等人都赞成联省自治,他们在《时事新报》、《改造》、《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陈独秀、康有为、张君劢等反对者在知识界明显是少数。赵恒惕在湖南首倡自治、制定省宪法,这年3月中旬聘请李剑农、蒋百里、王正廷等十三个专家名流在岳麓书院起草省宪法草案,4月20日完成,交给全省各县选出的审查委员会,当年9月9日通过审查,在12月11日举行的公民总投票中,以1800多万票对57万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个高潮。青年毛泽东1920年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等一系列评论,为湖南自治推波助澜。
浙江督军卢永祥6月4日发出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在此之前,部分在社会的浙江人1920年就成立了旅沪浙江自治协会,著名律师、杭县律师公会会长12月8日在浙江省议会提出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的建议。1921年2月1日,旅居上海的浙人张静庐等人创办了《新浙江》杂志,与《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新湖北》、《新安徽》等构成了一曲鼓吹省自治的合奏。5月22日,浙江各界一千多人召开浙江省宪法期成会,阮性存发言说,我们没有武力足以驱逐北洋军阀,“只可用布流血之革命,亦即自订省宪,自选省长”。军阀卢永祥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出来呼应的。“浙江省宪法期成会”、“省宪促进会”、“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纷纷成立,这个过程中,教育会、律师公会、商会、报界公会、工会、农会等团地体都曾参与。6月16日,在阮性存等人推动下,省议会组成了55人的浙江省宪起草委员会,7月23日举行浙江省宪法会议,选出阮性存为审议会委员长,9月9日通过浙江省宪法,号称“九九宪法”。
四川、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省都出现了自治和省宪的运动,联省自治浪潮波及北方,远到西北,年初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就发起了“甘人治甘“运动。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十三个省市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等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出现了,上海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在湖南省宪运动中,除了新闻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湖南改造促进会等30多个团体都积极参与,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军阀只是利用了这个旗帜。
正是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权威衰微,没有力量号令天下,联省自治运动的勃兴,给各种思潮、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那时,中国工商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兴的工厂、银行不断冒出。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看到,在大片桑田的对面,墙壁上涂者油漆的广告,“无敌牌牙粉、双婴儿香烟……这些牙粉、香烟的广告在沿途所经过的车站无处不见。”那正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度的转型期,工商界与知识界的思考几乎同步,张公权、聂云台、穆藕初这些银行家、实业家和蒋梦麟、胡适、蔡元培等“五四”知识分子都有相当的共识,他们在金融、工商业等方面的努力构成了那个多元时代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时代的急风暴雨打断,在那样的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健康力量主导历史的进程,一切都有可能朝着正常的方向变化。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