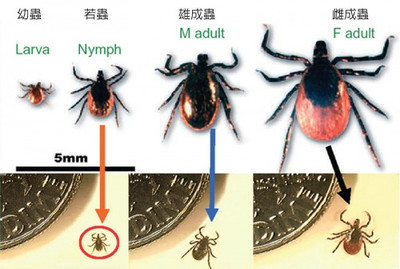放蜂人
梅寒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
乡间四、五月,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一树一树的槐花都咕噜噜开了。村庄便被笼在一片如雪似雾的花海里。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似一串串的玉制酒盅,每一盅里头都灌满琼浆,那香气,浓而不呛,无风自扬,在春日的晴空下,一路就飘向远方……
放蜂人该来了。每一年槐花盛开的时节,村子里的人就开始念叨,像念叨一位久别的故交。
某天早晨醒来,才走到村头老槐树底下,就发现树下多了一顶草绿色的帆布帐篷,一排溜排开的几十只蜂箱,上百只蜜蜂已嗡嗡嘤嘤地开始忙碌。蜂箱旁,头戴防蜂纱布罩子的男人在小心地割蜜,帐篷旁边,几块石头支起的炉子上,火舌正欢快地舔着黑色的锅底。女主人正弯腰往锅里下米……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没人知道。每一次都仿佛从天而降。
放蜂人的家,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那里是全村地势最平坦宽敞的地方,搭起一方帐篷,再摆下几十只蜂箱,还绰绰有余,离公路最近,车子可以开到树底下,公路外侧就是绕村而过的小河,取水也便捷。放蜂人说,他在外放蜂十几年了,年年最盼的就是到我们村上来。不光是因为村前村后那漫山遍野的槐花,更为村子里的人。放蜂人的峰箱,就摆在村头的公路边上,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他的蜜蜂却从不受扰,蜂箱里的蜜,从不少半两。
在小孩子的眼里,放蜂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快乐的人。一年到头,从南到北,哪里花开就到哪里去,他们与他们的蜜蜂一样,沐浴着清风明月,吃下的花蜜花香。试想,在这世间,谁还能像他们一样,追着花香奔路?
那些林间嗡嗡嘤嘤的蜜蜂却每每都把孩子们好奇的脚步远远地挡在离放蜂人的帐篷很远的地方,哪怕手上端着送给放蜂人的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或者大饼。
天南海北到处漂,不容易。村上的女人们并没有放过蜂,却似乎都深谙放蜂人的不易。放蜂,在她们的眼里,不似孩子眼里那般浪漫。家里蒸了热馒头,烙了热饼,总是会想到村头的放蜂人,会让家里的孩子送一份去给放峰人。放蜂人家里也有孩子,一大一小,小的还躺在帐篷里的床上,动不动就哇哇大哭。大的那个已经会帮妈妈烧火、去河里打水。
石头支起的小火炉旁,女孩儿的脸庞被火映得红红的,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等炉子上的水开……
很多个早晨,我们背着书包从放蜂人家那里经过,都会看到同样的场景。
我被妈妈遣去给放蜂人送过几次吃的。不敢靠前,也不知道该喊他们什么,远远地就站下了,用力朝着帐篷的方向喊:哎——给你们送的热包子——来拿吧……
每一次,都是那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小女孩儿第一个从帐篷里跑出来,随后出来的就是她的妈妈。母女二人接了食物过去,女儿羞怯怯地躲在妈妈身后,友好地冲我笑,妈妈却是对着我千恩万谢,然后让我站在那里等着。她转身回屋,不知何时装好的一酒瓶蜂蜜就拎出来了:这是纯正的槐花蜜,拿回去给你妈妈……谢谢你们啦,每次都想着我们……
我不要,但执拗不过她,只好接过来。
我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甜的蜂蜜,浓稠,晶亮,化都化不开,舔一点点在舌尖,甜透了,再细细地咂舌回味一下,有淡淡的槐花的清香润散在五脏六腑……那瓶蜂蜜,却给我妈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她说:这怎么好?我们不过送人家仨瓜俩枣儿的,倒要让他们这么破费……

家里再有稀罕的东西,妈妈还会去送。却不再让我去送。她自己去。装一个塑料袋里,趁放蜂人一家不注意,悄悄地挂在他们帐篷外面。
小孩子熟络得快,慢慢的,村里的小孩子都跟放蜂人的女儿混熟悉了。听她给我们讲放蜂经,成了我们放学之余最开心的事。哪里的蜜源好,什么地势上开出什么花,什么季节酿什么蜜,她都了如指掌。
你们放蜂人,是不是天天都可以吃到香甜的蜂蜜?这是馋嘴的孩子们最关心的事。
才不呢。哪舍得吃。不光我们不舍得吃。我们的蜜蜂也舍不得吃。它们要采满一囊蜜,得采上千朵花,要飞出去好远。有一些蜜蜂采满了蜜,在飞回来的路上就累死、饿死了,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它们采集的蜜……
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对那种黑黄相间的小生灵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也第一次对那个坐在灶前托着下巴烧火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情。我们坐在课堂上,眼睛、耳朵却都被朗朗的读书声堵住了。那个女孩儿,才是大地上的精灵,同那些飞舞在群山间的蜜蜂一样……
放蜂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庄,是数年之前的一个春天。那一年,他们没有赶上槐花花期。
他们来时,那漫山遍野的槐树,因其生长缓慢,因其极低的经济效益,已经被乡人砍掉,换成了成片的经济林。
春来,故乡依旧是漫山葱翠,却再没有槐花香如海,更没有飞舞在花间树下的成千上百只蜜蜂和住帐篷的放蜂人。
没有了槐花、蜜蜂和放蜂人的春天,一片寂寞。
已刊《百花园》2014年3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