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都很宿命,当然也很奔命,这些在语言中驰骋的疯狂者,随时可能挂在半道。论宿命,是因为诗人天生被命运胁迫,内心永无宁日;说奔命,是强调诗人一直在语言中流浪,千里单骑,万里绝尘,不舍昼夜。
其实我们都被顾城早期的童话色彩蒙骗了,去掉他童话的外衣,撕开他“自我戏剧化”掩饰的内心,就会发现他从小就成熟着一副硕大而诡谲的魂魄,这魂魄浩然到千山万水,精细到一草一木。
拿“童话诗人”说顾城、拿“雪人”说顾城、拿“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说顾城、拿“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说顾城,其实是说错了人。顾城诗歌语言的制高点,不在于早期他成为极左文艺思潮围剿朦胧诗的“靶子”,而在于他后期颠沛异国达到“零度语言”开悟性的释放。
在他最后几年的诗歌中,他近乎通灵地把“顾城”演绎成一座“空城”。是啊,钱钟书写多少围城,也围不住顾城这座空城。因为顾城无城,他的城都在府中,所以他走进了——语言的王府!
从1991年到1993年,这是顾城生命中最后的三年,这三年中他一共写了263首诗(1991年146首、1992年81首、1993年36首),这三年中,顾城在激流岛(新西兰奥克兰威克岛)上,向他迷途的生命做最后激流探险般的冲刺。其实这最后三年,顾城没完全封闭在激流岛上。他各种旅行——去柏林搞创作、去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去纽约和三藩市浪诗、去伦敦演讲、去塔希提岛拜访高更故居,甚至还抽空回北京待了六天。
解析顾城生命的结点和终止符,要从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首诗《回家》来寻找蛛丝马迹。这首诗作于1993年9月3日,写给杉的。杉,就是顾城结发之妻谢烨1988年在奥克兰妇女医院产下的男婴木耳。面对天真无邪的亲生骨肉,此时的木耳也许是他唯一的安慰,顾城在诗中除了表现出顽皮的父爱,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悲悯情怀——杉/我要对你说一句话/杉,我喜欢你/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再没有人听见。果然一月之后,咔嚓一斧了断。
顾城在他最后三年,写出了一首可以称为中国现代诗歌清澈而又艰巨文本的组诗——《城》。他在异国他乡玩命回忆打小生活在北京的各种据点,这五十二首构成的组诗《城》,绝对是顾城作为一个纯然流氓的清澈体悟。顾城就是一位内心高洁的文艺流氓,只不过被他的所谓“童话”过滤了很多。文人一动笔,直达流氓处,把流氓都提升得高贵到饱和。在灵魂深处,顾城隐藏于王朔之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灵魂的病态天才、语言的恐怖杀手!
在组诗《城》的序中,已看出顾城要与这个世界进行生命的结算——像我小时候,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把手伸得高高的找粉笔,这条走廊也会变成颐和园的长廊,而我的手一直伸着,不知是示威还是已经投降。这是我独自承担的事情。
这组诗中有一首骇人的诗篇《午门》——我一直在找那块石头/磨我的刀子/她太软/没法打散。所以,这把刀,没磨好,锋利度不够,后来顾城只好选择了斧头。顾城写的《新街口》更加令人叫绝——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这俨然是在新街口一带混的追风刺客,出手就是腰斩。谁都没想到吧?顾城诗中还有武侠,要知道他从来不看武侠,却语如剑芒。
在顾城后期诗中,能读出老大的创口,创口里沉淀着惨白的月光。鲜血,在创口中,泼面而来,你带着一身鲜红,傲然碎裂而去。
于是,在顾城辞世前的一首诗中,我们不寒而栗——你在等海水吗/海水和沙子/你知道最后碎了的不是海水/你在等消息吗/这消息/像一只鸟要飞起来。
整个世界在顾城的冷漠中茫然冻僵,语言只有在抽象中才能覆盖成为万象。
如果你想在语言中游走,请记住顾城写《紫竹院》中的一句诗——影 子碰我/影子说/你和别人在黑暗里吹笛子。
怎么样,夜里三点,我们下楼,让我拿影子碰碰你,敢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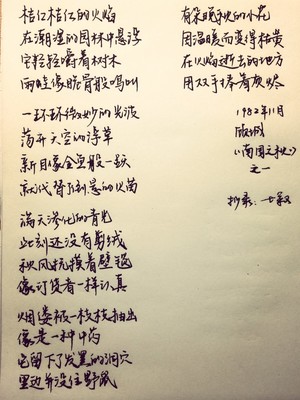
我们和顾城的鬼魂一起进城遛达一下如何?鬼进到城里,坦坦而行,还有何顾虑——一路灯影朦朦/鬼不说话/一路吹风/站上写/吃草/脸发青/一阵风吹得雾气翻滚……
(绘画:老兰)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