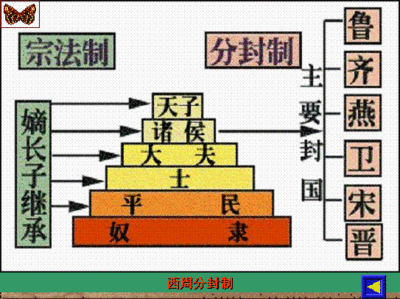第四十九章严管队
严管队就在十三监区,专门看管扰乱监规纪律和抗拒改造的犯人,在监狱里违规严重的犯人都会被送到这里。
严管犯由几个班长看管,严管期间会被停止接见,收发信件,购物和减刑等一切权利,每天早上随新犯一起到外面大球场训练,但是训练内容不一样,新犯的内容是军事化训练,包括三大步伐和报告规范,而严管犯的内容则是地狱式折磨,完全称得上是体罚,晚上回到监区后,老犯看电视,严管犯就在球场后面面壁,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严管期结束。
之前我刚入监的时候,见到过严管犯,其中就包括那个在狱内贩卖白粉的老油子,但也只是白天在球场上看到他们训练,其他的就不得而知。
龙跃说起严管队的时候,先是皱着眉头,然后半天不吭声。
我推推他,问:“怎么了?你说啊?”
“李杨,你有没有吃过大便?”龙跃突然冒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操,说啥呢?我可没吃过,我又不是狗,只有狗才会吃屎。”
龙跃摇摇头,说“不是只有狗才吃屎,人也一样会吃。”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一头雾水。
“如果不是钟浩,我就差点被弄去吃屎了。”
“啥?”我张着个大嘴半天合不拢。
龙跃望着我,缓缓给我说了他在严管队的经历:
在禁闭室禁闭以后,龙跃又被送回了十三区,关进了严管队。
那时严管队值班的有四个班长,分别叫老刁,贾勇,温德才,戴四捅子。
那天龙跃被送到严管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开饭时间,犯人们正在开饭。
严管队当时关着五个犯人,三个是参与卖白粉的,一个是个老头子,在监区私藏了一块刀片,还有一个就是打架的龙跃。
吃完饭,五个人被老刁和戴四捅子带回了仓号。
老刁和戴四捅子的外号据说都是根据他们的特点而取的。
老刁是十三区所有新犯公认的最难相处的班长,此人心计颇深,而且性情古怪,对待事情的态度和之前八区的杀手誊有得一比,不同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管教一个是犯人。

老刁最著名的案例是:曾经因为一个新犯在他讲话的时候忍不住放了个响屁而将新犯的门牙打掉了一颗,该新犯才十九岁,涉世未深,被打掉门牙后还得哭着给老刁赔不是,之后给老刁足足洗了一个月的衣服直到被分下监区。
而戴四捅子的外号则是来自于他的案情:他入狱被定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犯案时,喝得摇摇晃晃的他在打斗中将对方按在桌子上连捅了四刀,这四刀不仅换来了七年的刑期,还换来了一个新外号。
“冲凉,从小到大,一个个去。”老刁一回到仓号就给五个严管犯下达命令。
龙跃最先去,因为他的年龄最小。
冲完以后依次是那三个卖白粉的老犯,最后是那个老头子。
老头子刚冲到一半的时候,老刁说时间到了,让他赶紧把衣服穿上,老头子胆子小,性格懦弱,哆哆嗦嗦连身上的水都没擦就把裤头套上,穿裤子的时候一脚直立,摇摇晃晃站不稳,龙跃本能的扶了他一下。
就这么扶一下,把爱找刺的老刁给得罪了。
“谁他妈让你扶他的?”老刁瞪着眼,问:“你学雷峰还是他是你爹啊?”
龙跃皱着眉头,问:“你怎么这么说话?他年纪大一点,我扶他一下有什么不对的。”
“我让你扶了吗?啊?你报告了吗?啊?你他妈还是个严管犯,知道什么叫严管犯吗?”
老刁边说着一脚就把龙跃蹬翻在地。
在严管班长眼里,犯人本就是没有尊严的,而严管犯更是连人都算不上,想打想骂对他们来说太正常不过了。
可是,他不了解龙跃,龙跃是个炮筒子,根本没有情绪自控这些意识。
那一脚把龙跃蹬在地上站不起来,刚好戴四捅子在隔壁抽完烟回来,看到这一幕后又火上浇油的在龙跃头上补了一脚,之后一脚踏在他脸上,说:“你个小逼是不是还没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严管队,你他妈犯了监规是过来严管的,放个屁都得报告,知道不?”
戴四捅子说完后居然一口痰吐在龙跃脸上。之后转身走了出去,想去隔壁仓继续晃荡晃荡。
戴四捅子刚转过身,已经怒火中烧的龙跃一跃而起,按住他的头往前猛力一推就往墙上撞去,口里大骂着:“操你奶奶……”
戴四捅子当时离墙大概一米远,龙跃推他的时候,他出于本能双手一撑抵住了墙,虽然如此,额头还是重重的磕在了墙上。
老刁看到龙跃居然敢反抗,先是一愣,接着一拳就打在龙语的耳门上,戴四捅子顾不得疼,转身又给龙跃补上一脚,紧接着两人乱拳乱腿就往龙跃身上招呼。
“你他妈的敢打我?”戴四捅子顺手抓了个内务盖在龙跃身上,紧接着隔着内务乱踢乱踩。
老刁则是双手紧紧抓着内务,死死盖着拼命反抗的龙跃。
如果是换着别人,可能会大声呼救,可是龙跃不喊,他习惯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无奈双拳难敌四腿,这场斗殴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空有一身力气,但是实战经验跟这两个既当过兵又混过社会的班长根本没法比,除了挨打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换成是好勇斗狠且经验丰富的覃有国,这场架估计还有得一拼,但是他不是覃有国。
十分钟后,两个班长骂骂咧咧停手了。
戴四捅子扔下一句话:“小逼,你等着,这里是严管队,老子是班长,会叫你以后生不如死。”
那是龙跃进严管队的第一天,被打得直不起腰,全身上下都破皮肿了,唯有脸上干净点。
脸上干净是因为两个班长没打脸,不能在他脸上留下伤痕,以免被管教看到后生疑。
进过号子的人都知道,里面就是这样,打人都讲技巧,用枕头垫着打,用衣服包着打,即使打到你吐血,但也只是内伤,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当时觉得没事儿,直到多年以后内伤发作才知道当初被伤得有多重。
整场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其他四个严管犯至始至终没出声,三个卖白粉的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多年,都是人精中的极品,深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理论,他们还巴不得这种闹剧天天发生,让双方鹬蚌相争。
至于那个老头,也许心里对龙跃是感激的,但是天性的懦弱让他面对斗殴只能噤若寒蝉,甚至在之后为了自保,还更加刻意的和龙跃拉开了距离。
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枪打出头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戴四捅子撂下的那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第二天龙跃刚吃过晚饭就被老刁以打扫卫生为由叫进了厕所。
十三区的老犯开饭在饭堂,新犯开饭在球场,如果太阳大或者遇到下雨,就在二楼的活动室开饭,开完饭后班长们会安排新犯把地面清理干净。
严管犯一般不负责二楼卫生,但是这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还是要看班长安排。
所以,老刁发话后,龙跃信以为真,跟着他进了活动室的厕所。
但是,进去后龙跃就知道自己麻烦了:严管队另外三个班长都在里面,一看就知道是在等他。
实心眼的龙跃依然执拗,进去明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结果,可是他就是不跑,仍然直直的站在那里,甚至,瞪着四个班长。
“咦,这王八蛋不是以前和浩哥对着干的那杂种吗?”贾勇昨天没带班,今天才看到龙跃,不免有些意外。
“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龙跃临危不惧,指着贾勇的鼻子骂道。
“我…操!”温德才瞪大了眼睛,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严管犯居然有这么蹿,他还从来没见过有严管犯敢骂班长的。
“勇子,怎么样?看到了吧,这小逼就有这么嚣张。”戴四捅子点上一根烟,淡淡的说道。
“好,你够种,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贾勇一边说一边掏出几副棉套子扔给其他三个班长。
这套子是用棉花加烂布缝的,里面是厚厚的棉花,棉花外层是碎石子,外面包着烂布,像是一个简易的拳击手套,不同点是里面装了石子儿。
龙跃下意识的往后退了退,还没退两步,班长们就扑了上来……
整个过程过于血腥,所以不过多描述,龙跃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被揍得当时就趴在地上吐血,后来我曾带他去做了一次透视,胸部有一片阴影,估计是凝结在里面的淤血。
但是这并没有完,满嘴是血的龙跃还没喘过气儿,又被贾勇扯着衣领拖到便坑旁。
“妈的,老子今天非得让你舒服了不可,你给老子尝尝屎是什么味道……”
贾勇把龙跃的头往便坑里按。
便坑里有一堆大便,不知道是谁上完厕所没冲还是几个班长特意给他准备的。
“你们先伺候着这杂种,我去叫浩哥过来,给他解解气。”温德才打开厕所门走了出去。
“行,把浩哥叫来,看看他还有什么交代。”老刁接话道。
龙跃双手死死撑着便坑的两端,可是戴四捅子又一脚踩在他头上。
他的头离那堆大便近在咫尺,就在这个时候,厕所门‘咣’的一声被推开了。
钟浩心急火燎的跑了进来,喊道:“人在哪里?”
贾勇望着钟浩,说:“浩哥,你来得正好,这小子你看怎么收拾好?”
“勇子,赶紧放手。”
贾勇愣住了,说:“放手?”
“赶紧啊,我操!”
贾勇松开了手,戴四捅子也把脚放下来,两人望着钟浩,不明所以。
“浩哥,啥意思?”老刁也是一头雾水。
“行了,把他放了,这事儿就这样算了,这人是我兄弟。”钟浩一边说一边给四个班长派烟。
“啥?你……兄弟?”
四个班长都傻了。
“浩哥,你没搞错吧,不是听说这小逼上次还和你闹事儿吗?怎么又说是你兄弟啊?”戴四捅子问。
“唉,那是误会,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反正你们记着,这是我兄弟,以后别为难他,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给我个面子。”
四个班长面面相觑。
钟浩的出现让龙跃免了这顿没受完的皮肉之苦,如果再晚点,可能他那天就得跟狗一样趴在这堆大便上。
有了大组长打招呼,四个班长再也没为难龙跃,工于心计的老刁甚至还格外照顾起他来,偶尔会跟他聊聊,想打探一下他和钟浩的关系。
不过,龙跃也不知道为何钟浩会帮他,直到一个礼拜后钟浩去找他,他才知道是受了我和覃有国的嘱咐。
“钟浩还算讲义气,要不是他,你还真的麻烦了。”我感慨着说。
“是的,后来钟浩时不时会过来看看,几个班长也没为难我。”龙跃点点头,接着咬紧牙,说:“不过,我会记着他们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了,覃有国呢?现在在哪个监区?”龙跃问道。
“他在十一监区,做衣服,我上次还让他们监区的犯医给他带信来着。”
“哦,他还好吧?”
“还行。”
我望望墙上的挂钟,已经五点了,于是说道:“马上天亮了,你先下去,明天我会给值主班的交代一下,你先在下面呆两天,我到时去给医生打报告,给你开出院通知。”
“恩。”龙跃站起身就准备出去,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说:“李杨,给我几张纸和笔,我要写点东西。”
“哦。”我拉开抽屉,一边拿一边问:“你要写啥?”
“我想给晓玲写封信,最后一封信。”
我停住了,问:“兄弟,你觉得事到如今,还有这个必要吗?”
“李杨,你体会不到我心里的感受,你就别劝了,给我吧,我只想最后给她写封信。”
“唉!”
我叹了口气,把纸和笔给他,然后送他下楼,关上了铁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