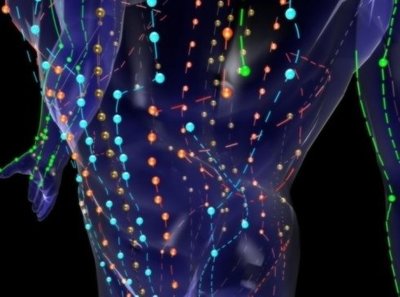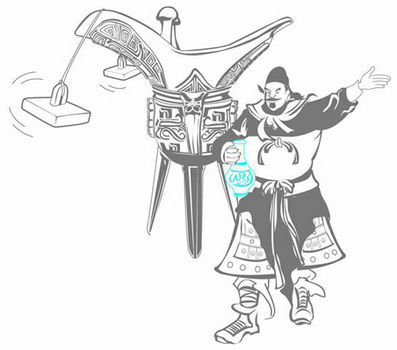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明朝丁忧的制度,官员在遇到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
张居正照例上疏请回原籍守制。万历不允,张居正又多次上疏,皇上依然还是不允。
大臣们都是看皇上的眼色,于是众多官员上疏请留张居正,可偏偏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却上疏请令夺丧。
吴中行说: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赵用贤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紧接着,他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和刑部主事沈思孝也请令守制,他们说:
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当然,皇上要求张居正夺情的旨意已经非常明确。因此,反对夺情的人必然受到惩处,吴中行和赵用贤各杖六十,艾穆和沈思孝各杖八十。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等人都来找张居正求情,可张居正只是说圣怒太严重,求不得了。王锡爵再求,张居正无奈之至,甚至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可见张居正也为夺情之事的矛盾而痛苦万分。
由于张居正不肯营救,朱东润先生以此认为“张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
我想,第一,张居正是否应该夺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按照常理,张居正要马上回家守孝三年。但是,当时张居正主持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且已初显成效。国家安定,经济复苏。但是改革并未完成,张居正有着更大的手笔,治理河漕、清丈土地等等。因此,张居正不能离开。如果此时丁忧,改革大计无人主持,辛苦几年的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再加上朝政风云变幻,反对者们很可能在他丁忧期间罗织罪名,对他反攻倒算。不但改革不成,甚至三年后能否起复都成为疑问。如果夺情,会引发“不孝”的骂名,这对于身为首辅的名声也是极重的打击。但是,如果夺情能够得到皇上的支持,那么一切都可以顶住,改革的事业也可继续进行下去。因此,综合考虑,应当夺情。

第二,吴中行等四人上疏是对还是错。一开始,我觉得是错。我感觉这些士人太迂腐了。回家守孝固然重要,但国家大事岂不是更重要?忠孝不能两全,怎能舍国家而就小家?
可转念一想,“国事重于家事”的思想只是现在的价值观,我不能以现在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人。当时这些士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孝治天下”的礼制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他们坚信儒家思想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一旦有人违背,即使是自己的座主,也要奋起反抗,坚决说不。这是极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源于内心的坚定和信念。这不能说是迂腐,甚至可以认为是正义和高尚的行为。
如今我感觉他们迂腐,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处在明朝,没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没有当时当地的束缚和牵绊。因此,我可以看到张居正在改革中的重要性。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改革本来就阻力重重。如果改革者离开,则必然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因此张居正断然不能走。而这些认识不过是旁观者清罢了。试想如果我也身处当时,我也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或许当时我也会反对夺情,很可能也会落入“我执”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我理解了吴中行等四人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不希望自己的座主落下“不孝”的罪名。
第三,张居正是否心胸狭窄?我认为不是。古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张居正万万想不到自己的门生和同乡上疏骂他不孝,这就不得不让他愕然与痛心了!难怪他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这是发自肺腑的痛苦感叹,无奈、愤激,甚至是委屈,尽在其中。这个时候还要求张居正能够宽宏大量,为免难人所难。以此说张居正气量不够宽宏似乎过于苛责了。
通过夺情,更显张居正的伟大.他能顶住如此重重压力,不畏人言,坚持推行改革新政,使得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在万历初年恢复了生机。张居正不愧是明朝最杰出的首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