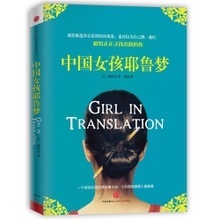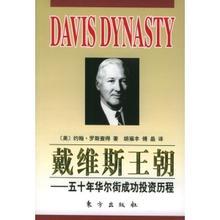读《管惟炎回忆录》
2008年7月4日,第一批大陆游客踏上宝岛台湾。这使人们想起5年前客死台湾的物理学家、政治活动家管惟炎先生。
管先生可以算是载入历史的人物了,据说海外还成立了他的基金会。就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任上几年,可谓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之上,后又在“事件”之后际会风云,折腾了几年,最后落在台湾。如果光凭他物理学家的身份,恐怕世界上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好在管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卷回忆录,生动地记录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中的经历,也描绘了这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风雨,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洛杉矶逸事
我和管先生只能说是同事,不能算朋友。我和他最密切的交往是1982年,他到洛杉矶出席国际超导大会。他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却得不到院里的支持,勉强凑了路费,到我的住处投宿。当时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人,都是两人住一房间。每人的床就是两个床垫子叠在一起。如果来了人,将一个垫子拉下来,主客各睡一个,所以安排住宿非常简单。管先生还随身携带了他夫人给准备的几瓶小菜。我说你难道是来“拉练”的吗,饭食我们还是能管的。
这样我和管先生抵足而眠,谈了谈所里情况。我问他所长是否有权,他似乎不很想谈这话题,但谈到他早年在哈工大教政治课事。他还说,他知道有一位在美的华人叫管惟原。这次来美想和这位名字相近的人见面。
管先生刚走,我们宿舍又来客人,是院外事局某副局长率领的外事局人员来美“考察”,安排两人在我们宿舍住。他们照例召集我们这些在洛杉矶的院内人员开座谈会。在会上我不想听那些官话,忍不住提出管先生来开会的问题。我说,管先生身为有成就的科学家、所长、国际会议主席团成员,院里居然不支持他来开会,而你们外事局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来此,要花多少外汇?副局长没想到我会和他叫板,仓促应战,说院里没给管惟炎支持,他就根本不应该来。会议不欢而散。在1980年代,派到国外这些人,对使领馆人员和国内去的官员还是很尊敬的,至少表面如此,这样的炮轰事件很少发生,叫他们淬不及防,当然后来我反思,可能说过了一点,特别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住在我宿舍的两位外事局朋友,都不在我处吃饭了,也许对我很痛恨,也许怕惹事,虽然我已为他们做了物质准备。
我为管先生“拔闯”(天津话,打抱不平的意思)事,可能他到死也不知道。
现在说管的回忆录。这书内容丰富,跨越年代长远(从抗日战争到新世纪)。我当然没能力予以全面评价。我只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
中苏社会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原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是按照苏共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建国初期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斯大林体制类型的,如单位制、党委制。但是从管的回忆录,我仍可看出,至少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两国有相当大的区别。
管先生说“苏联跟中国的特点,非常鲜明的不同是,没有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如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及后来批判斯大林,都没发动群众,没停产专搞运动。在研究所大学里也没有强调政治挂帅,还是专家说了算。党委书记的权没那么大,莫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没有办公室。在工厂里是厂长说了算,党委起监督作用。
之所以如此,管先生分析,是历史造成的。中国革命是农民起义,党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委员作用特别大。苏联革命是政变,红军使用了大批原来的军官,对专家还是尊重的。正因为如此,苏联30年代政治上镇压反对派,中央委员杀了80%以上,大批不同政见者或无辜者发配古拉格,但30年代正是苏联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涌现了朗道、卡皮察、福里德曼这样一批大师。
反右运动
因当时在苏联,管先生未参加反右运动。他很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在,肯定要拥护反右运动的,但也可能被打成右派。其实这两者差别不大,很多人刚批判完右派,自己就被打为右派。
书中对我院被打成右派的项志遴先生(1931-2001)的叙述不正确,也许是记录者的责任,将名字误为项子麟。项先生当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而不是在物理所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留苏反苏”,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还专门讨论过“项志遴的道路”。他落难后下放到二机部的工厂劳动,而不是下放农村。
项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离子体专业的创建者、我国核聚变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和俞昌旋教授编纂的《高温等离子体诊断技术》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至今仍是这一领域重要参考书之一。
正如管先生所说,项先生在右派“改正”后,由于心情过于激动中风,直至去世,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令人遗憾。
项先生是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胡绳的胞弟。但是据说他们兄弟的政见不尽相同。
学术秘书室
文革前,中科院物理所设有学术秘书室,作为所领导的学术咨询机构。但其实际权力很大,为所领导业务上依靠的对象。原因就是其成员均为从苏联学成回国的党员学术骨干,有管惟炎、郝柏林、孟献振、陈春先等人。
这种情况在中科院的研究所里不多。像地学、生物学部的一些所,基本上还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家在掌权。而在基础科学和技术性的研究所里,则情况各异,视人员具体组成而定。
这样一批青年科学家类似清华大学蒋南翔培养的“双肩挑”干部,但业务方面更强一些,已经起了研究骨干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一辈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科研路线”,而像物理所的学术秘书室的一批人,也好不了多少,被谥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但既然老科学家不掌权,所受的批判也就少一些。但均受到一些冲击,特别是孟献振先生。他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竟以身殉,令人扼腕。
臧否人物
在回忆录中臧否人物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管先生气量较窄,往往拘泥于过去的一些个人恩怨,甚至睚眦必报,难于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物理所文革前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成美(梅),开滦煤矿工人出身、抗日英雄节振国的战友,在游击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让他当物理所的领导应是勉其为难,文革开始不久后就被打倒。但在几年的揭发批判中,没看见揭发出他有什么劣迹。我认为这就很不容易,现在的很多领导恐怕做不到。至于管惟炎所津津乐道的关于张成美的轶事,并不可靠,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能做文革大字报的材料。而管惟炎说他因为得罪了张成美而受到歧视和迫害,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管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对其他许多有关人员进行了指责和诋毁,大多数是站不住脚的。
陈春先问题
在物理所的人物中,管先生最痛恨的就是陈春先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据说起源于学术秘书室时代。其中的隐情,我辈并不知晓,但我想也没什么大的原则问题。
他们之间的冲突集中爆发于1980年陈春先要“走出去”开公司,直至后来成为“中关村第一人”。对此,管先生是坚决反对的,官司一直打到报纸上,直到中央首长批示,肯定了陈春先的方向,舆论上才认为陈春先对。但是群众舆论对陈并不很有利。管去世后,又有些对管的同情,一般来说,这事就摆平了。
陈春先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管先生,就不能那么说。管有相当功利主义的倾向。但这不是褒贬,理想主义未必都好,功利主义也未必不好。陈“走出去”办公司,应该是个方向,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开公司的模式,都是“星期六工程师”的方式,即不离职,工资照拿,而用所谓业余时间去开。但是绝对的业余时间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脚踏两只船的形势,公司开砸了有个退路。还有的院办公司是拿公家的钱去开的,更不合理。当然在当时人浮于事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分流人员有一定合理性,但终究会造成对正常业务工作的冲击。很多群众对此反感,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打着“技术推广”的旗帜,但实际上必然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否则就不叫公司了。所以大家称之为“骗子一条街”。这个问题直到1984年才完全解决。当时院里叫这些办公司的人完全退出科学院。
管惟炎身为所长,有维持正常科研秩序的责任。但是他处理此事仍不能脱离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成立了专案组审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后来不了了之。他还在全所大会上批评陈未经批准,在自己家里接待外国人的作法。在已经改革开放的当时,这样做显然太过时了。所以管对于扩大矛盾是有一定责任的。
等离子体研究方向问题

可能是对陈春先有意见,管先生竭力诋毁物理所的等离子体研究方向。研究方向是个学术问题,本来可以讨论。但管先生有一点不好,就是歪曲事实,把等离子体研究方向的建立说成是陈春先弄出来的。
陈在文革前搞有机半导体、大能量激光,文革开始的时候,所里叫他负责筹建的技术物理中心的等离子体部。这是1964年院里筹划长远规划后的决策,绝对不是陈个人所能决定的。至于物理所搞热核聚变,是施汝为所长到二机部去与钱三强协商的结果。所以物理所的等离子体方向是先决定,陈春先后涉入。我们在1966年7月份曾听当时的计划科长游俊明的有关传达,有当时纪录为证。这一点(科学院和二机部两家搞)也是1966年5月份第三届全国电工会议做出的建议,后来周恩来总理也肯定了这一布局。管先生身为领导,对以上事实应很清楚,却罔顾事实,肆意歪曲。
有机半导体
管先生提到陈春先另一罪状是有机半导体问题,在文革中也因为此事遭到批判。这确是一桩糗事,因为无任何结果。不能说承担这一课题的陈春先没有责任。但是不为人知的是,这个任务是周总理下达的,其根据是报纸上登载苏联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消息(根据李德仲生前讲话)。在那个年月,由中央首长亲自下达科研任务并不罕见,如果成功了就赞扬首长的英明伟大,如果失败了就不吭声,没人知道。
那时候,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对上面下达的任务都非常重视,组织攻关。这种组织形式有点类似现在体育界的举国体制,有其优越性,特别是对于大工程,如两弹一星,但对于基础研究如有机半导体不适合。
当然有机半导体研究也非无任何结果。他们把研究结果写成一篇文章,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但是同一期学报中有另一篇文章后来被撤回,连累这一期学报也撤回了,至今无处寻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