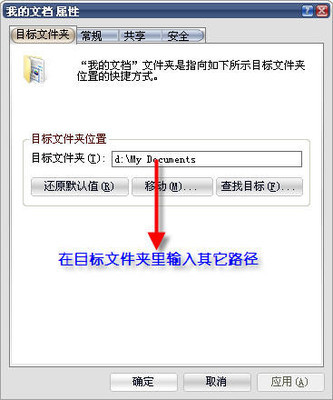张君遇到文强
周末的一个下午,一个晴天。
从重庆主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朝天门顺水东下,地处两百里路程长江左岸的丰都鬼城,非常清晰,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高高矮矮的房屋,街道,桥梁,村落,一切都罩在明亮的阳光里。西边鬼头山上,时常缠绕着的雾散去了,露出起伏的山脊和山顶上的树。时令已入深秋,很难遇到这样的太阳天。气温正在一天天变凉,多数树丫上,光秃秃的,吊着几片黄叶,干瘦的枝杆伸向四方,没有风,凝然不动,一些四季不落叶的植物,叶子上像蒙了一层灰土,泛着朦朦的暗绿色。
这季节天冷,来鬼城游玩的人不多了,虽是出太阳的天,仍没有多大暖意,人们已换上冬装,围着围巾,有的还戴着线手套,三三两两在鬼街上走。街虽然不宽,但是游人少,一条街上,空荡如许,路边那些卖祭品,纪念品的摊前,少了许多平时的嘈杂和闹热。一些年轻摊主,凑在一起打牌下棋,扯开嗓子大声地喊着叫着,声音传出老远,给这条冷清的街,增添了一点生气,年纪大一点的,端着张长椅架在自家摊前,懒懒地躺着,有的拿条毛巾搭住脸睡觉,有的拿着张过时的报纸翻看,打发时间,偶尔来一点风,摊上的纸人纸马纸房子便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
张君一个人,在奈河桥边闲逛,走了一大圈,他走渴了,甩掉手里快烧着手指的半截烟头,走进旁边一家叫来来的小超市,买了瓶“农夫山泉”矿泉水,一边喝一边从店里出来,刚走到门口的一棵杨槐树下,隔十几步远,他看到一个人,这让他惊奇不已,那人走路的神态和肥头大耳的样子极像当年重庆公安局的副局长后来是司法局局长的文强。
张君开始有些不相信,以为看错了人,忙揉揉眼,在远处盯着那人看,看了好一会,还是拿不太准,但确实又像,他绕过树子从侧边走近点看,果然是他,没有错,真是在阳间呼风唤雨,鼎鼎大名的文强,他上前去,走到那人面前,问道:“你,你不是文强,文二哥吗,你怎么在这里?”
文强听见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张君,眯着眼上下扫他一遍,先是一愣,随即不自然地苦笑笑,表情现出些尴尬,想打招呼,嘴张开半边没出声,不晓得怎样称呼。喊张哥吧,似觉不妥,他比张君大,不好喊,而且有失身份,喊张老弟吧,怕张君不领情给他来个猫洗脸。张君他太熟悉了,那年张君就是他带着十几个警察在渝中区枣子岚垭抓的,记得当时抓住时,文强气狠狠上来给了张君两脚,还把手上的一个值三千多块钱的三亚手机砸在张君的头上,口里咬着牙骂道,张君,你服不服。那时张君跪在一个巷子里的水凼边,被六个虎背熊腰的警察按在地上,衣服裤子上全是黑泥巴,头发凌乱如一团鸡窝,眼圈青黑,右眼上方裂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边上翻开一小块肉,血糊了整个脸,想那时,我文二哥是何等威风。
张君体谅文强此时的心境,呡了呡嘴,也不去计较,大度地对文强笑着说:“二哥,你还认识我吧,我就是当年在七星岗抢重庆上海一百的张君呀,咱们可是老相识,老对手了,过去的事咱就算了,你别老去想它,想它作甚,当时你也是身不由己,没得法,端哪个的碗,服哪个的管嘛,现在啥子都不要说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哥们,就是兄弟了。”
听张君这么一说,文强悬着的心才放下一些,想起往日,可又实在心有不甘,胸口堵得慌,气像出不来,跺跺脚说:“唉唉唉,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提当年勇了,而今我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虎落平阳受犬欺,受犬欺啊,哪个都可以踩你一脚。”
说后,对着天啊啊的连叹几声。
张君把话听岔了,以为文强这话是朝他说的,脸骤然阴下来,像板结的土,青中带黑的说:“二哥,你说这话就点都没得名堂了,我可是从来没有欺负你,我想都没有那样想过,你那阵黑起屁眼打我,骂我,吐我满脸的口水,还向我脑壳上砸手机,我都没有怎样你,说一句话,不记你的仇,现在你怎么啦,怎么倒说我欺负你了?”
文强见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引起了张君误会,忙陪着笑说:“哪里哪里,我不是说你,我说的是那些审我的抓我的人,想我文二哥当初有权有势时,一天围着老子屁股后头转圈圈,生怕哪点服侍不周,引起老子不快,那些格老子铁哥铁姐们,而今我算是看穿了,看透了,太他妈的混蛋,不够意思,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心黑,一个比一个滑,和老子斗心眼斗法,在老子搞女人拿钱的时候,还录他妈的像,录他妈的音,看老子今天栽了,一个二个跳出来把老子的事弄了个底底朝天,卖乖充英雄当好汉,把老子朝死里头整,弄得老子如今这个下场。”
文强一口一个“老子”,一口一个“他妈的”,牙齿咬得咯吧吧响,含血喷天,历数哥们姐们的可恶,奸诈,朋友的不可靠。
见文强这样,张君不好再说什么,过去按了按文强的背。
搞清楚文强才处了极刑,刚从阳间来,是来阴间登记上户的,张君拍拍他的肩,领他过了桥,来到一座房子跟前。
房子在桥下,单独一间四方的平瓦房,坐东朝西,前面临河,后是一面斜坡上有石梯连到桥上,房子的墙壁,屋顶的瓦,门,连门前五六级石头砌的台阶,清一的黑色,房子没有窗户,有个刚容一个人进去的门。
张君指着头上的桥告诉文强,那叫奈何桥,这条河叫奈河,东边那头是阳间,西边这头是阴间,这座桥隔着阴阳二界,又叫阴阳桥,死了的人,都要来这里过桥,才能从阳间来到阴间,过了桥,先在这里的接待室办手续,然后安排去处。
文强探头朝屋里看,里面不大,面积不过二十平米,心下想,这地方也太寒碜了点,还没有我在南坪住房厕所的一半大,但看周围,屋里屋外,收拾得倒挺干净。
进门靠右一张桌子,一张木沙发摆在桌子的对面靠墙,沙发前放了张长条形的茶几,七八个黑色塑料方凳,重叠一起放在沙发的右端头,里面东西也全是黑的,桌后的墙面上,一个综艺体的大白“静”字,占了墙的约三分之一,十分醒目,旁边贴着张黑底白字的“阴间须知”的条文。
一个咪咪眼,头顶半秃的中年男人,趴在桌子上正打瞌睡,见有人进屋,懒懒地从桌后站起身,打了一个长哈欠,两手支在腰上,向文强问道:“来啦,叫什么名字?”
文强正要答话,声音还没有出来,那人似被蛇突然咬了一口,原地一跳,惊叫一声,指着他叫起来:“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认得你,认得你,你是文强,就是那个在人间搞得鸡飞狗跳,残害百姓,被砍了脑壳的文强。”
文强的脸要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不敢看他看着桌面,暗自吃惊,真他妈的怪了,我的事咋传得这样快,连阴间都知道了,真是应了民间传的那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他低着头说:“是,是是,是我。”
文强发现舌头僵硬,有啥东西堵住了口腔。
这时,一个容貌娇好,十六七岁的姑娘左手端个杯茶,右手拿着根塑料方凳过来,那男人一眼看见,凶巴巴吼住她:“小红,你咋不长眼睛,也不看事,一点脑壳都没有,一个罪大恶极的杂皮杂种,端啥子凳子,喝啥子茶,让他站着。”
张君在一旁不便说话,他知道阴间的鬼同样嫉恶如仇,对于人死的说法,就有很多讲究,如英雄死了,叫牺牲,一般的人死了,叫百年后或升天,冤枉整死的,还要平反昭雪,来个追认啥烈士啥党员的,在阳间,五花八门的名堂更多,这些,都是向阳间学的。
对前一类人,来时人家都客客气气,像文强一类残害百姓死的,人家不可能给好脸子看,不像人间,只看钱,谁的包包鼓,看谁的官大谁有权。
咪咪眼的人从抽屉里拿出张A4大的空白表格,叫文强填。
待文强填完表,那人把表格从文强手里拿过来,偏着头看看,又递回文强,指着一个地方,叫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按手印。
签完字,按过手印,记很快登完,该安排去处了。
那人把表放在嘴边尖起嘴把墨水吹干,对文强说:“先五马分尸,然后下油锅,在十八层地狱去推铁磨。”
文强一听差点昏倒,双腿打颤,他哪里经历过这样的阵仗,太阳穴两边的青筋乱跳,眼前金星飞舞,身子肌肉紧缩,裆下一阵发紧,尿都快流了出来。他颤着声说:“这位官长,能不能不分尸,不下油锅,把我和张君安在一起?”
张君也被吓住了,忍不住说情说:“我们是熟人,老朋友了,把他安在我那里吧,平时两个也好有个照应。”
文强手伸进裤腰,抖抖索索摸出五根黄灿灿的金条,仍不敢抬头,曲着背上前一步,弯着腰,小心将金条放在桌上,怯怯斜一眼那人说:“官长,行行方便,这点小意思,您,您老买包茶喝,买包烟抽,一点小意思,实,实在不成敬意。”
谁知那人一看,脸顿时拉长,桌子一拍,骂道:“文强,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把人间那套拿到阴间来耍了,你以为你有钱,真的就能使鬼给你推磨,给你说,听清楚了,那是你们在阳间放你他妈的狗臭屁,一派打胡乱说。”
张君见场面僵了,看了文强一眼,怪文强事先也不和他打招呼,以致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怕不好收场,忙打圆场说:“官长,没啥意思,真的没有啥子意思,文强只是说,让有个关照嘛。”
文强想最后争取一下,声音细如蚊子般问:“张君安在十六层,我为啥要安在十八层呢?”
进门时,他问过张君,知道张君在十六层地狱。
那人从牙缝里冒出一股冷气,道:“张君和你岂能一样,他虽有民愤,但不少老百姓恨他不起来,张君代表的是他个人,是刑事案件,而你,却代表的是共产党,代表的政府,你和你保护的那些黑社会,穷凶极恶,贪得无厌,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奸淫妇女,打着的是合法的外衣,政府的幌子,共产党的招牌,罪比张君大到哪里去了,影响更大更坏,老百姓不把这些看成是你个人的作为,而是把它算在党和政府的身上。哼,你还想和张君比,你自己想想,能比吗?去去去,别在这里费时间磨牙齿,说啥子条件了,快走快走。”
两人看那人一张黑脸,铁豌豆油盐不进,只得从屋里悻悻退出。
路上,文强突然问张君:“张君,阴间有女人吗?”
张君随口说:“有哇,咋没有,哪里都有,怎么,你想结婚?”
张君知道,这次文强的老婆没有一起来。
张君当然明白文强的心思,好奇的问他:“二哥,听说你在阳间搞了许多女歌星女演员,真有这么回事?”
提到女人,文强立时来了精神,暴眼放光,如数家珍说:“有,有有有,有这回事,只要来到重庆的,我都要想法弄上床,那味道好爽呀,有个女的,那地方好紧,搞起只那么安逸舒服了,可惜你没有尝过。哦,对了,”文强又像突然想起说,“张老弟,你看接待室那个小红咋样,女娃儿细皮嫩肉蛮乖的,十有八九没有开过处。”
张君盯着这个七分猪样的色鬼,恶心想吐,刚想骂他几句,迎面走来两个尖头的瘦高个子,都穿着拖地长衫,一个黑如煤炭,穿白衫,一个白如冬雪,又穿黑衫,黑白分明,两鬼舌头从口里面吊出,长至脚面,每鬼头上,戴顶丈余长的尖帽,手里,各拿着一串拇指粗的铁链。

张君用胳膊碰碰文强说:“别说了,黑白无常来了。”
“黑白无常是干什么的?”文强好奇地问。
文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阴间的事,他知道得很少。
“干啥的,拿人的唄,”张君斜一眼他道,“好比抓我的警察。”
说话间,黑白二无常来到跟前,黑无常提起链子要往文强脖子上套,张君伸手想挡,说:“二位大哥,别给文强套了吧,他跑不了。”
黑无常拨开他的手说:“那哪里行,不行不行,阎王说了,他倒想看看,文强倒底是个什么鸟,什么玩 艺,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和能耐,搞得三千万人口这么大个重庆城乌烟瘴气的。”
天空突然落下几滴雨,太阳沉入山后,一团黑云飘到头上,几个鬼急三慌四在高低不平的泥巴路上,小跑起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