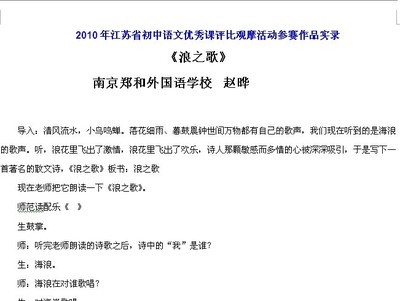朝鲜之歌
王 陆
导语 这是我2007年写的一篇散文,先投到《散文》杂志,执行主编汪惠仁先生立刻回信,说“这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但我等了好几个月,最终没有发表。我理解。后来投到《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也回了信,说需要等一等,但最终也没能发。所谓政治气候吧,我不以为然。无论什么气候,我都相信眼睛,相信人类共同的感受。我的朝鲜学生们都私下里读过到这篇原稿时,他们只能用无声的眼泪来表达。时间已经过了五年了,那些学生我已经联系不上。这次朝鲜又起大的政治动荡,不知这些青年是否能可好。他们的家庭与那个极权王朝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荣或损,都避不开,逃不掉。今天,我又拿出这篇文章,重读了一遍,往事历历,难掩心酸,不仅仅是为了朝鲜,也是为了我们。面对残暴,一言不发,还算什么礼仪之邦,正义之人?
一
父母在世的时候说,朝鲜的大米好啊,都是油香油香的,不用就菜都好吃。那次父亲病重吃不下东西,母亲就给他做一小罐“芥渑祗”(朝鲜辣菜),又打发我买回一点盘锦米。母亲把盘锦米用一点花生油淋上,凉干,再淋油,又凉干,然后用瓦锅焖上。米饭端到父亲枕边,母亲舀小半勺,哄他说这是朝鲜米。父亲就睁开了眼睛,抖动着嘴。多少年过去,一提起朝鲜,我就想起朝鲜大米。我想,父母是中国人,虽然他们年轻时在朝鲜闯荡了十六年,可他们大半生毕竟是在中国营生的,什么好吃好喝没见过?为什么偏想着朝鲜大米呢?
大哥年长我二十二岁,他生在朝鲜咸兴,在那儿长到六岁。几年前,他得了脑血栓,但一问到咸兴的家,他依然能比量出那个样子,那幢房子有青瓦翘檐,房前有苹果树,房后有青石桥,桥下是滚滚的顺川江。他最愿说的是他的朝鲜干爸干妈,那年过春节干妈给他缝过一件“韩帛”(朝鲜服),是蓝色刺绣襟面,白色丝绸领口。他现在保存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穿这件“韩帛”的。一说到这些,他就激动,一激动,他就干哭。大哥是粗犷性情,很少叙长道短,却为什么单单对老早的咸兴情景有那样细致的牵挂呢?
2005年11月15日,我去朝鲜讲十二周中文课。从大连起身时,是零风碎雪,过了丹东鸭绿江,风雪就大了。新义州是雪,定州是雪,安州还是雪。我紧挨车窗,往最深最远处看,风天雪地里只看到隐约的房子和零星的人影。1927年,父亲是沿着哪条线去咸兴谋生的呢?1943年,父母领着大哥大姐和二姐又是从哪条线逃离朝鲜的呢?今天我不是要寻找全家的历史路线,但我意识深层依然感到有一种推动,让我的身体和思想走近某个地点和某个时刻。其实,这没有现实意义,因为人与事都不在了。有关朝鲜,我懂得一些。我不会像某些游客,总想窃窃私语和揶揄,但也不会像父母和哥姐那样,总是耿耿缠绵着。所以,当躬背的行人与耸立的标语在风雪中此远彼近,当朝鲜陪同小朴介绍沿途的这个或者那个,我都是另有思想。
自由的步行者,不需要带路。但我告诫自己:你经历了很多,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是一只青蛙,很可能你依然是一只蝌蚪。
朝鲜风貌确实触目。比如,在平壤,庞大的建筑、宽阔的马路和整洁的面目,就像一个超级主题,而人们在主题下面,简陋着,冷峻着,相信着。看平壤是一回事,看咸兴是另一回事,再偶然看到乡村,看到田地和路基,你就会感到这个非常的世界与你冷静的思想并非风马牛不相及。
我想到我在平壤的第一节中文课。那天是傍晚,很冷,大教室里没有供暖,是坐得满满的青年用他们的热忱烘暖了空气。那天我介绍中文流行报刊,刚讲到一半,电停了,一片黑暗。下面八十多名学生整齐地坐在黑影里,没有动静。有一个负责的学生很快从包里拿出两支蜡烛,在我的讲台上一边点燃一支。我从来没有在烛光里讲过课,但在这烛光里,我的感情是明亮的,我是能看到学生们的眼眸的。蜡烛燃尽,学生依然不走。这样自始至终的专注和渴求,中国学生现在恐怕没有了。我知道这种意义。因为我十六、七岁时也是这样,为了买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唱片,我天不亮就在大连东方红商场门口排队。也是这样的冬天,排队的青年也是不可阻挠。
但是,我的目光仅仅是用来捕捉这些景象的吗?我叮嘱自己:不要依赖平面,也不要依赖观念,就做一滴温水吧,去浸淫身边的泥土。但,我发现,这非常难。好比在一片经久的板结泥层上,我只能晾晒在寒石冷沙上。
从平壤去咸兴,火车途经阳德站时,无故停了车,一停就是几个小时。我看到窗外对面货车底下躲藏着一个男孩子。他光着小头,黑黢黢的,穿着破旧的单衣服。我再仔细看,他的右衣袖是空管。我打开窗,向他招手。他羞赧地看着我,胆怯又渴望。我把我的一件毛背心拿出来,伸到窗外,向他递着。小男孩猫着腰,左看右看。我想他是害怕,就把毛背心放在了地上。可他向我这儿走了两步却突然转身往远处跑去,空荡的右衣袖在他身后飘着。有一个男人紧追着他,而另一个带袖标的女人快步来到车窗跟前,用汉语问我这是谁的衣服。我说是我的,是我送给那个小男孩的礼物。她用鞋尖踩着毛衣,背着手,愤怒地喷撒出一堆的朝鲜语。小朴对我脸色也不好看,说我羞辱了朝鲜儿童,也就是羞辱了朝鲜。我走下车,把衣服捡起来,心很难受。我的朝鲜兄弟姐妹,你们在说些什么啊!1943年冬天,比这个天还冷,日本宪兵迫害在朝华侨,我父母领着我三个哥姐,连夜逃出咸兴。他们是怎么逃出的啊!是朝鲜干爸干妈给他们换上朝鲜衣服朝鲜鞋,干爸还借一辆牛车,送他们一路过了平壤,上了席岛。对于我们一家而言,朝鲜的长裙短袄已经远远超过了温暖和美丽。大哥总跟我说,干爸的名字叫郑泰吉,这家人好啊。这段家史,一直在我心中淙淙流淌。现在,朝鲜似乎只是一个国际政治词汇,日常生活的痕迹统统被淹没了。我在大连所任教的大学里,中国学生也好,俄罗斯、日本甚至韩国学生也好,问到朝鲜,都是遥远陌生的感情。难道生活人心也如同季节,彼时是枝叶相连,此时就是冰冻雪封吗?
这里肯定有一个巨大的空白,甚至缺陷。这种空白或者缺陷连眼睛都逃不过,怎么能逃过心灵呢?
二
冰路雪途中,朝鲜的路面如同皲裂的皮肤。偶尔看到一辆汽车,从窗口,从轮胎,从代替汽车燃油的燃烧的木炭,都能翻捡出朝鲜人的不容易。还有代用的铁路枕木和失修的桥墩;还有,山脊和瓦舍,有旗帜有标语的地方,有炊烟有儿女的地方,都装在我的眼睛里。那天,在咸兴,我看见了岔路口上有一辆拉着木柴的牛车滑进了路边的浅沟。我招呼停车,要大家帮助那个农民把车拉上来。在七手八脚中,我发现牛车的车轮竟然没有轮胎,是光秃秃的木轮!还有,车老板的两只脚上不是鞋子,而是绳子捆绑的鞋底和几层脏布!朝鲜农民这样的日常盖过了我的思想。我没有去想它是什么政治意义或经济意义,我想到的是他的一家人,想到他们的脚底和脚趾。我的心瑟瑟发抖,感情一刻间被颠覆了。我看到了小朴非常难堪的眼神,也看到农民大哥负罪般的表情。农民躲在车后,藏在人后,怕我再看。我的泪一下子涌了上来。我把脸转向别处,不忍再深入想。一条冰河伸向远方,它大概就是大哥说的那条顺川江吧?江边的枯草中已经有了一只寻食的小麻雀。小麻雀羽毛稀薄,张望着天空。

我记起1974年,也是这个季节,全中国都在声讨一个意大利导演,他叫安东尼奥尼,因为他拍了纪录影片《中国》。当时我十四岁,学校要给《旅大日报》组织批判稿,要我从小学生的角度驳斥这个“帝国主义文化特务”。谁也没看过这部电影,但上面发下来一本厚书,叫《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东串西联了一些句子,又加进“帝国主义的跳梁小丑”、“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之类的话,交上去了。其实,那时我最关心的是放学后能打下几只麻雀来吃。大连那时每人每月是一块豆腐、半斤肉、三两油,辽宁省那时有个大干部,我们就叫他陈三两,他早就不在人世了,但我们还是这么叫他,根本不原谅。少年饥饿,还能有什么与鸟与人与理想与主义的共鸣之心?我那时身单力薄,又是近视眼,但我能用绳子勒死一只狗,能用弹弓打下起飞的麻雀,最多时,一天能打下18只。我把活麻雀裹在粘土里,用火烧,觉得好吃。不是人性恶,而是肚子饿。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是在1987年,1992年又看了一遍,才认识到我和我的祖国那时对安东尼奥尼的谩骂是多么的野蛮。和英国华人作家韩素音那种引颈高歌不一样,安东尼奥尼是在“到处莺歌燕舞”的铜墙铁壁中窥见到了中国70年代沧桑的民间,然后告诉世界:这是中国农田里疲惫的牲口,这是中国都市里简陋的晒衣绳,这是中国孩子的出生,这是中国老人的死亡。都是日常,冷静而忧郁。因为真实,70年代的中国面貌被力量性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民族的心性也在此凿刻了下来。我跟我的每一届外国留学生都说:如果你们想理解中国为什么要炸堡垒,破航道,搞改革开放,就看《中国》这部片子吧。
在朝鲜,我没有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可那份亲人般的敏感和真诚,我心里有,眼里也有。在咸兴,侧倾之间,看到许多泥坯房窗户是空的,看到许多家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的窗户上蒙着白塑料布,还有的是遮着纸盒板,我就知道了,这里的玻璃是怎样的奇缺;在平壤和咸兴的郊区,无论远近,都找不到一处像模像样的温室大棚,田野与荒山一色,我就知道了,这样的季节里,孩子吃什么,老人吃什么;还是在咸兴,那次我发高烧,到医院我要求挂一个青霉素吊瓶,医生却百般劝我用朝鲜的草药,我就知道了,这里的药品比食物更缺乏;我还知道,家家户户缺煤少柴,因为在电视新闻里一位人民军英雄的母亲在家里穿着大棉衣,窗户上结着厚冰。还有,我知道了,朝鲜学生书本奇缺,眼镜奇缺,钙片奇缺。
这里奇缺的东西一定比我所看到所想到的更细微,更深远。
那天和小朴在我房间闲聊,谈到孩子,我问他有几个孩子,都多大了,他张着嘴,淡笑了一下,说他就一个女儿,叫静云,再有两天就是她12岁的生日了。他从口袋里拿出钱夹,里面有静云的照片。小静云有一双善良的眼睛,这和我女儿很像。想到我女儿那么大时,有多少绽放和渴求啊!我想给这个朝鲜小女孩送一个礼物。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东西来,我就把我正在用的MP3打上包,写上汉字,是“祝福小静云,12岁是春天最美丽的花朵”。但是小朴坚决不要,他说孩子这么小,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在送拒之间,我不仅强烈感到了他的自尊,还感到了他的某种警惕。这是一堵墙,无法勉强。可是,除了这个,我还能给孩子送什么呢?我挺不愉快,不再做声。这下,他倒难为了起来,脸也红了,手脚也窘了,他吱唔着说,让他请求一个礼物吧。什么礼物呢?他问我能不能把我带的一箱牛奶送给他一袋,让他女儿在生日那天尝一尝。
这件小事是非常历史性的,我至今想起来,也是难以平静。我不知道一袋牛奶能给这个朝鲜小姑娘的生日带来多大的欢乐,但她赠送给我的礼物却真真切切地让我满心喜悦。那是一把美丽的折扇,扇面是小静云自己画的。是一只翩翩欲飞的小翠鸟,颜色无比鲜亮。
这面折扇现在挂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我无数次地揣度这个小小的扇面:一个还要与大人一道承负艰难的小姑娘是从哪儿积贮了这么饱满的感情呢?这是来自单纯的艺术天分,还是来自人类内心不由自主的生长?
三
朝鲜人的方向沉闷而独绝。沿途而往,草痕石迹,枯硬连绵,非同一般。你似乎透不过气来,或者,你会鄙夷。可是你有什么理由啊?看到一根鱼刺穿透了蝴蝶的翅膀,你的眼睛不也是随之疼痛吗?
你有眼睛和经验,你就会有你的道理。可我得说,你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可能只是政治上的道理。政治,不简单,但是,人,却非常简单,一碗饭,一件衣裳,一床铺盖,要喘气,要排泄,精子和卵子要相依为命,而已。即使在最严酷的迫使中,精子和卵子也要润滑,也要伸张,也要分娩。
在朝鲜,最简单的事情最不容易发现,可一旦发现,你就明白,他们的生活曾经就是我们的生活,就像鸭绿江两岸,都是一样的碧波。
那天在咸兴。早晨防空演习,在一个简易防空洞的拐弯处,我蓦然看到了朝鲜人泄露的生活。我看到了一束干瘪的花!花是插在一个锈迹点点的炮弹壳里的。在等待演习解除的潮冷中,粉色的干瓣与枯蕊就像少女死亡的唇和乳头。我想用矿泉水稍稍滋润一下,但发现炮弹壳里已经有了盈盈的水。我问这是什么花,小朴不知道,他问旁 边一个拄拐的残疾老人。他告诉说这是凤仙花,春天里咸兴满山遍野都是。他还说,有一首歌曲就叫《凤仙花》,他还用拐棍打拍子,哼了几句。小朴翻译给我听,有这样的句子“你一定等待很久,才这般开怀绽放”,是讲一个人背井离乡,悄悄同山坡盛开的凤仙花道别。
这种简单的美丽不是一处。在这个冷峻和阴湿的空气里,在一些带袖标的男女激昂的穿梭中,我看到一个又瘦又黑的姑娘倚在洞壁上,偷偷地给自己抹唇膏,然后羞赧地给旁边一个小伙子看。小伙子悄悄说了什么,姑娘满脸绯红。其实,那位姑娘的嘴唇非常艳嫩,什么样的唇膏能比得上她嘴唇的芳泽啊!可是,那位姑娘对唇膏不顾一切的渴望,谁又能挡得住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背景,都挡不住美丽。我9岁那年,也有这样的防空洞和气氛。苏联百万陈兵嘛,我们也是以战备为第一生活,每天都唱“刀出鞘,弹上膛,同仇敌忾打豺狼”。大连甘井子那些纵横的防空洞我都呆过。近四十年过去,有关当时的激烈气氛和心情都忘了,但在防空洞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却一生不忘。那一次也是演习,解除警报后,我们都回家了,有一对青年男女偷偷留藏在了里面。可能是摸索到了爱,可能是在黑暗里难舍彼此,他们想出来的时候,各道洞口的层层铁门都锁上了。半个月后,人们发现了这对青年,俩人都死了。男青年是咬着女青年的发梢,女青年是含着男青年的手指。女的是我们家后街理发匠老田家的二闺女,脸上有一些雀斑,手巧,织战备网织得又快又好。男的是街道民兵,会吹口哨。这件事,街坊大人戳戳点点,上纲上线,可在我少年的心里,它就像蔷薇,急切地蔓延着。我慢慢大了,懂得了只要有花粉,就一定会有盛开,即使是在铜墙铁壁中,也要盛开的。
我告诉小朴,我喜欢情不自禁的东西。唇齿之间、眉目之间就是面貌,昏黑也好,饥饿也好,都不能拆除它。我不明白,那些乘兴而来的外国游客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为什么,朝鲜人对自己真实的面貌也视而不见,甚至遮遮掩掩?
那天,小朴搞来两张票,是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的大型歌舞演出。小朴以为,我所寻求的朝鲜之美就是宏伟的歌舞,是万众一心和辉煌。小朴啊,就像一个贫掉底篦却又好面子的主人,背后喝凉水,当面打饱嗝。可,我怎么跟他说呢?说我从小就反感大型歌舞?说我厌恶仪仗队,厌恶合唱,甚至,厌恶“万众一心”这个词?我好像不能那样说。我只是说,我太累了,我想安静。他很敏感,目光很强烈。他冰冷地说:你要不去,是不礼貌。
我也是冰冷,直话直说:我不喜欢大型歌舞。
他走出门,又回来,嗫嚅着说,这个晚会有他女儿小静云,她在《统一的彩虹》里领跳彩带舞,他答应她演出后领着中国的王伯伯到后台看她。
我忽然感到,我和他之间有一种推脱不掉的东西。可是,在这样的近千名少年儿童的演出群里,我怎么可能找见小静云啊!他说“静云在那儿,在那儿”,我说“噢,噢,看见了”,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知道小静云是快乐的,她一定像一朵小浪花,在里面用力地翻腾着。我怕她摔下来。一个孩子为了博得赞赏,会不惜一切。
我在小静云那么大的时候,也是,排在整齐的队伍里,不惜一切。是1973年夏天,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要参观大连。在大连沿途组织十万人欢迎人群,我们学校的方块表演队是在火车站台里,要在“亚非拉人民心连心”的歌声里挥彩棒,变队形,整齐地欢呼,整齐地欢笑。本来我是在第一排,彩排的时候,市里检查的人跟老师说我的眼太小,还有些鸡胸,要换一个身高眼大的能体现新中国青少年风貌的学生到前排来。我就不高兴,非要在第一排。我还说,我可以把眼睛睁大一些,也可以把胸脯挺高些,这都没有问题啊。几个老师一块剋我,说我小小年纪怎么敢不服从革命需要。我就哭了,还把彩棒扔了。正式欢迎那天,班里别的同学都正式穿着白衬衫,握着彩棒,上了大卡车。我留在班里。留在班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拄着拐的女生,另一个是中苏混血儿,我们一齐擦玻璃。
那以后,一看到排练的大型的东西,比如千锤百炼的队形,比如万众一口的欢呼,我就痛苦。
可是对小静云,我只是抚摸她的头,跟她说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读书,要多吃东西,身体最重要。
很长时间小朴和我都不多说话。他有他的性格,我也有我的性格。这与民族与国家与历史有关吗?在冰冷的宾馆里,晚上我一个人,写日记,备课。那天又停电,我走到街上,是星月寒风。走近万寿台,我前边是一个背着书包、衣衫单薄的小男孩,他走向金日成铜像。到了铜像底下,他放下书包,向铜像鞠了三个躬,然后背上书包,消失在黑色中。我看到了他雾一样的呼吸,我的心也随之苍茫起来。
第二天,我把晚上看到的告诉了小朴。我说那个孩子有多么矮,有多么瘦,有多么忠诚。小朴,忽然,背过身去,捂着脸和嘴。我不知所以。他蹲了下来,曲着十指狠命地抠着自己的头,泣不成声。我只能拍着他的肩膀。他告诉我,他的儿子也是那么矮,那么瘦,也是那么忠诚,9年前,没有吃的,死了。
我不能问,也不会安慰,只能等着他。可是他擦干了眼泪,又告诉我,朝鲜人不怕苦难,因为他们有卓越的领袖。
四
这种感情不顾一切。
还有一首歌曲,也是不顾一切的。它名叫《苦难的行军》,是男声大合唱,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是泥泞的节奏,是顶风冒雪的旋律。我怎么掂量不出,这里面的咬牙生存,还有所埋葬的代价呢?
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决定生活在其中,并为此注入了神圣和希望,其日常生存必然如攀岩一样。中国人也曾经这样。我,一个遥远的中国人,凭什么以青蛙的姿态来嘲笑蝌蚪的幼稚?
所以,我一言不发。朝鲜的空气是清新的,河水是清澈的,人民是忠厚的,但我的眼睛却常常充满泪水。小朴在吉林大学留过学,他懂得中国,他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心思呢?但是,他从来不探测我。我也是,不想让他为难。所以,一个人的性格与感情怎么能与民族的命运没有关系呢?
我不怀疑这个民族。逼山仄水必有荆棘苍茫,带血带泪的,九死一生,肯定激烈,肯定倔强。
在我的家乡大连旅顺白玉山,就有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的骸骨。看1910年他在哈尔滨击毙日本首相伊滕博文,看他在旅顺日本监狱写下那首汉诗“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烈。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就知道了这份汹涌的骨血。干爹郑泰吉一家也是。父亲讲过,1942年,郑爹的三儿子郑义玄也要去会宁,拿枪打日本。临走的夜里,我父亲过去给他理了发,郑妈妈用手把儿子的头发捡起来放在布袋里,都是缕缕的青丝,但一家人却都没掉泪。
我坚信,这种荆棘之根已经给了这个民族一席之地,但眼下,我不知道怆痛瘀血之中能否生长出一棵理性之树,至少是一株理性之芽。我亲眼所见,农舍里没有灯光,工厂里也多是裂墙和破风,但坑坑洼洼的路边总有低头背着大包裹赶往远方的人。我心有纠纷,却看不清面目。这十几年,我看不清朝鲜的生活,但是饥饿、逃荒和死亡迎面而来。一个家住顺川的失去父母的10岁小女孩,讨不到饭,就从排水沟里捞些残豆残梗,细细地嚼,然后唇对着唇,送进襁褓里的小弟弟的嘴里。她抱着弟弟从冬天捞到春天,从朝鲜嚼到图门又嚼到大连。这个女孩叫白顺喜,她现在23岁了,是我的学生。
我一直在思索白顺喜,为什么一个没有力量、没有哲学的孩子能在饥饿必死中活着并且长大?我想是真实的本能吧。从哪条路来,往哪个方向去,不重要啦。真实地生活着比什么力量都大,比什么哲学都强。
我想到中国文革结束不久,《美术》杂志有一个封面,是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罗中立的《父亲》。画的是巴中农民的褴褛,是中国的僵硬,讲述着几十年人民无奈的心情。当时上上下下有多少人对《父亲》斥责啊!可是在大学里,这个图画被我们镶在了人民日报的报栏里。我们的泪光是盛在思想里的。有什么作品能比痛心地表达人民的心情更伟大的?还有一首诗,是北岛的《回答》,“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讲的是时代真实的心。我们在那个时代啊,就像风聚集在路口,前呼后拥地走,有真实的青年,有真实的作家,还有真实的领导者。真实是最能让人警醒的。没有什么真理能大过真实的生活。
所幸,朝鲜也有这样真实的青年。
他叫金泰信,是朝鲜元山人。其实,他的奶奶是中国人,他有华侨的身份,但他从来都说他是朝鲜人。1996年是朝鲜大饥荒第三年,他17岁,父母为了儿子活下来,申请送他来中国学习。他汉语说得不好,是当时我班里最差的,拼音声母里“z”“j”不分,常把“早起”说成“脚气”,但他在班里却是最努力的。班里有韩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都是家境不错的,他们课上课下都是随意的,而金泰信不是,他话少心重,上课用的报纸都不舍得买,但他的眼睛里有渴望。那年冬天放寒假,其他学生都走了,就他没走。到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是热热闹闹,我就去学校把他接到家里。家里有酒,有菜,有饺子,还准备了朝鲜年糕。他酒喝得多,年糕吃得多。到半夜烧完纸,电视上响了新春钟声,我给女儿二百压腰钱,也给了他二百元小红包,他死活不要,我硬塞给了他,他却哭了。
春天开学,他没来。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了。一晃过了五年多。那天,我下最后一节课,看见教室门口站着有一个高高棱棱的青年,他喊我“王老师”。我仔细看才认出来,是金泰信。他完全脱了样子,穿一件蓝条绒西装,是一个很体面的青年了。那时大连有一家平壤菜馆,他开一辆马自达把我拉到那儿。第一杯酒,他站了起来,向我鞠了一躬,说了一句“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几杯酒下肚,他才慢慢说起那些年。
他家乡元山先是定粮减少,而后是上山挖野菜刨白菜根,到海边捡海菜抠海蛎子。后来这些也没有了,他父亲就领他扎猛,碰一点海货,但那次父亲被破渔网缠住了,死在里面。再后来,全家定粮一个月只有10个玉米棒,最后连玉米芯和玉米秸都给煮烂了吃了,老鼠也吃了。奶奶死的时候肚子都是鼓鼓的,里面都是风。按朝鲜风俗,人死入殓嘴里要塞进一捧大米,让魂儿走黄泉不饥不饿。但家里没米啊,他和姐姐就捡些米粒大小的沙子,洗净了塞进奶奶的嘴里。过一年母亲也死了。大姐生下一个女儿,都两岁半了还坐不起来,最后大姐是搂着孩子睡死的。现在,家里只剩下二姐一个亲人了。
我问他咸兴怎么样。他说咸兴也是一样。我的泪怎么也收不住了。
他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做出口朝鲜的粮食生意。他又开车拉我去他的住处。他住在皮口港,离大连有一百多里地。他的房子离码头不远,是小二层楼,里面没有什么家具,都是堆的货物,有米袋,有面袋,还有化肥。房子前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种的不是花草,而是半地的玉米,半地的高粱。他说,种花没有用,还是种粮食好,看到玉米穗和高粱花,能想到家。玉米和高粱都是迎向大海的,海对面看不见的有云有雾的远方就是朝鲜。
亚麻色的玉米穗儿,火红色的高粱花,谁能说不美呢?对于饥饿的国家来说,热爱庄稼,拯救亲人,应该是最高尚的信仰了吧!我们的父亲母亲当年就是这样。我是出生1960年的。为了我和我上面七个哥姐都能活下来,母亲把姥姥的一大块坟地给平了,开了荒,种上地瓜;在饭店工作的父亲还偷过东西,他时常抓一小把米或者黄豆甚至豆腐渣塞在鞋窠里,回家煮给我吃。但那天,米从他的破鞋洞里漏出来了,让单位领导抓住了。父亲挨过批,办过班,政治上一直没抬起头来,但我们这些子女都活了下来。
金泰信告诉我,他这几年里往元山送过上千吨的粮食。我没有算过,上千吨的粮食能让多少人抗过多长时间的饥饿。但我知道这是另一种不顾一切的力量。不顾一切地成长,不顾一切地把粮食送给亲人,甚至以命相搏。这种力量比天大。
我听过一首钢琴独奏,叫《阿里郎奏鸣曲》,是金哲雄弹的。风雪般的旋律仿佛是泥泞里的脚步,有乳房干瘪的妇女,还有奄奄一息的幼儿,更多的,是嶙峋的青年,他们扛着米袋,踩着冰河,蜿蜒向前。夜深独自时,我反复听,反复被淹没。这是最大的主题,是人民的主题!
五
我在朝鲜一路,思想比语言多,层层叠叠。小朴告诉我,现在朝鲜那些能够种庄稼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即使是平壤,在大同江两岸,在居民楼间隙,在夏天在秋天也能看到玉米秸和地瓜蔓。可惜,不能等到春天我就得回去了。我想,春天里,随风摆动的禾苗一定是平壤最庄重的景象。
其实,在这个沉寂的冬天里已经悄悄有了绿意,大街小巷有了新的标语,上面写着“种子革命、两茬农业和土豆革命”,还写着“彻底告别饥饿”,还写着“只有大家都吃饱饭,我们的腰板才能硬起来”。我选好“只有大家都吃饱饭”的标语一角,让小朴给我照了一个相。
新年除夕,平壤大街突然刷出一片的明亮,有彩灯,有霓虹灯,万家都是灯火,大同江也是,江面像光亮的眼睛一样。我四下望着,心底有意外的惊喜。
路边有行人,越来越多,朝着金日成广场方向走。我也跟着人群走。前前后后,青少年多。有一个清脆的口哨声突然响起,我猜,是年轻人之间的召唤吧。金日成广场上,青年们盯着人民大学习堂顶部的大钟,跟着指针一步步向前,都是虔诚的。大钟响了,许多人伸出手臂欢呼,也有许多人紧紧裹着棉衣一动不动。我看到一个明亮的窗户里,有一个少年伸出一支魔术弹,燃起后,窜出红色和蓝色,向夜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所有人的眼睛都跟了过去。这是属于青少年的夜晚。我想到我少年时的心情,也是这样。1975年最后一天夜晚,我们那帮浑小子在大连斯大林广场逛荡,宣传车喇叭一遍遍地播送元旦社论,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还记得里面有最有权威的一句“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全是目”,还有最激昂的一句,“在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吟诵毛主席的诗词,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那天乱风碎雪,衣单身寒,我们根本看不清天空,但新一年最年轻的时间最终不是我们的吗?时针不停,冬杀春生,千秋万代从来更新。
过了元旦是春节,我也要回家了。家里人还等我回去挂红灯笼呢,父母在墓地里还等我去烧纸拜请呢,还有年三十那顿饺子呢,还有大年初一大早学生们来给我拜年呢。想到这些,我的心便像孩子似的不顾一切了。
我也想到,金泰信现在是不是也和我似的,背起了包裹,不顾一切地往家赶?是,他一定是和我一样的。他有姐姐在家等他。有家,才有千山万水,才有祖国。
安重根烈士也是吧?他一定会在除夕香火氤氲之时回到家乡黄海道海州,他要看子孙,还要喝子孙端供的年糕汤。英雄也要子孙香火,也要庄稼牲畜。
我再端量一下平壤,再思量一下我和中国,思想一下子变简单了。庙瓦宫檐,斗角构心,无关乎亲人身上一寸布;日月星辉,哲学道路,哪及得百姓手中一碗米!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生结出那么多的冻疮、险恶和屈辱。我是1960年生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简单而复杂的存在中生长出来的。谎言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啊!它能假扮成广袤的星空让我们仰望不到尽头,而真相却像散沙。但就是散沙里分娩出了一株又一株最坚硬的植物。而今三十年,期待已久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坚硬地活了下来,终于有了一片葱茏。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是长吁一口气。
我临走那天,天是晴天,但风还是硬风。平壤火车站里没有暖气,硬风钻进候车厅里,凝结成第二种冬天。小朴来车站送我。他拿出两个绸布小口袋,说是送我的礼物。我小心地打开,一个是装着四个苹果,一个是装着一斤多的大米。苹果和大米的样子恐怕远不是大哥记忆中的样子了,但我知道这是小朴家里最好的东西。他用家里最宝贵的东西来满足我对朝鲜的感情,我心里是热乎乎的。他小声说,朝鲜苹果举世闻名。我说是。他又说,朝鲜大米也是举世闻名。我又说是。我嘴是那样应着,心却不是那样想着,咳!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痛苦。我责问自己:别人的景象真的与你无关吗?如果你的历史和经验已经为你赢来了一束烛光,你为什么就不能探出窗户,为夜行者照一照坎坷?我想到板结的土地和干瘪的米粒,想到自欺、善良和坚强。最后,我想到小静云,想到她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应该有什么样的时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