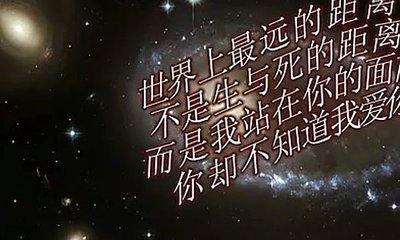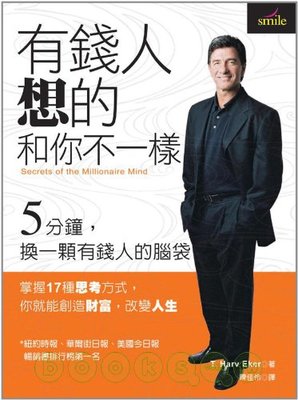栖居于雪域圣地的灵魂
——凌仕江及其散文印象
周天白
其实,给凌仕江写评论似乎有些多余,因为,他自己已经将许多话都说了,包括该说和不该说的。他就是这样袒露着胸怀,裸露着心灵,率真而执着得令人感动,让你读他的散文的同时,去读懂他的人,读懂他笔下的西藏及其故乡。
一、捧着腊梅般冷静和馥郁之沁香走向西藏的凌仕江
认识凌仕江,是在成都,在我办公室对门的《西南军事文学》编辑部。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正是凌仕江刚刚开始创作的发韧时期,他从西藏来到编辑部学习写作。那时候,青春的凌仕江略带些青涩,仿若一枚青果。但你却能从他执后学礼的谦逊中,从那纯净的眸子里看出坚毅和不凡来。从那以后,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他的第一本诗集《唱兵歌的鸟》付印后就是先从印刷厂拉回寄放于我的家中,然后才投放市面的。
编辑部的黄老先生对凌仕江喜爱有加,荐举不遗余力。可是在我看来,凌仕江是不用过于举荐的,尤其是用不着举荐他当官。况且他名字中虽有仕字,但体制上的现实原因,他离仕却相当远。也不是没有人愿意帮忙,但面对体制,你只能徒呼奈何。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虽然这条路看起来有些坎坷崎岖,但文学之路,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为他早就铺好了的。他的人生就这么注定。他只有走下去,包括他走进西藏。假如一定要在作家和普通军官中作一个选择的话,我甚至庆幸,军营里少了一位写官样公文材料的军官,雪域高原多了一位心灵的阅读和叙述者,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凌仕江和黄老先生相约一起去拜觐文珠院的宽林大师。凌仕江特意买了一大束最好的腊梅,走在文殊院前的街上,在许多捧着腊梅的人中显得十分抢眼。冬天的成都阴冷阴冷的,但那一剪寒梅香了宽林大师的佛堂。听说大师甚是喜爱,称赞凌仕江是有大善心的青年俊彦。
最近得知,宽林大师已经圆寂了。不晓得大师走入异世佛界的时候,手上是否握有这个尘世的腊梅,那一缕冷而暖的花香会否陪伴他执着的佛心。但凌仕江捧一剪腊梅前去佛寺礼佛的形象却好久定格于记忆之中。
好像是一种寓意一样,凌仕江捧着一颗向善的心,怀揣着一缕腊梅般冷静却馥郁的沁香走向人间佛国—西藏。“我在西藏之上的天堂里走了十二年,最终我没有真正地走进西藏,也没走出西藏。我庆幸,我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和西藏所有最初的居住者一样保持到现在。真正进入西藏八瓣梅中的只有佛祖释迦牟尼。西藏成批的信徒笃信佛教,释迦牟尼是他们心中崇高的佛。”(《写在前面:西是天,藏是堂》)
“西是天,藏是堂,人在中间是天堂”。这样的句子,只有凌仕江才写得出。这样的意蕴,只有凌仕江才悟得出。他说,“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想让你看到我所坚守的文字方向。而西藏恰恰又是一个容易给写作者创造无限空间的地方”。但人们理解这个句子会更加多维。所以文字写出来之后,就不完全属于作者,每一个人都会从接受的角度,以自己的经验、阅历去理解和诠释这些文字。所以,凌仕江做由自己文章出的考卷只能得一半的分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了。
西藏在凌仕江面前,展开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西藏也必然地要以一种区别于任何地域的自然景观和文明状态呈现在他面前,吸引他,侵蚀他,渗透他,甚至,俘虏他。对一个爱思考的孤独的灵魂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礼遇,是上苍的一种恩赐,特别是当他选择了以散文的心去聆听并讲述西藏的时候。所以,凌仕江说:“上苍在我眼前铺开了一张宽广无边的神纸,我在花边嵌满了经文的纸上开始与神和自然对话,聆听雪山的声音,我离自己更近了!”(《你的腹中闪烁着万道光芒》)
凌仕江选择了西藏。
西藏等到了凌仕江。
对这句话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但我要说,一直以来,亿万斯年,西藏就在那里等待,等待他的知音,他曾等到过一些人,一些介绍西藏的作家,但西藏要等的人不止一个,而这个叫凌仕江的青年应该是他等来的人中比较满意的一个。毫无疑问,西藏,还在等。
二、在苦难中用文学浇灌自己长出大气势的凌仕江
“我说的西藏人,是指与西藏有着血脉关系的在场者,灵在其身上的书写者。”(《我把整个灵魂都交付给了西藏—对话凌仕江》)
凌仕江的西藏与许多人的西藏不同。有人说,如何定位凌仕江的作品,特别是他针对西藏的书写,有时会觉得彷徨。从他的散文作品,既可以看到一个西藏当代边防军人和文学青年的艰难成长。也可以看到一个心灵跋涉者对文学的执著追求,而其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西藏魅惑及其潜藏的言说主体的异样心理和姿态,让人对边缘与现代之间的西藏书写有所思考。
在西藏,生存的艰难自不待说,而于孤寂中面对荒原落日和夜月冷风时的灵魂拷问固然是某种神旨的昭示,但对每个现实中的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折磨和砥砺。
凌仕江说:“越是小小的生命,在西藏越要生长出大大的气势来。”(《不可居无竹》)“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只是我们消解和认识孤独的方式不同,承受力的轻重不同。有时,孤独决定品质,当折磨成为一种享受,最终拯救自己的人永远是你自己,而非永远期待他人。”(《你的腹中闪烁着万道光芒》)
写作成为凌仕江寻求精神寄托的载体,抵抗命运安排的武器,渲泄情感的渠道。他也在写作中发现自我,重新发现西藏。“发现自己,表达自己的发现,从“我”出发,然后接近我们,这是一条朝圣的旅程,你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穿越。……你随时会接收到上苍赐予你的信号,那个上苍,就是另一个你。“(《你的腹中闪烁着万道光芒》)
与其他追求畅销写西藏的人不同,凌仕江十分不屑于对西藏“探询文化背后的隐秘”,不单纯描写她自然的瑰丽、博大、雄奇,更绝不猎奇式地撕开西藏的衣服去展示她的神秘和赤裸。或者说,凌仕江喜欢用他自己的心灵,感同身受地感知进行时的西藏。他笔下的景语,皆是情语。“其实我的西藏只是一个适合让人用来默默感受的地方”(《西藏无言》)“我从乡村一路跋涉而来,此时我正独居于天堂,天堂就在西藏的空间中。这里有神的风景,奇得让我不知如何才能创造神的语言,让你体会我面对长寿佛所产生的神之冥想。我只是尽我所能,向你表达它们带给我灵动的思绪和飞升的灵魂。”(《写在前面:西是天,藏是堂》)
阅读凌仕江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观察西藏。因此西藏的天空在他看来,也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把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与罪恶裹起来。’”(《他的腹中闪着万道光芒·扬长·凌仕江印象记》)
在凌仕江看来,能掩盖一切苦难和罪恶的不仅有雪、时间,还有西藏的蓝天。“天天,天蓝,像一块蓝丝绒,把全部答案裹起来,把一切苦难与罪恶裹起来,让人们以各种姿势在天底下猜测它为何蓝得让人生疑,蓝得叫人伤心。天天天蓝,与谁都无关,天天天蓝,谁都有关。人与天永远隔开着,像愈合不了的伤口。人在天下看天,天在天上看人,看人在天底下的一场烟火表演。天,把人看得很矮——同在一片蓝天下,人比人高不了多少。但天和蓝又习惯包容万千纷纭愁和欢。”(《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
凌仕江在这种啃噬灵魂的俗世的痛苦中顽强地呐喊,长出了自己的大气势。
三、在少年和青年的两种乡愁中纠结的凌仕江
凌仕江说,“丘陵与高原各自以半个故乡的名义将我分裂在城市中央。”(《想丘陵》)
读凌仕江的散文的时候,我戴着耳机听范吉利斯(Vangelis)《征服天堂》的电影音乐,它曾经被电视剧《士兵突击》借用为主题音乐。当连长满足班长退伍前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的愿望,于霓虹灯闪烁的夜色中穿过长安街的时候,震撼的音乐和着班长倒在连长怀里痛苦的场景悲壮地穿行于我的时空,与西藏,与凌仕江给我们的散文所描写的西藏重叠。
军人卸甲和离开西藏,是再自然不过却也是无奈的选择。雪域啊,我把人生最精华的时光,美丽的青春献给了你,甚至,我把我被你改造过的灵魂的大部分都留给你,但我除了是我自己,我还是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这些都是推不掉的神圣使命。况且,无论你头上有多少光环,但从同样绕不开的体制上讲,你不过是一名士兵,十六年的军旅生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离开西藏,心,能够离开吗?
“走出西藏,我才发现我是西藏的一朵云,总在回忆中飘零。我只能用比云朵更轻的声音轻轻地告诉你:云朵——云朵……云朵!——登峰造极的云朵。……忽然想伸出双手搂抱她,怕黏住了灵魂。忽然想钻进去,怕碰碎了宇宙。玻璃般的蓝天,云朵好似神山上盛开的雪莲,当太阳落泪的时候,大块大块的玻璃都被那贞洁的云朵揉碎了心,一丝一缕地飘飘然落到湖光里。”(《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
读凌仕江关于故乡的文章,你常常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这是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造成的效果,在想像空间和视觉转换中,将故乡与西藏进行情感揉合。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凌仕江的故乡在哪里?故乡在四川自贡还是在西藏?
两地都是他的乡愁。
这种将会纠缠一生的乡愁困惑着凌仕江。
身在西藏,他说:“只是有一点我坚信,只要有树作参照,我就永远不会迷失自己;只要树上刻着我的名字,走得再远我也一定能够回得去;只要我不放下手中的树根,即便明天的明天再暗无天日我也能摸着黑回来……进入那一片竹林笼罩的小路,走过那一条芋叶铺出路面的田埂,我听见树喊我的乳名。”他问树:落叶之前我能回家吗?(《一棵刻着我名字的树》)
离开了西藏,他说:“走出西藏,我才发现我是西藏的一朵云,总在回忆中飘零。”(《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而且,“我相信一个人一生当中能让他产生切肤之痛的地方并不多,但有一个地方他却要用一生的情感去堆积它,他对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单纯的爱,也不仅限于对温暖之家的感受眷恋,更不是去过之后就要怀念一场的风景区,这个地方不是家胜似家,在那里或者离开那里之后,你都愿意用尽一生为它歌唱,为它醉舞……你是我梦中打马仰望的天堂”“真正的离去者,必将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我突然悲哀地发现——//他不是别人。//他就是西藏:我梦里梦外的乡愁呵!”(《你的腹中闪烁着万道光芒》)
“离开西藏,也是为了更好的书写西藏,发现西藏,表达西藏,创造西藏。我需要这样的距离来审视西藏。如今,我已正式进驻西藏的后花园成都,而西藏已然成为我的乡愁时代!”(《我把整个灵魂都交付给了西藏—对话凌仕江》)
再说一遍,读凌仕江,是适合听着音乐读的。读《绕不过的布达拉》的时候,建议听埃里奥·莫里康内(Ennio·Morricone)的《西部往事》,伴着那种旷远和缠绵、苍凉得无与伦比的忧伤,去理解凌仕江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虽然他写的布达拉宫所代表的拉萨的斑驳陆离的生活,与我的印象中的拉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应该说,凌仕江的笔触是勇敢而直率的。“在拉萨,只要出门,无须打车,随便你往哪个方向一站,你都有可能望见布达拉,或者说布达拉在看着你,高高在上地看着你的脸和眼,但你并不愿意多看它一眼,这简直成了你无路可退的现实,神在看你,谁能绕得过去?”(《绕不过的布达拉》)这应该是说人始终在某种必须坚守的操守,也就是神的注视下所应有的秉持。
“我已认清更多人生的信念,有时过多怀疑天堂时光简直成了一种真空的迷失,但内心的生活从不虚伪,只有不可阻挡的使命让我如此隐忍空度,空度却又如此沉重。”(《绕不过的布达拉》)这话的寓意是什么?他是不是也如我曾经有过的犹豫一样,是继续把自己完全交给类似于云朵之上的精神世界,还是选择回归脚跟能够有个踏实处,服从自然和亲情的回归?我想,这大约是一种总结式的告别仪式般的思考。
“你要相信,布达拉的光芒一定是照耀过你的,你做的每件事,布达拉都看在眼里,包括你的心事,所有人都可以在后来的后来知道,但布达拉一定已经提前知晓。”(《绕不过的布达拉》)他不仅是想告诉旁人,也是告诉自己,不管你是不是用身体抵达布达拉,但重要的是布达拉始终曾经或者将会抵达你,受“神”的召唤,你曾经也仍然能够在内心保留布达拉。
于是,从身躯上,少年时的故乡开始近,青年时的故乡开始远。而在灵魂上,青年时的故乡开始近,与通常意义上的故乡一样近。
于是,西藏就成了乡愁了。
像许多西藏老兵一样,在西藏当兵十六年的凌仕江的灵魂,栖居于雪域圣地了,永远。
写在后面的话
作为一个先于凌仕江进出西藏的老兵,我的西藏与凌仕江笔下的西藏有许多地方是如此交集和重合,以至于我会从他的文字中找出许多我们共同熟悉的人和事,就像我告诉他这一点时他说的那样:“是的,会有许多熟悉的影子的。”比如《去拉萨看树》、《塔克逊的春天》、《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聊斋查果拉》、《我看见珠峰在移动》、《旋转的布拉宫》、《往返米拉山》,……等等。他甚至用闲笔隐约地点出了我在他的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我在深刻地读懂他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不得不感叹,西藏,就是这样融入我们的共同记忆。大约因为这一点,他才会约我这个行走在文学边缘上的人来为他写一篇评论。
然而,凌仕江的叙述却全然全新,给人是绝然不同的精神体验,让你明白,哦,对这样一件事,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原来还可以这样表述。
在《去拉萨看树》一文中,他说:“……我看到了新的拉萨,新的生命,季节渐趋分明的圣城不再惧怕和低吟冬天的死亡,当树叉与树叉全部枯萎,当你在人的世界里撞得头破血流,不要叹息,离他们远一点,像树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狠狠的钻进地里去,你就可以看见森林,你就能听见小鸟在歌唱,你甚至可以比他们自信勇敢一点,密密麻麻的树舒展着一年四季蓬勃的力量,它们在拉萨神采奕奕地唱着自己的情歌……坐在树下的人,你听见了吗?”
我告诉他,我也是坐在树下的人,我听见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