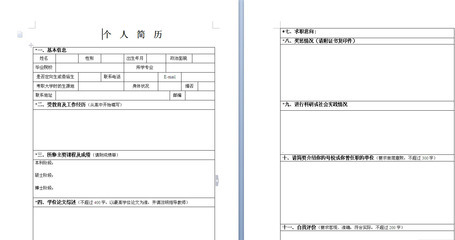敏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亲近的哥哥。
敏哥大我两岁,是我大伯的儿子,也是我们堂兄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但因为大伯年少时就走出故乡去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谋生,所以敏哥虽是我仰慕的近亲兄长,我们却很少有机缘见面。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几乎每个家庭都要遭遇不同方式的悲欢离合,我家也难逃劫数——大伯三十多岁就因心脏病英年早逝,抛下大娘一个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苦苦维生,那年月家家穷困,连火车票都舍不得买,大娘几年回不了故乡一次,我和堂兄弟之间的往来就只能局限于书信了。
还记得八岁那年的冬天,我去故乡的祖父家度寒假。很偶然的一天,看见三个穿蓝色棉猴的孩子站在祖父家的猪圈前对着那只体态并不饱满的黑毛猪指指点点,像是很稀奇的样子。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用自己的手给最小的那个孩子捂着耳朵。那时乡下极少见穿棉猴的人,大都穿着家里自制的棉袄,窝窝囊囊,且有时经年也不拆洗,前襟一块会磨得光亮可鉴,袖口也会磨破,露出星星点点没了本色的棉花。一看那三个穿着整洁的孩子就是城里人。是五婶眼尖,她高声喊道:“妈呀,那不是小敏吗!”祖母听到喊声,忙不迭的从屋子里错步出来,带着哭腔喊到:“是敏儿吗,我那苦命的大孙子,你咋回来了?”
敏哥也很激动,对两个弟弟说:“这是俺奶,快叫奶奶!”两个堂弟异口同声的喊了声:“奶奶!”
祖母一边流泪,一边用颤抖的手不停的抚摸三个孩子的头,嘴里喃喃的说:“都长高了,都出息了,你爸没有福啊,若是能看到你们的今个这模样儿他得多稀罕啊!”
一打听才知道,三个堂兄弟原来是跟着大娘去邻村的姥姥家省亲,大娘脱不了身,才打发他们特地来老家看望祖父母的。
这算是我童年中见到敏哥以及两个堂弟最深刻的一次印象。记忆中,敏哥和他的两个弟弟长得都非常英俊,个子高挑,浓眉大眼,和大伯特像。
后来和敏哥接触最多的时候是他下乡之后。敏哥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难逃下乡接受所谓再教育的劳动改造。他下乡的地方是距沈阳不远的新民县,虽然他可以吃得饱,也不怕干重体力活儿,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在沈阳的大娘和两个弟弟。所以会不时跑到我们家来,表面上说有闲暇时间,抽空来看看二叔二婶,其实多半是求父亲帮他走后门,早点返城工作,以便挣钱养家。可那时候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到处在揪走资派,斗私批修。父亲自身难保,哪里还敢帮助侄儿托关系走后门呢?
那一段我经常能看到敏哥写给父亲的长信,尽述乡下劳动之苦以及大娘在家带两个弟弟生活之难,有的信纸上还能看到斑斑泪痕。信的结尾处总有一些相同的句子:“二叔,你是我最亲的长辈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能脱离农村这个苦海,回到母亲的身边了,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面上,你就帮帮我们吧!侄儿跪求。”
每次接到敏哥的信,平日里最能睡觉的父亲都会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暗夜里不时听到他一声喟叹。
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最终也没能帮上敏哥的忙,直到清点时敏哥才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沈阳。

敏哥其实极具表演天分的,他曾和我说过,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电影演员。如果不行,当话剧演员也行。敏哥并非异想天开,他记忆超群,可以大段大段的背诵当年流行的电影台词,并具备极强的模仿能力。每次他给我表演电影片段的时候,听着他那略带磁性的嗓音,看着他那真诚而迅速入戏的眼神时,我都会被他感染,陷入他制造的情境中难以自拔,甚至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敏哥还有美术天分,我后来喜欢画画很大程度是受了他的影响。他在知青点时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给我和一群孩子们画漫画,他给我们画的漫画像极能抓住每个人的个性特质,惟妙惟肖,令我们乐不可支,我曾把那些画保存多年,并向同学们炫耀,舍不得丢弃。
可惜如此有艺术天分的敏哥,回城后被分配到一家兵工厂,只当了一个普通工人。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变成了以工代干身份,搞起了供销。
大娘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凭一己之力将三个儿子拉扯大并成家立业,如今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其中二子与我同龄,因为患有先天性聋哑症,五十岁时又不幸患上结肠癌,已先去年病故。大娘性格极为刚烈,文化大革命时,别人都当造反派,她却成了“保皇”派,她认为当时的厂领导是好人,不应该打倒,有一次还因此与造反派们打成一团,被打伤了两根肋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院。有人劝她:你一个女人家何苦这么较真呢?她说:我看不惯那些流氓地痞胡闹,非和他们战斗到底。
敏哥遗传了大娘的血性,好打不平,经常和别人打架。某一次在酒店里和客户谈生意,因为对方故意刁难他,说着说着他们吵起来了。敏哥一时气急,操起身边的椅子狠狠向对方脑袋砸下去,当时就把人砸休克了。事后对方告他重伤害,还报了警。结果他花了二十多万元钱才把事情摆平。辛辛苦苦做了数年生意挣的几个钱全都搭进去了。但敏哥依旧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酒照喝,架照打,日子照样过得很开心。
多年前家的一个晚辈结婚,他特地从沈阳赶到辽--南参加婚礼。和别人喝酒时又和人家拧上了,结果对方当场喝吐了,被人从桌子上抬下去的。他也没好,走路直晃,自己回不了沈阳了。还是我二姐夫连夜开车跑了二百多公里把他送回了沈阳。在那之后不久,二姐夫因患胆管癌去世,他听说后,打电话询问结果,听说人已去世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
我因为近年在多伦多——北京——辽南之间不停的奔波,一晃又有几年没和敏哥见面了,但是那种骨肉亲情却永远在心头萦绕。即便无缘见面,但心中念念不忘的牵挂则是亲情最好的证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