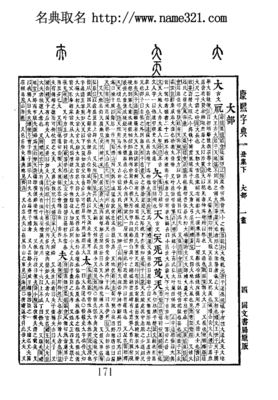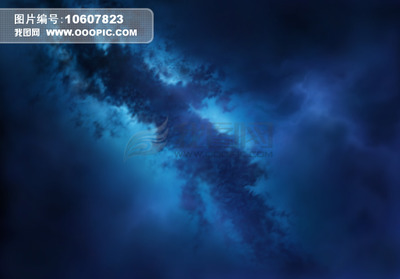传统中国画的题材,无非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走兽之类,然若有人问我最喜何种题材,我当脱口告知以“竹”;若蒙进一步垂询最喜哪几位画竹大家,我定也不假思索地罗列那一串令我敬畏的名字:古有苏轼、文同、倪瓒、柯九思、郑板桥、石涛;近有蒲华、吴昌硕等!
之所以爱竹,是因为它的清正、气节,雅而脱俗,淡而天真,正所谓“不过数片叶,满纸都是节”,实为做人之参照物;之所以推崇以上那几位画竹大家,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各逞性灵,各有千秋,无不以学识、品格活脱艺术个性。每每赏之,便感气韵贯通,画境超拔,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绘画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家。
让我有选择地提一提其中的四位吧。
苏轼画竹,苍劲雄迈,淋漓酣畅。清李景黄《似山竹谱》谓苏画云:
“苏之下笔风雨,其气足也。”
也诚如苏轼本人所言:
“气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鹊落,少纵则逝矣”。
可见苏轼画风,以气韵见长,而“气韵生动”恰是谢赫所提“六法”中的首要之法。苏轼一生,磊落坦荡,胸无城府,无论时济还是运蹇,皆不改耿介随性之本色,故频遭小人陷害,后被贬于黄州,依然写出赤壁巨制,开一代豪放词风。就画竹而言,他又堪称“鼻祖”,因画竹传说始于唐,但有作品传之后世的则以苏轼为始。
其画竹实乃人格之活画、性情之流露: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从中不难窥见:“竹”被苏轼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并提升到人生和思想境界的高度。
倪瓒是“元季四大家”之一。他一生不入仕,过着丰裕而悠然的名士生活:
照夜风灯人独宿,打窗江雨鹤相依。
他赏字画,调音律,游山水,作丹青。他的画竹,直抒胸中逸气,萧爽清丽,不求形似而契神合,虽意笔草草,兴之所至,却心手相通,自出机杼。其古淡疏朗、格调荒寒、以简胜繁的画风,可以说自古以来鲜有出其右者,如其所言: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直哉”?
——(倪瓒《清閟阁全集·卷九》)
故倪瓒画竹,便是他超逸洒脱、学识修养、品性气质的生动写照。
清代画坛巨擘,“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一生清贫,虽曾入仕,然廉政爱民,体恤底层疾苦。他 的画竹瘦劲挺拔,高风亮节,毫无媚骨,无不赋予性格和生命,是其高尚人格、悲悯情怀的艺术再现。
一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传递的是他高贵的灵魂: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也体现出自古以来有良知的文胆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特质。他的题竹画诗写道: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从中透露的更是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崇尚道德勇气和价值坚守的精神传承和庄严独白!
而清末海派大家蒲华,虽才华横溢,诗、书、画俱佳,但公认以画竹成就最高。此翁困苦潦倒一生,青年丧妻,后未再娶,无儿无女,死时竟无一人相伴。蒲华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曾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因其性情所致,未能实现愿望。转而“彩笔铓颓草莽中”,绘画便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遭际如此,却能笑对人生、淡泊名利、为人风趣,甚而天真。他的《墓志铭》上说他“性简易,无所不可”;又说他“年臻耄耋心婴儿”。他的画竹,章法奇特,无拘无束,笔墨苍润,不假修饰,如野鹤翔空,益形恣肆。吴昌硕谓之:
“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其襟怀洒落逾恒人也如斯”。
蒲华死后,其艺术成就长期被埋没,直至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重新挖掘,发扬光大。
笔者也算是一名墨竹画爱好者。
记得幼年时,以数年积攒的压岁钱去朵云轩购得一套《芥子园画谱》,其“四君子”梅兰竹菊一册尤为我钟爱,以后的丹青绘事便是受之启蒙。二十岁出头那年冒然以一幅题为《枝繁叶茂》的墨竹图投寄上海《新民晚报》,承蒙素昧平生的美术编辑、山水画家康济先生的抬爱,仅隔数日即见报,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以后虽也有画作见诸报刊、入选画展,但随着时光流逝,人到中年,虽笔耕墨舞不辍,却愈感写竹之难!难就难在写其形易,写其气、其格、其骨殊属不易。同是画竹大家的宋代文同说过:“画竹还须八法通”,而这“八法”所蕴含的学识、功底、品格、修养既寓画内,又超乎画外。清代张式在《画谭》中谈到:
“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而能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
是啊!不注重读书和修身,就不可能有画境的超拔。
那寥寥数笔顷刻可成的墨竹,在不同的画家笔下,由于学问、修养不同,当可立判高下。若一味只是画呀画,不注重提升全面的艺术修养,脱离内在的情怀,“心不静”——受名利的驱使和画商的摆布;“气不足”——没有坦荡磊落的心胸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便苦练一辈子,除了技艺的圆熟,充其量只是一名画匠而已!
那么,还是从前人的画竹,多多汲取一些做人学艺之道吧!
窃以为竹之精髓、竹之魂魄、竹之气节,可状人之风骨、人之精神、人之修养、人之品格;即使受着风的鞭打,依然斜而不歪,刚直不阿;即便受着雨的剥蚀,依然翠而不灰,吐露清新。我曾写过一首名为《咏竹》的诗:
疏落的影斜插的枝
一袭青衫随风轻拂
又似旧时的骚客孤自地长吟
玉立于初春的霜冷
静泊于自身的幽隐
潇潇之气简淡空灵
任那众树的喧哗
花圃的逗引只微微地欠身
不作趋附的和鸣
或深扎于山间或根植于村落
或栽培于雅舍
或置身于市井
不拘形迹超然于遭际
无论是电闪雷鸣
还是月白风清
可醉高风可抒胸襟
可比布衣寒士
可状耿介公卿
从东坡的神韵
到板桥的风骨从伟岸的诗文
到旷世的丹青
俯仰天地啸傲古今
放达生命境界
投映世道人心
——它已然化作水墨的精魂,撑开画轴的天地,奏响绿色的音律;它荡涤世俗的尘埃,展现挺拔的身姿,挥舞生命的旗帜。
可映心灵,可照灵魂,甚至是,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脊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