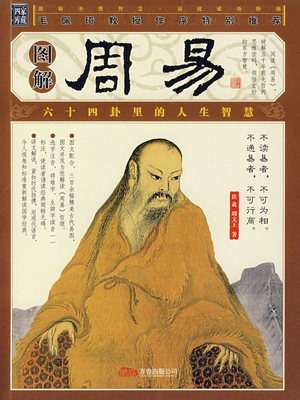1
服,信服也;膺(yīng),胸也。服膺,亦写作“伏膺”,谓服于膺,信服于胸中也。信服于胸中云者,谓牢记于心也。心在胸内,言胸即是言心。外国人胸是胸,心是心,闻“言胸即是言心”,必以“不科学”讥之。然而你的科学不是我的科学,我做啥非要按你的说? 十三亿人都能听懂,这就合乎“科学”,语言科学了。
《礼·中庸》:“子曰:‘回(指颜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指善言),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是“奉持之貌”(朱熹说),捧住不放手的样子。“拳拳服膺”,也是牢牢地记在心里,“拳拳”只是加深“服膺”的程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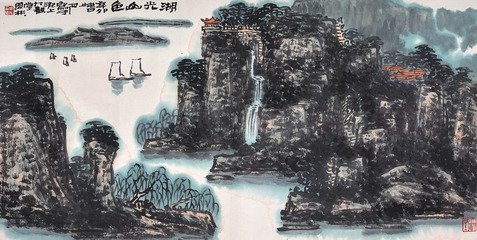
2
服膺,由“牢记在心”的本义引申出去,就有“衷心信服”,亦即“非常佩服”的意思。
《世说新语·品藻》:“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yuàn)?’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这支、孙、许三人,都是东晋的大名士。
支是支遁,字道林,本姓关。其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家世事佛,二十五岁乃释形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孙对他自称“弟子”。据说,谢安、王羲之曾与之清谈,都被迷倒,留连不忍别去。
许是许询,字玄度。此人总角秀惠,人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有才藻,善属(zhǔ)文,与孙绰并称。曾受征辟为司徒掾,故支称他为“许掾”。但实际上他没有应征,而去隐居于永兴之究山了。
孙是孙绰,字兴公。尝作《天台(tāi)赋》,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自负如此。
孙绰答支大和尚问,说在高情远致(超逸的情致)方面,是早(蚤通早)就对许询非常佩服的;但在吟诗作赋(一吟一咏)方面,许询当北面备弟子礼,拜我为师了。
孙绰是出仕的,先任著作佐郎,迁散骑常侍,寻转廷尉卿,领著作郎,一帆风顺,爬得很高。而许是请他做官也不高兴出来做的。所以孙不能不说自己在“高情远致”方面不如他。妙在说话先退后进,一转折,比起诗赋来,竟把对方说得只够给自己当徒弟的份。
这也太过分了。其实许玄度长于五言,简文帝司马昱(yù)就曾称赞他“妙绝时人”。孙兴公实在是大言不惭。用绍兴话说,孙是勿晓得剥糟(难为情)。
3
2013年7月7日文汇报《悦读》上刊登《远去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摘自《百科知识》今年第3期,作者是史晓雷先生。
文章有一句说:“我们的祖先一直缺少‘证’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时,徐光启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写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
“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这话听上去别别扭扭。
我们已在前面说过,“服膺”的意思是“牢记在心”或“非常佩服”。“被该书的体系所牢记在心”,“体系”不是人,安得有心?“被该书的体系所非常佩服”,亦极无可能;如果可能,“体系”也必须先变成了人。
应该这样说:“徐光启服膺于该书的体系。”徐光启是人,他才可以服膺,也可以不服膺。
4
我因为体弱多病,所以小时候就服膺侠客。侠客中有个六月里反穿皮袍的欧阳德(可能叫欧阳春。我记不清楚了),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欧阳德有什么好?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只是服膺而已。现在揣想,可能是因为赤日炎炎人家汗出如浆,他却还能穿皮袍的缘故。虽然是反穿的,但也不容易,其人非有大内功不可。不信,你试试?
岁数大起来,就转而服膺一些“家”了。
岁数再大起来,服膺的却反少起来,越来越少。
这倒不是我妄自尊大。只是因为我不断地发现,那些曾为我所尊崇的人,其皮袍里面却裹着“小”。
“皮袍里面裹着‘小’”,这话不是我的原创,是鲁迅先生说的。声明一下,以示不敢掠人之美也。
有个伟人,我年轻时崇拜他比小时候崇拜欧阳德还要加三分。孰知后来他会神经搭错搞什么运动,也把我打得五荤六素。我服膺于你,你却让人来打我,真正岂有此理!而且,把他的大皮袍掀开些,见里面也不全是“伟大”。“伟大”是有的,“渺小”也是有的。不值得盲目崇拜。
其人虽不值得我万分服膺,但他与“娘希匹”的蒋介石是不可同年而语的。现在有许多人在捧蒋,明捧暗捧。这些人不是立场反动,就是神经有病。
有个古人说:“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予乃不能是?”
只有说过这话的这个人,我对他的服膺程度至今不减。
5
《远去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和古代医学并不属于科学范畴”,因为“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概念作为基础来讨论”。
天文学呢?其“三垣二十宿(xiù)”体系,是“为战争胜负、王室兴衰、年成丰歉等军国大事服务的”,“已经是出了科学的范畴”。
数学呢?确立“我国古代数学的基调”的《九章算术》只是一本“服务于实际生产生活的应用问题集”,所以也“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概念作为基础来讨论”。
总之,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外国人的概念为概念呢?外国有外国的概念,我国可以有我国自己的概念呀!
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应该妄自菲薄。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定义权呢?
而且“科学”这个概念在外国,是每个历史时期都一样的么?他们在几千年前就是现在这样的概念么?
服膺洋人的“科学”,也不能服膺到这样吧?
我怕这些人再服膺下去,就会怨恨自己的鼻子不高,怨恨自己的眼睛不放蓝光了。
这不是研究科学史的科学态度。
对这样的“家”,打死我也不服膺。
2013年7月8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