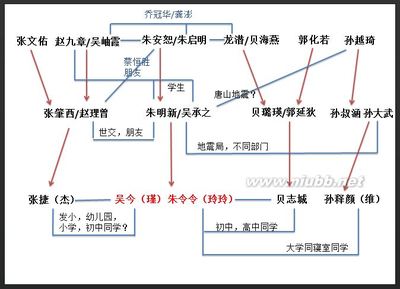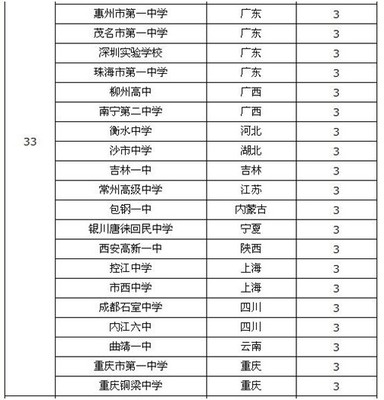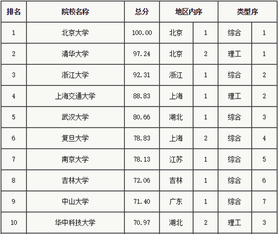昨日于网上惊悉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张青林在今年2月19日突然离世,这一噩耗虽知悉甚晚,却仍使我陷入无限悲痛之中,夜间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往事历历在目,一件件浮现眼前,仿佛昨天。
张青林小我一岁,今年67岁,按他现在的职务级别应该是65岁退休,那就是在2008年,退休还不到两年。
我们的相识是在高中三年级才开始的,那年我刚从外校调来分到他们班,由于我们两个是同宗,而且名字只一字之差,学习又都很上进,所以很快就相处融洽。他性格稳重,处事沉着,任何事不急不躁,从来不和谁发生矛盾。我的性格却和他大相径庭,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两个性格上有如此巨大反差的人走到一起,有时我自己也纳闷。
因为高三的学习非常紧张,不知不觉中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考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他考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我们两个的学校距离不算远,他们学校在西大直街的东头,我们学校在学府路,乘公共汽车到西大直街的西头,再乘有轨摩电车,很快就到他们学校,由于交通方便,彼此能经常见面。有一年的暑假我去了他家,他家离我们家乡的县城60多里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父亲是一位朴实可敬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很少在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慈祥可亲的农村老太太,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给我的感觉就像自己的母亲。她每天给我们做饭,因为我最喜欢农村饭菜,特别是小白菜裹葱和香菜沾鸡蛋酱吃二米饭。她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饭的样子非常高兴,可能当时她把我也当成他的儿子了吧。张青林他们共有三兄妹,一个哥哥在部队当兵,是位少校,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职务不算低,相当于县长的职务。他还有一个小妹妹,当时14岁左右的样子,很活泼,在学校念书。他家的门前有一个大水塘,每天我们两个就去水塘游泳,反正一天也没事,除了吃就是玩,非常开心。由于他家人的热情,在他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回家后家人都说我胖了。
读高中时的张青林
读大学时张青林在哈尔滨兆麟公园(博主摄)
我们学校的校址在郊区,去市内必须经过他们学校门前,所以我经常到他们学校去,他也到我们学校来。我们有时也到市内各处去游玩,比如南岗秋林公司,道里兆麟公园,江边防洪纪念塔等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当时还拍了很多照片,一直到现在我都珍藏着。大学后期,学校因文化大革命停课了。一天晚上我到他们学校去玩,准备晚上在那里住下来,吃完晚饭后我躺在他的床上和他们闲谈。大约7、8点钟的时候,忽然走廊里传来了多人走动的脚步声和喧哗声,我预感不妙,因为当时哈市已经有了打砸抢的事件发生,一会儿从外面回来的同学说是哈尔滨电工学院的造反派到这里来抓人了,我害怕他们对我发生误会,就在张青林和他们同学的帮助下从后大门跳出去逃走了,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哈尔滨火车站待了一宿。
大学毕业时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都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心情留下个联络方式就都匆匆走上了自己的分配岗位。几年后我们两人才有了联系,他分到了国家建设部,我分到了黑龙江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可谓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在那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我受尽磨难。性格决定了我多舛的一生。后来经多方努力,耗尽精力和财力(当时经济拮据,生活捉襟见肘),七年后我和妻子调回了家乡的专区医院,十年后我们又调到辽宁的一个中等市,我后来又为了在市内能有一所房子,无奈调到一个落后的区级医院,忍辱负重,如履薄冰的总算达到了目的,以后也就是庸庸碌碌度过余生罢了。
1980年我在上海进修时,张青林随他们副部长到上海宝山钢铁厂视察,我们终于在分别十多年后在他下榻的锦江饭店见了面。我们到南京路、淮海路逛街,并在一家照相馆留了合影。后来我到北京开学术会议时去建设部看望他两回,那时他已经是建设部施工管理司的司长了。后来听说他调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任党组书记,级别是副部级,以后我再也没去看他,我们就再没有什么联系了,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因为这是在中国。
退休后,曾经于全国两会期间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是他在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他胖了,笑容可掬很有精神,我为他高兴。这两年有了电脑,退休后闲附在家,无事可做,常在网上查一些资料,也查过张青林,了解了一些他的近况,知道他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建筑界都很有影响,在国外也有学位,在中国建筑界享有教父之誉,我很为他取得的成就高兴。他算得上是我们高中同学里的佼佼者。我为失去一位高中时期的好友而痛心。信息虽晚,我还是献上一篇祭文以示悼念。吾弟一路走好。
青林祭
呜呼青林,不幸早殇。

追思旧事,有生难忘。
弟志高远,身居庙堂
殚精竭虑,众向所望。
兄性愚昧,久处蛮荒。
纵隔千里,未敢相忘。
惊悉噩耗,不胜哀伤。
捶胸顿足,痛断肝肠。
弟乘鹤去,永别梓桑。
英灵有知,愚兄拜上。
酹酒一觞,泣别同窗。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愚兄顿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