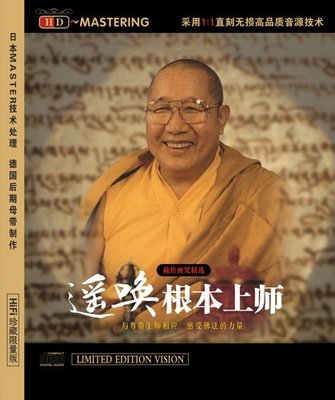重看西班牙影片《切肤欲谋》,还是令人震撼。生活中可能不会真的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但它确实描述了身份与生活的关系。人是高等动物,一个人的现在包含了所有的过去,无论那过去糟糕或辉煌,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影片涉及爱、友情、亲情、控制、身份等诸多命题,我想,每一个观看的人都可以从这部片子中解读出他所经验的生活,通过自己的解读重新理解生活,重构关于这些主题的认知。
罗伯是一位外科医生,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狠辣果断,恩仇必报。他的妻子盖儿在一场车祸中重度烧伤,罗伯在一线希望的情况下,日夜坚守在盖儿的身边,研究人造皮肤,也许是凭着爱的力量,盖儿终于捡回一条命,但身体大面积烧伤,非一时可以恢复,甚至她一辈子只能生活在阴影中,因为她已面目全非。她所在的屋子没有灯光,没有镜子,没有窗户——被窗帘遮住了。她极端虚弱的身体使得她几乎只能躺在床上,只剩下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有一天,她听到了歌声——罗伯和她的女儿诺玛在楼下院子里哼着一首母亲教给她的歌曲。这歌声忽然打通了盖儿神经通路的联系,提取过去某刻她和女儿幸福相伴的时光记忆,触动了她心灵深处的人性。她感动了,第一次有动力从床上起来,颤颤巍巍,走到歌声传来的方向,慢慢抬起手,动情的掀开一直紧闭的窗帘,想看看她美丽的女儿。可是,死亡之路也打通了,从窗户中,她看到了一具丑陋不堪的面容,不,那根本不是脸庞,而是怪物,是僵尸,是她不曾认识的恐惧的物种。但那个怪物就存在于她的身上,不可否认的代表她,于是,只剩下纵身一跃的崩溃。其实,影片中这一段描述出自罗伯身边仆人玛丽利亚的叙述,当时,影片中的悲剧主角薇拉正和玛丽利亚坐在罗伯家中花园的一条长椅上,前面燃烧着篝火,照亮了夜空。玛丽利亚回忆罗伯失去妻子的不幸,那场车祸直接导致,尽管经历了漫长的救治,罗伯心爱妻子盖儿的死亡。而那场车祸的另外一名当事人,也就是罗伯的兄弟——西卡,却逃跑了。玛丽利亚同为两人的母亲,只是罗伯是玛丽利亚作为仆人当时与主人私通生下的孩子,主人及其夫人如获至宝,因为其夫人不能生育,赶忙对外宣称这是他们亲生的孩子,罗伯得以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并获得良好教育,而罗伯也一直由玛丽利亚照顾,对于罗伯来说,玛丽利亚是其养母。西卡由玛丽利亚和另外一名仆人所生,自小就长在街头,7岁时贩毒,成了一个野孩子,没有任何教养可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车祸发生于西卡和盖儿一见钟情后,私奔的路上。
如果仅仅这样的话,故事没什么好讲的。但盖儿的纵身一跃,给女儿诺玛留下了永久的阴影,导致其长期患抑郁症。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医治,后来,病情基本痊愈,重新回归社会。罗伯带她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而在婚礼上,诺玛和一个叫文森的青年互有好感。在文森自己酒精及精神药物的作用下,在诺玛略带神经质的动作、表情被误读的情况下,在天真无邪诺玛回答文森“嗑药”问题的巧合下,悲剧发生了。文森误以为诺玛要和他做爱,在搞清楚文森的意图后,诺玛大声喊叫起来,而文森由于害怕捂住诺玛的嘴巴,在诺玛极力反抗下,将诺玛一巴掌扇晕死过去,文森以为出现人命,草草处理后仓促逃走。在大厅舞会上的罗伯很快发现情况不对,找到昏死的女儿后,女儿认定他是强奸者,精神重又错乱,进入精神病院治疗,而这一次刺激的严重后果使得诺玛的病情一直不能明显好转。
罗伯怒火中烧,将文森私自绑架囚禁在地下室。终于,当诺玛依其母亲老路跳窗自杀后,在诺玛下葬的当天,罗伯决定实行他的计划:变性文森,在文森身上进行他的皮肤试验。阴差阳错,罗伯将其彻底改造成变性人之后,竟将其面容改成盖儿的摸样,以此减轻思念爱妻之苦,甚至,希望这样盖儿就可以永远陪在他的身边。
独立看每一个事件,我们都不会想到它具有那样可怕的后果。但悲剧是一系列事件痛苦的叠加。不幸会传染,这并不是指不幸的消极作用会持续的加诸于某个当事人,而是身处不幸影响范围内的人更易形成消极的态度,或者,不幸所造成的缺失感会让一个人丧失其生命中本来应该有的东西。并且,不幸的总和绝不是每个不幸事件痛苦量的加总,如果痛苦可以用数值衡量的话,而是要远大于这加总的量。当不幸接踵而至,它就会日益加重无力感,使人陷入绝望与悲观中,并且,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外界力量的帮助,而是仅仅依靠他自己,他就愈加感到不能掌控命运,以及自己强烈的孤独,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一个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是脆弱的。在持续的不幸的刺激下,对痛苦的感觉就会麻木,而非常容易留下的,是对以前幸福或者平和日子的那种怀念,它因为现在的生活而显得更加令人留恋,甚至带了光环。这个受难的人,只凭自己的力量行事,由于缺乏更宽广的视野——这视野多半由于过于关注自己的苦难而缩小了,就更易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他忽略了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习俗和约定,转而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指导他的行动,用他自己的道德对他人进行审判,特别是当导致他苦难的有着明确的指向时。而一个人是不可能具备程序正义的,也即在行动时保持适当的克制,以及对他者基本权利的尊重。
没有程序正义的正义不是正义,它只会导致冤冤相报,永无尽头。因为,要界定每一事件的影响以及对事件后果每个人应付何种责任非常困难,现代民主社会所遵循的立法及司法程序尚不足以完全保障,将这种判定交给个人就更不必说。何况,要使每个主体为它所负责的部分承担相应的惩罚,这惩罚如何才能与责任一致,也非常困难。单看罗伯的性格,你会认定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但这么多的打击后,罗伯丧失了理性的思考力,他把文森当做全部错误的替罪羊,因为他急欲寻求所有过去错误及失去一切的补偿。文森的错误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或者这错误根本不可能发生——正常女孩不会如此单纯也不会使人误解,或者这错误本身很小——女孩不会精神错乱。即使放在本片中,文森也只不过是“嗑药”的一时冲动罢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但文森的错误的后果很严重,所以,在罗伯看来,他犯的错误便很严重,这个价值判断涉及哲学上对于好坏的争论:边沁的功利主义——以结果为导向、康德的定言命令——根据行为本身判定、柏拉图的应得观——无所谓好坏,每个人得到他该得到的(只是了解,并不熟悉)。实际上,功利主义的地位并不那么牢固,这种观点容易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被权力当局滥用。罗伯失去的都是生命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爱情、亲情。当妻子背叛并遭遇车祸死去后,女儿对他的重要性如果对比其他正常家庭来说,要高很多。所以,当妻子的死亡出现在孩子面前,并导致女儿心理阴影后,他容不得她再受伤害,所以,当文森的行径致使诺玛精神病加深,最终死亡时,罗伯已经不管不顾了,他失去了所有重要的东西,当他找到一个替罪羊时,他便紧抓不放,要给予他最残酷的待遇,要解他心头之恨,甚至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失去多少就要让你失去多少。究竟为什么一个人容易陷入不管不顾的境地呢?一个真正的强者,面对这种状况,必定得有精神上苦苦的挣扎,必定得有自我的反思,必定得重新定位自我,寻找生活中新的生存的精神支点,这支点可以和失去的有关,也可以转向新的方向。虽然这很痛苦,因为人不仅是现在,更多的是过去,但要明白的是,不可能在报复中重建自我标示,它只是意味着自我毁灭。诚然,这种毁灭不像自杀那样直接。

罗伯这么做基于两点:一,文森和这个事件有关,并且是直接点燃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导火索;二,惩罚文森是对死者的安慰。这两点都没错,可惜,罗伯做过了头,这些惩罚并不是文森应得的。在罗伯心里,盖儿和诺玛都没死,死去的是盖儿和诺玛的未来,死去的是罗伯的身份,盖儿和诺玛一直都在,所以,罗伯才可能有部分理由惩罚文森:对死者的安慰,由于对于罗伯来说他们存在,而实际上他们不存在,所以,对于如何惩罚是适度的、恰当的、令盖儿和诺玛满意的,这些都只能由罗伯来判断,而绝无互动的可能,假若他们可以托梦,必定也不会使罗伯这么残忍。另外,罗伯消耗在文森身上的精力,无论是直接的惩罚还是剥夺他的自由,无论是进行皮肤试验还是改换面容,都是在现在寻找过去的感觉,或者说寻找过去感觉的现在的、即时的真实感,即通过文森寻找诺玛和盖儿的影子,进而恢复他的身份感,虽然他令罗伯失去了一切,但他是唯一能与罗伯珍视的一切联系起来的事物。仅从结果上看,他 最终被杀也是因为入戏太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