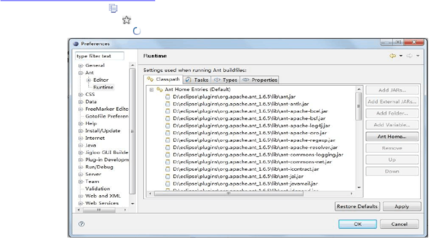本论文被收入社科院重大课题A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集体著作:《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七章第五节内容,第332-346页。承蒙导师不弃!虽然研究“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觉得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鸠山下台了,菅直人不搞东亚共同体了,准备加入TPP了。我将继续关注日本和东亚,国际关系理论的东西也不放下,毕竟读博士的话还会用到。也希望师长师兄学友们继续批评指正!王广涛谨识。
一、相关概念解析及东亚共同体的源流
共同体这一概念,从抽象意义上来理解就是一种感觉(Feel),能够在共同体中感受到了快乐、温馨和互相依靠。[1]这种共同体既具有哲学意义(例如共同体主义),也具有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意义(例如社群、社区理论)。二战以后随着一体化理论和地区主义研究的兴起,共同体的概念被赋予了国际政治学意义,它尤其体现在欧洲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地区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在国家(地区)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寻求在政治、经济(目前来看经济领域尤其引人注目)、军事安全和文化认同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实现国家(地区)内外政策的趋同,这可以被看作是更高目标,目前的欧盟正在致力于其成员国的共同内外政策。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将共同体定义为:“共同体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以适应各自面临的不同环境。一些共同体是战争和征服的产物,另一些则是共同体成员通过自愿组合而形成的。”[2]20世纪30-40年日本所着力追求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或称之为“东亚协同体”)就可以被看作是战争和征服的产物,当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并没有实现。二战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更多是在平等自愿组合的基础上构建的,现在局部区域(如欧盟)已经实现规范意义上的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在构建的过程中具体由谁来推动,这里涉及到一个主导权问题。所谓“主导权”,其实是一种“秩序”的争论,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3]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秩序”的定义持不同见解,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具体主要指涉“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内涵。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在其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中提到,“所谓世界秩序,指的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格局。”[4]地区秩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世界秩序在地区范畴上的切割和细化,是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在地区层次上的反应。[5]地区秩序是一个综合性的界定,它包括对地区内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安排。具体到东亚地区,历史上先后曾出现过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中国的朝贡体系)、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主导的“门户开放”秩序(或称之为“殖民秩序”)、日本主导的“大东亚秩序”(日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美苏主导的“冷战秩序”等。这些秩序在不同的领域着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华夷秩序”旨在追求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安排,它是一种政治上的从属性质的安排;“门户开放”秩序旨在寻求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共同殖民市场,它是一种经济上的安排;“冷战秩序”则是美苏两国全球利益在亚洲的反映,它主要是一种军事安全或战略利益上的安排。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区域合作成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的亮点,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规避金融危机带给本国的风险,东盟国家主动加强了同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与对话,由东盟主导、中日韩参加的对话合作框架渐趋完善。在东亚国家一系列的对话与合作的过程中,各方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构建“东亚共同体”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各方也基本上持积极立场,但是具体谁来参与,谁来主导推进,如何构建等一直是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东亚共同体”,是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一种参考模式。虽然目前仍然停留在提出和构想阶段,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是今后东亚合作的必由之路和最终目的。东亚地域广阔,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较大,这也客观上导致了“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困难,在构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在主导权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因为主导权问题的掣肘,导致最近几年东亚合作的进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东亚域内各国对“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国家有各自不同的见解。作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首倡者和组织者,东盟为东亚合作提供诸多的制度框架和合作愿景,以东盟方式(ASEAN Way)推进“东亚共同体”视为理所当然。中国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东盟作为主导进行推进的政策,寄希望于东盟在制度性框架的基础上发挥积极作用。日本有意主导“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并且极力阻碍中国在“东亚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作用。[6]添谷芳秀和田所昌幸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显著,但日本到目前为止在东亚一体化中承担的责任以及今后在东亚一体化构建的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日本应该为东亚的一体化以及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整体构想提出综合性战略并寻求政治上的领导地位。[7]作为亚洲地区大国的中国和日本虽然在某些场合提出愿意以东盟为中心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实际上“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更多的充斥着中日两国的博弈色彩,中日两国的学者对此多有阐述。[8]
东亚共同体再次受到各方关注的契机是日本民主党实现了政权更迭。2009年8月30日,日本政坛大变天,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席位,民主党顺利实现政权交替。2009年9月15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就任日本首相。2009年9月22日,鸠山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会见胡锦涛主席,并向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中日合作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是鸠山由纪夫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且是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首次提出的,争取同中国合作的意图明显。其后,鸠山又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其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并希望能够获得东亚国家的支持和合作。2009年10月10日,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形成共识,该主张被写进《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一时间“东亚共同体”成为热点话题。
“东亚共同体”这一构想肇始于何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一般认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马哈蒂尔于1990年12月10日在会见到访的中国总理李鹏时首次阐述了这一构想,1993年在其会见日本客人时也介绍了这一构想,并明确指出该集团所包括的成员只限于东亚各国,并期望日本能够起到主导作用。”[9]由于该构想是一个排他性的区域一体化构想,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其他国家的反对。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在处理亚洲问题时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因素的干扰,所以也消极对待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的这一构想。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出现时,日本的对亚洲投资和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日本才意识到亚洲团结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1997年12月15日,日本参加了以东盟为核心的首届东盟与中日韩(10+3)首脑会晤,该首脑会晤机制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政府正式使用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在2003年的日本东盟首脑峰会上。2003年12月11日,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在这次首脑峰会上日本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日本重返亚洲扫除了制度门槛,其后在双方共同发表的《东京宣言》中声称“日本与东盟共同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基本目标,并进一步深化东亚合作”。[10]从整体上看,小泉纯一郎时期的日本政府在对待东亚共同体的立场上带有鲜明的排斥中国的性质,这区别于民主党执政后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之所以说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同于小泉时期日本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立场,与鸠山家族和鸠山本人性格有深刻的关系。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源流和家族背景。2009年8月尚未就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在月刊《VOICE》上发表了《我的政治哲学》一文,文中提到了他的“友爱哲学”,其友爱哲学的思想源头正是来源于其祖父鸠山一郎(曾任日本首相)对欧盟思想之父卡雷尔基(Count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著作《自由与人生》的翻译,鸠山一郎在理解卡类尔基的“博爱”一词时将其翻译成“友爱”并把它当做自己的政治信条,鸠山一郎成立了一系列以友爱命名的组织,如“友爱青年联盟”、“友爱青年协会”等。鸠山由纪夫很好地继承了祖父的友爱精神,并把它作为其执政时期的政治哲学,在谈到东亚共同体构想时,他主张“各国要摒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友爱革命的方式实现东亚共同体”。[11]“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思想与小泉内阁不同,其根源在于两者的政治哲学不同。小泉执政期间仰视美国而俯视邻国,几乎无政治哲学可言,而鸠山把‘友爱’理念奉为‘辨别政治方向的指南、决定政策的判断标准’,把‘友爱’视为政治哲学和‘自立与共生时代的精神支柱’”。[12]鸠山由纪夫的这一理念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它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勾画了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美好蓝图,但是落实起来就难免陷入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怪圈。所以,鸠山版本的东亚共同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ImagedCommunity),至少在现实操作中有很多问题是违背他最初所设想的原则的。
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小泉内阁时期的东亚共同体理念还是民主党(尤其是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就其基本主张和目标而言并无本质性的差别。简言之,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核心具有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共同体。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东亚共同体的成员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成员构成,不仅仅是一个数目上的加减算数问题,而是涉及到日本的国家利益能在多大程度实现的重要问题。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并且官方和学界的观点多有不一致的地方。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曾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龙头,并且产生了“雁型发展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雁阵模式”)。1956年,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最早提出了日本产业发展的“雁型发展模式”。该模式解释了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分工和转移的格局,在这一模式中,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经济、科技等优势成为毋庸置疑的雁首,靠着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来推进地区经济增长;排在日本之后的是作为新兴工业体(NIEs)的“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从日本接受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来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再将它们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到雁尾,即“东亚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作为雁尾也加入到该模式中。毫无疑问,在这一垂直分工模式中日本作为雁首对“雁型发展模式”拥有当之无愧的主导权。在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框架中将它的辐射范围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事实上日本并没有并且也没有能力将其范围覆盖的更广(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的热潮中,日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于是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采取排挤中国的策略,通过扩大东亚共同体的地缘范围进而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不失为一项遏制中国的“良策”。日本学界也普遍将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合作的对象,只是到最近随着日本官方逐步趋向于“10+6”模式之后,才出现了一些关于支持“10+6”合作模式的主张。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地缘和历史’涉及东亚这一区域在世界地标中的定位,是东亚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13]从地缘上讲,其实定义本身已经告知了我们“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即“东亚地区”,传统所理解的东亚地区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从历史的角度看,早在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就已经通过朝贡或者频繁的人员往来成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其后该体系持续扩展,实现了地缘和历史的重合。因此,在“东亚共同体”的成员构成问题上,中国更多的主张是以地缘和历史为基准进行构建,中国所提倡的“10+3”合作模式,就是在尊重地缘、历史和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合乎逻辑的主张。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尊重地缘和历史,毕竟东亚这一称谓太过复杂。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认为:“东亚不是一个在地理上有明确界限的空间,它有各样颇有争议的认同。”[14]他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因素出发,指出价值观的不同构成了理性认识上不同版本的东亚。经济发展水平上既有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诸如韩国、新加坡之类的新型工业国、也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也不乏像缅甸、柬埔寨等最不发达国家;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既有东南亚地区为数众多的伊斯兰信徒,也存在着深受中国儒家传统影响的华人社会;社会制度上既有中国、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这样的西方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更有缅甸等国的军人政权。卡赞斯坦的这一主张直接为日本提供了构建不同于中国主张的“东亚共同体”范围的理论论据。2006年11月30日,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讲座上发表了名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日本外交地平面》的基调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形成一条自由与繁荣之弧,支持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这被广泛解读为“围堵中国”的政策。2007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说,向印度推销其“自由与繁荣之弧”计划,大谈价值观外交。无论是麻生太郎的“自由繁荣之弧”,还是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其理论依据就是其西方价值观的认同,所以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成员范围上更多的是主张“10+6”机制,即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到“东亚共同体”的范围中来,倡导“外向型的地区主义”。日本借重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认同,主观的将东亚的地理范围扩大了。
基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之所以会选择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纳入共同体的合作对象,其首要理由是基于防范中国的考量。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根据官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刺激了日本加快“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步伐,一旦中国经济大幅超越日本的话,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发言权无疑会被弱化乃至无足轻重。日本意欲联合澳新印三国以集团的形式也有壮大它“价值观共同体”经济力量的考虑。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日本更加“忌惮”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本仍然担心中国每年两位数的军费预算增长率(虽然2010年降低为7%左右),日本政要也在多种场合指责中国军事力量的不透明。笔者查阅了冷战后历年来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除2009年的《防卫白皮书》将朝鲜作为第一防范对象以外,其余各年度均将中国纳入日本的优先防范对象。[15]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和积极鼓动者,日本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自由国家”,以防范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威胁,并最终掌握“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的意图显而易见。担任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的伊藤宪一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将‘ASEAN+3’冠之以东亚的名义,其争取在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占据主导的意图明显,并且中国在东亚的潜在的存在感也在不断的明显化,抱之以警惕态度的日本只有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招致麾下,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放射状辐射的系统无疑是日本所欢迎的。”[16]日本政府(尤其是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小泉、安倍、麻生时代)用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等意识形态的说辞来为其排挤中国的政策寻找借口。
鸠山由纪夫上台以后倡导尊重多样性的价值观,以“友爱”精神为指导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指出建设东亚共同体应该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以超国家和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姿态予以推进。所以鸠山由纪夫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先向中国提出,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并且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但这也并不表示日本支持“10+3”框架下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在他的亚洲政策演说中,鸠山强调:“日本将积极参加10+6框架下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讨论与研究。”[17]在具体涉及到“东亚共同体”的成员时,鸠山则玩味日本式的暧昧之辞,指出是“拥有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人们”,其言外之意并非将成员对象绝对限定在东亚或者“10+3”的框架以内,而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寻求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国家。可见,日本在“10+6”框架内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构想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带来改变,只是弱化了其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措辞。
2、FTA/EPA战略与东亚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将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Agreement,以下简称为FTA)作为日本的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予以积极推进。FTA的基本内容是消除关税壁垒实现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因此从整体而言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但是目前来看日本的FTA战略推进得并不是很理想。无论是缔结的FTA数量上还是贸易自由化率(自由贸易占一国对外贸易的比例)上,日本都低于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有些甚至还不及中国、韩国等邻国取得的效果显著。究其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来自于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日本的农业生产成本高,政府对农户也予以较高额度的补贴政策,在对外贸易中也对输入日本的农产品采取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农产品不受侵害。1998年10月,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为契机,日韩两国开始了关于缔结FTA的研究,但是日韩两国的谈判进展的并不顺利,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日本农产品的关税问题上。
日本在同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时往往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其优先选择对象大都是一些经济规模不大、与日本贸易额很小的国家,即使是其中经济估摸最大的泰国,其与日本的贸易额也只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3%。”[18]一旦同大国尤其是农业大国讨论缔结FTA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碰到日本关税政策的硬伤——开放农产品市场。在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称呼上,日本也进行了圆滑地变通,当世界各国缔结FTA形成热潮时,日本独自创造了经济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EPA)这一称谓,“日本的EPA 是指包括FTA 要素、包括更广范围的协定,例如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扩大人员交流,取消边界和国内的有关限制,协调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方面的合作。日本之所以采用EPA 方式,是由于日本农业市场的开放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只限于FTA的谈判,往往会因日本在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而陷入僵局。为了使谈判对象国感到能更多获益,从而舒缓在农产品关税问题的对日压力,日本增加了在其他领域提供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实质上是开放强项、保护弱项的一种策略。”[19]自2002年以来,日本先后同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瑞士、越南等十个国家缔结了EPA,在这些国家中如新加坡、文莱等国基本上没有农产品出口,瑞士也是不主张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国家,这同日本的立场一致,同墨西哥的协定有助于日本借助于墨西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rea,简称为NAFTA)的名义进入美国市场。总的来看这些国家在农产品的出口上并不会给日本农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同具有农业优势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EPA,日本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条件,在农产品关税问题上也获得了这些国家的妥协。
要想构建东亚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日本政府也明确了应该遵循从贸易、能源、防灾减灾、环境、政治、军事安全的顺序逐步构建东亚共同体。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没有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显然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小泉纯一郎时期的日本政府从不把中日缔结FTA的问题纳入正式日程,只有中日两国学界和民间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2005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访问日本时就中日经贸关系提出六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启动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区进程,与东亚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中日韩合作相协调。但是中国的这一合理倡议并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回应。日本拒绝同中国缔结FTA既有在政治上排挤中国主导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考虑,也有其经济层面的原因。一旦中日缔结FTA,日本的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遭受打击,除此之外在日本的进口关税中除大部分的农产品以外其他产品大多较低,这样也会造成中国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日本,给日本的中小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小泉下台以后,安倍晋三继任首相,宣布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首相对中日FTA表示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福田首相积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麻生当政后在对待中日FTA的态度上有所改变,称两国“也可以研究日中FTA的可能性”。[20]鸠山由纪夫上台以后,积极推进他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表示希望中日两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并且表示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缔结EPA倡议,最终以EPA为途径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愿望。日本致力于东亚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没有中日两国的FTA是不会取得较大进展的。
3、“10+6”模式对GDP的提升作用——以FTA为例
毫无疑问区域一体化建设对一国的经济效益是有提升作用的,否则就不会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日本主张在“10+6”的框架内构建“东亚共同体”也有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考虑,而不单纯是出于防范中国的政治目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因其规模效应,潜在而长期的经济收益更为显著。2007年版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贸易投资白皮书》的分析报告显示,以缔结FTA对各国GDP的增加效果为例,与“10+1”和“10+3”模式相比,“10+6”模式对域内各国GDP的增长贡献率明显更高。其中“10+6”模式对域内全体国家(16国)的GDP贡献率达1.3%,略高于“10+3”模式下的1.0%(13国);对日本GDP贡献率将达到1.0%,高于“10+3”模式下的0.7%。而16国范围内的任意其他组合对GDP的增长效果均低于“10+6”整体模式下的增长率。(具体可参见下表)
表 缔结FTA对GDP的增长效果(单位:百分比)
ASEAN域内 | ASEAN 中国 | ASEAN韩国 | ASEAN日本 | ASEAN 澳大利亚 | ASEAN印度 | ASEAN +3 | ASEAN +6 | |
缔约国整体 | 0.9 | 0.7 | 0.7 | 0.5 | 0.8 | 0.9 | 1.0 | 1.3 |
ASEAN | 0.9 | 1.3 | 1.0 | 1.4 | 1.0 | 1.0 | 2.0 | 2.3 |
日本 | - | △0.01  | - | 0.3 | △0.01 | - | 0.7 | 1.0 |
中国 | △0.01 | 0.4 | △0.02 | △0.02 | △0.01 | △0.01 | 1.5 | 1.7 |
韩国 | △0.01 | △0.04 | 0.3 | △0.02 | △0.01 | - | 1.6 | 1.7 |
澳大利亚 | △0.01 | △0.03 | △0.02 | △0.1 | △0.02 | 0.9 | △0.1 | 1.2 |
印度 | - | △0.02 | △0.01 | △0.04 | 0.5 | △0.01 | △0.1 | 1.4 |
注:“-”表示增长率为0%,可忽略不计;“△”表示负值。
资料来源:2007年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贸易投资白皮书,第23页,2007年8月。
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来看,“10+6”模式构建“东亚共同体”自然具有其在经济方面的吸引力。但是日本明显忽略了东亚“10+6”模式合作的复杂性。就推进东亚合作的进程来说,“10+3”模式明显比“10+6”模式更方便、更深入,地区内国家间更容易达成共识,参照欧洲一体化的渐进式推进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作是区域一体化模式的最好参考,在欧洲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也只有六个国家在煤炭和钢铁领域的联营,就成员国数量和涉及领域而言根本看不到欧洲最终实现一体化的未来。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和扩展理论[21],合作的范围不断加深、成员国越来越多,欧洲实现了更多国家和更广领域的一体化。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在东亚合作中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立场,但是对待“10+3”框架外的国家不妨参照欧洲一体化模式,在一体化的进程中融入到集团中来,而不应该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日本在八十年代曾主张将APEC建成泛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但是APEC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它只能是一个非正式的首脑会谈,在地区合作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纵观东亚合作的历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东盟和中日韩就通过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定期会晤的形式,将“10+3”模式确定下来,而“10+6”模式则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的东亚峰会(EAS)上所采用的。关于“10+6”模式的操作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的阶段,而“10+3”模式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0年1月1日,中国和东盟已经通过“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lan)顺利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日本也宣布分别将于2011年、2012年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因此,日本方面提出的“10+6”模式从目前的实践上来看,尚不具备可行性。
4、美国因素与东亚共同体
美国一直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影子”成员国,任何有关于东亚的构想与见解都不能忽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隐形存在。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主要涉及军事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上美国并没有显示出对东亚地区足够的重视和关切。而且,美国的帝权在东亚和西欧的存在形式迥然不同,卡赞斯坦认为,“美国在与北大西洋伙伴交往的时候,倾向于在多边基础上采取行动;但在与东南亚伙伴打交道的时候则偏爱双边行动。”……“从广义的角度讲,美国愿意在欧洲建立多边制度,但在亚洲美国却急于建立双边制度。”[22]“东亚共同体”作为未来在东亚的一种多边合作机制安排,美国本无意参与,从冷战后美国的实践来看也确实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兴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提高,而美国则尚未摆脱金融危机后的颓势,它也急需要东亚这一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本国的经济复苏。更重要的是,美国深切的感到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受到了中国的威胁,除此之外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的“美亚平衡”的政策使美国感觉到日本有脱离美国控制的危险,中日联合推进“东亚共同体”的举动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融入亚洲并积极地影响东亚共同体,争取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一员对美国来说能够起到一石三鸟的效用,既可以借重亚洲高速发展的经济提振美国经济的低迷现状,又可以发挥其对日本的影响力而不让日本过快过远地背离美国,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实现其遏制和威胁中国的目的,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2009年7月22日,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东南亚。同时美国拟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设立联络机构,以确保美国同东盟国家联系的紧密性。
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日本主张美国增强其在亚洲的存在,但是在经济领域两国多有龃龉,日本在对待美国与东亚合作的立场上也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并没有政策的一贯性。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太平洋经济连带构想中,就曾经主张美国应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成员国,在其后的APEC峰会等场合对美国参与东亚合作基本也持欢迎态度。小泉纯一郎时期的日本政府曾表示希望美国能够以观察员国家参加东亚峰会。[23]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以后,为了表现出与自民党执政时期政策的不同,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建立“紧密且对等的日本同盟关系”以及“美亚并重”的重视亚洲的姿态。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阐述日本的外交政策时强调日本、中国、韩国、东盟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应为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而努力,刻意没有提到美国的参与,这也招致了美国的不满。“2009年10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表示,目前亚洲地区的主导机制并不明确,但任何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置在外。”[24]2009年10月25日,鸠山由纪夫在参加东亚峰会时指出,“即使是新政府,日美关系第一的立场也没有改变,现在没有必要决定美国是否加入(指东亚共同体,作者注),我的构想是要灵活且多方面地加以考虑”。[25]从长远来看,日本的立场是并不排除美国加入“东亚共同体”,而且从现实角度考虑,日本也无力将美国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
美国因素之于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的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中国在对待美国是否应该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则不同于日本式的善变。中国在对待东亚合作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即“东亚合作的进程应该坚持开放透明的原则,反对搞排他性的、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区域合作。其言外之意对于美国是否应该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也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立场,但是在美国的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峰会之外。”[26]事实上,中国欢迎美国积极参与到东亚乃至亚太合作的进程中,但是中国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性因素远远多于日本以及中国的周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并共同推进无异于天方夜谭。美国也不可能在涉及关税等中美贸易冲突的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这也客观上否定了美国作为“东亚共同体”初始成员国的可能性,而并非中国有意为之。当然,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表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参与,这一点是跟日本的主张有所契合的。
三、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之争及应对
2010年6月2日,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积极鼓动者鸠山由纪夫宣布辞去日本首相一职,但这并没有削弱日本在建设东亚共同体上的热情。鸠山的继任者菅直人表示他将继续尊重鸠山在东亚共同体构想中的主张,积极努力、身体力行地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当然,建设东亚共同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问题甚至结构性矛盾需要东亚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怀着战略的眼光和相互信任的勇气去共同解决。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主导权的不清晰导致各国合作缺乏信任、相互抵触。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上表示,中国绝不会在东亚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并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温家宝总理的这一发言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东亚合作所持的基本立场。中国只有继续坚持东盟国家在东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才能够获得东盟国家的信任,并在此基础上更顺利地推进东亚共同体。但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将其在东亚的影响力逐步上升,中国将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是必然的趋势。“未来东亚的国际秩序将是中国占主导地位,采取“东盟方式”的合作理念和方法,各国(集体)协调的多边体制”。[27]日本方面也多次强调在构建东亚FTA体系以及“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应该发挥东盟的主导作用。事实上日本对中国谋求东亚合作主导权的担心一刻也未曾消减过,日本提出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纳入到“东亚共同体”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弱化中国影响、日本谋求主导权的过程。“东亚共同体”是日本取得亚洲主导权的突破口。日本积极参与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对话,试图通过“经济伙伴协定(EPA)”,改变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确立日本在“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地位。[28]
日本除了积极主张“10+6”框架下的东亚共同体以外,自身也在不断的塑造其在东亚共同体构想中的影响力。并且将其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不断渗透到学界和民间,以获得国民的支持。2004年,日本成立半官方性质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议长为日本国际论坛的理事长伊藤宪一,同时该评议会还聘请日本外务省的官僚担任特聘议员,并向日本政府就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提供政策咨询。除此之外,日本学术界也积极展开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将东亚共同体研究列为重点课题,并于2008年发表了“东亚共同体宪章案”,该宪章案参照东盟宪章的模式对拟构建的东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基本原则、安全保障、共同政策等做了全方位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该宪章原则上将东盟和中日韩等13国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区别于日本的官方立场。[29]这样日本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势必获得较好的民意基础并占得话语权。面对日本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一系列举措,中国要有所反应,中国也应该成立以东亚共同体为中心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言的机构,并在适当时机提出中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和建议,并争取获得东盟国家以及日韩等国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不至于居于被动的地位。
至于东盟的中心作用,目前来看是不能忽视的,东盟作为一个渐趋成熟的国家联盟给东亚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和制度性框架,如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以及“10+1”和“10+3”合作模式等,这些是促进“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平台。虽然东盟曾一度占据过东亚合作的中心,但是近几年“随着缅甸问题再度升温、泰国陷入长时间的政治动荡,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陷入发展困境,东盟的地区作用、进取心和主导力均有所下降,”[30]东盟这匹“小马”能否拉动“大车”深受质疑。东盟的弱化效应近几年尤其明显,2008年原定于12月13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峰会因泰国内部动荡的局势而推迟,再一次显示了东盟国家领导能力的欠缺。为此,中日韩三国领导本着务实推进合作的考虑,2008年第一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召开,同时约定将该首脑会议制度化,三国轮流每年举行一次,2009年和2010年的会议分别在中国和韩国举行,中日韩三国的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架空了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缺少中日韩(尤其是中日两国)紧密而且积极的合作,仅仅依靠东盟的制度框架推进东亚共同体无异于是空中楼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东亚地位的日趋上升,日本这个“单引擎”(曾经的雁型发展模式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东亚地区已显露出马力不足之疲态。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地区性大国,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主导权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中日两个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紧要的是如何化解或消除这种主导权之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已成为冷战后中日处理两国间关系的重要经验总结,它也适应于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之争的问题上。中日共筑“东亚共同体”,首先需要摒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观念,避免或尽量减少主导权之争带来的相互损耗,形成中日“双赢”的战略心态和现实条件。[31]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如果能够放弃其在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之争,采取共同协作的态势来推进“东亚共同体”无疑更具有效果。2008年第一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中日韩三国已经就缔结TFA和A3货币联盟等进行产官研三方共同研究,“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已经从构想阶段落实到具体的案例探讨和谈判协商中。
目前来看,唯一可行的解决之道就是中日两国摒弃前嫌,本着互信、互利、多赢的原则和积极合作的态度携手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有部分学者认为:“在谈及东亚将逐渐出现共同体的时候,今后任何东亚的国家都不能像过去日本那样怀有企图成为共同体盟主的念头。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必须是,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经济发展快还是经济发展慢的国家都应当平等、对等发挥各自国家的特色长处,为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32]现任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回答记者关于日本是否要在日中韩三国中发挥主导权作用的提问时强调,不应该强调日本的主导权,而是应该站在各国平等并且抱着谦虚的立场去推进东亚合作。[33]日本拥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在高科技、环境保护、新能源等领域也领先于它的亚洲邻国,这在未来“东亚共同体”的科技、环境、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作为东亚地区发展新的引擎,中国对域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刺激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不是要强调谁主导“东亚共同体”,也不是谁主导的更多一些,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各尽其责的去推动“东亚共同体”向前发展。
[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曲第1页。
[2]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46页。
[3] 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第41页。
[4] 在布尔的论述中,他区别了“世界秩序”(WorldOrder)和“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不同定义,并且认为世界秩序是比国际秩序更高层次的一种秩序。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将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等同视之。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ed.),Peking UniversityPress, 2007,p.19.
[5] 尽管有学者并不认同将世界秩序的定义引申到地区秩序上,目前学术界仍然较多采用这一定义。参见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第41-42页。
[6] 参见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金熙德:《东亚合作的进展、问题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1-52页;[日]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1页;[日]伊藤宪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展望和我国的对应》,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编:《“东亚共同体”白皮书》,2010年夏季号。
[7] [日]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编:《日本的东亚构想》,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总论第3页。
[8] 关于东亚合作或“东亚共同体”主导权问题的相关论述参见张蕴岭:《东亚合作之路该如何走》,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8页;乔林生:《东亚合作与中日两国的政策选择》,载《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第62-66页;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编:《日本的东亚构想》,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
[9] 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载《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第34页。
[10] 参见日本外务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an_03/sengen.html
[11] 参见鸠山由纪夫个人主页:http://www.hatoyama.gr.jp/masscomm/090810.html
[12] 刘江永:《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第13页。
[13]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14] [美]彼得·卡赞斯坦:《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中国和日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14页。
[15] 2009年朝鲜曾进行过核试验和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防卫白皮书》对朝鲜的这一举动更为关切。关于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可参见防卫省网站:http://www.mod.go.jp/
[16] [日]伊藤宪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展望和我国的对应》,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编:《“东亚共同体”白皮书》,2010年夏季号。
[17] 刘昌黎:《“鸠山构想”与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页。
[18] 刘昌黎:《日本FTA/EPA的新进展、问题及其对策》,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第64页。
[19] 刘江永:《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第15页。
[20] http://www.kanntei.go.jp/singi/syokurgo/080507kettei.html.转引自刘昌黎《日本FTA/EPA的新进展、问题及其对策》,第68页。
[21] 参见[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主编:《欧洲一体化理论》(朱立群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63-93页;[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50-566页。
[22]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23] 张小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第13页。
[24] 周瑄明、[日]崛江正弘:《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进展、缺陷与中国对策》,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6页。
[25] 《东亚峰会 共同体构想获支持》,《国际财经时报》2009年10月26日,转引自刘昌黎《“鸠山构想”与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页。
[26]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 S. Policy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101. 转引自张小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第13页。
[27] 陈衍德,陈遥:《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第85-86页。
[28] 吕耀东:《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载《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7页。
[29] 参见[日]中村民雄、须纲隆夫、臼井阳一郎、佐藤义明:《东亚共同体宪章案——为可能实现的未来展开的讨论》,昭和堂,2008年。
[30] 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3-14页。
[31] 金熙德:《东亚合作的进展、问题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5页。
[32] 转引自高洪《略论鸠山联合政府及其对华政策》,载《日本研究》2009年第3期,第6页。
[33] 参见[日]中曾根康弘:《各部门领导层应怀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展望》,载《时评》2009年第1号,第34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