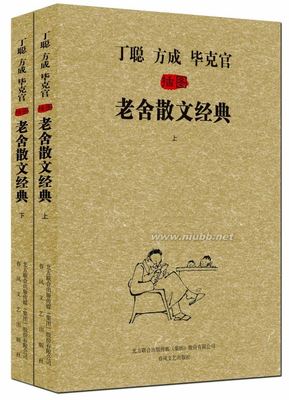老舍与赵清阁:此恨绵绵(上)
我一直试图写一本像样的《老舍传》。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学者王培元先生约写,到把书名商定为《老舍:他这一辈子》,再到现在,时间过去了近一年,写作的进度却很慢。我不断地暗示自己,这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着最合适的叙述方式,或曰让文体有些令读者耳目一新的风格。难!

但颇感欣慰的是,经培元兄介绍,我认识了韩秀——那个1946年生于纽约,父亲是荷兰裔美国人,两岁时来到中国,长于、学于北京,插队在山西、新疆,在中国有过许多年苦难历程,1976年返回美国,1980年代初开始用中文写作,到目前已出版了《折射》、《团扇》等多部小说和散文集的“奇女子”。尤其称奇的是,当她还在北京东城区的米市大街小学读书时,就为老舍与赵清阁当起了小小的信使。她管老舍叫“舒公公”,称呼赵清阁“姨”。她在给我的信里说:“1948年9月,在我刚满两岁的时候,自美国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船的两个人是我的外婆谢慧中与她的远房侄女赵清阁。……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生活中就有‘舒公公’这样一个人,他来我家,外婆客气地称呼他舒先生,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则直接叫他舒庆春。比方说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逼迫清阁姨写一部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停工资,清阁姨只能饿死。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舒先生告诉他太太我外婆病了,他必须去探病,然后进屋加了一件衣裳就拉着我的手出门了。我们在八面槽储蓄所停了一下,他关闭了一个活期存款,取出了八百元人民币。他永远没钱,我们两人在胡同口儿吃炒肝,我掏出来的蹦子ㄦ都比他多。他总是很羞愧,于是送给我许多好玩的东西,陶瓷寿星、文房四宝、字与画。经过无数浩劫,我手边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小水壶,铜的,是日本作家送给他的礼物。”
说实话,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应或者该如何在《老舍:他这一辈子》里书写老舍与赵清阁之间的感情关系,韩秀回忆里的老舍,是我丝毫所不知的。我知道多少呢?而这又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样,我也就理解陈思和老师在为我由与韩秀的通信而写成的一本特别、特殊的小书《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写的序里说:“我不想对赵、舒之恋做什么评论,只能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尊重个人隐私、只会炒作揭秘之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既缺乏同情理解、更不可能用审美态度去接受的恶俗社会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最好还是沉默相守,因为两个人的情事只有两个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好与不好,应该与不应该,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旁人无从评说,更何况我们都属于后来者,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大变化,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这些历史现象。当然,从人的感情世界的进化历程而言,可能真正的变化并不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前人的感情世界。那么,就让我们用美好的心灵去接近他们,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中,获取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吧。”
陈思和老师还清晰地记得,“近二十年前,诗人牛汉正主编《新文学史料》,一次他来上海看望我恩师贾植芳先生,我在场陪着两个老人聊天,牛汉先生曾经说起过老舍准备在新加坡买房接赵清阁出去团聚的事情,牛汉说当时老舍给赵清阁的有些信件是通过文协梅林转的,所以梅林都了解其中曲折。我当时年轻,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些不可理解,既然两人相爱,老舍也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而且连梅林都知道这个方案,可见也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他们都不是左翼作家,也没有承担什么必须留在国内的义务,老舍的朋友如林语堂等都在国外,老舍本人无顾忌,反倒是赵清阁犹豫了。”
事实上,坊间关于他俩关系的传闻,从相识、相知(颇感奇怪的是,倒是少有人用“相爱”这个字眼,因其太扎眼也未可知),到老舍夫人带着孩子由北平千里迢迢赶到重庆与丈夫团聚,再到老舍赴美,赴美期间与赵清阁书信不断,并在信里提到离婚,新中国成立后甚至还向赵清阁提议或索性不回来了,而与其“私奔”南洋(新加坡或菲律宾?),共同开始新的生活,最后却在周恩来亲自布置的多方力邀和劝说下热情无限、义无反顾地投入新政权的怀抱,或神神秘秘地凭空推想,或影影绰绰地胡乱猜测,始终没有间断过。而且,大凡提及到男女关系的“那点儿事”,一些国人总是瞬间即乐此不疲地陷入窥私的愉悦里,何况“这点儿事”发生在老舍和赵清阁的身上。许多人并不真正关心老舍与赵清阁之间一定是丰富美好的感情世界,却总在努力挖掘着他们到底有没有“肌肤之亲”。
洪深的女儿洪钤在回忆文章《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中写道:“赵清阁阿姨曾特别向我提过一件事。当时在重庆某次文化人聚会上,一位和赵阿姨他们关系一般的二流作家,喝了酒后,乘着酒劲有意大声地说:‘鹤发红颜……’多少有点‘不怀好意’地对在场的赵阿姨和某先生进行调侃。赵阿姨听到后,愤怒地立即起身离去。那次,应该是所谓‘流言效应’表现最严重的一次——公开场合,公开指向二人。”这里某先生自然指的是老舍。
也正因为此,我怕自己在书写到他们的时候哪怕稍有辞句上的不慎,便会对前人的感情世界有所亵渎。我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去接近和理解他们的感情世界,当然,这其中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要涉及到另一位女性——老舍夫人胡絜青。也许,理解比接近来得更容易些。
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无疑是美好的,却也是凄婉的悲剧。若不是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两人或许应就能在一起了。不过,也未可知。事实上,作为老舍夫人的胡絜青,那同样是一个无辜的活生生的女性生命,她是妻子,是母亲。到这时,我便感到语言的无力,可爱情常就是这般无情,相爱往往以牺牲其他的无辜者为代价。
洪钤“梧桐”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颇为意味深长。她说:“那时在重庆,被战火隔断了与家人正常联系的孤身男性大有人在,其中已经有名而后来更有名的文化人也有几个。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建立和发展新的感情关系,不算奇怪。同样,随着抗战胜利的又一种历史背景下,战争状态下的新感情也有不同结果:有理性使之,道声珍重割断了新情,保全维护了原来的家庭;也有重组新家,舍弃旧人的。印象中,对这些人感情上的这种表现,和赵清阁阿姨遭遇到的‘引人瞩目’,大不一样:对于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称得上真正‘流言’的传播。这有点令人‘不解’,原因大概也不单纯。它让我想到了《红楼梦》中那个‘心比天高’的晴雯姑娘, 想到了那个美丽、倔强女子的不幸命运。”
想想老舍去世以后的赵清阁,直到临终,都是那么的凄婉。据知情者透露,赵清阁晚年曾凄楚地表达过这样的意绪——老舍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那边是作为夫人和孩子们的母亲的胡絜青,有家庭的温暖与爱;这边,孤身一人的她,除了有老舍在三十年间写给她的信,什么也没有。这位知情者记得曾听赵清阁说过,这些信在文革时被老舍生前担任主席的北京市文联的红卫兵抄走了。文革结束后,当她到北京打听这些信的下落时,被告知,这些信当年就返回给了上海的红卫兵。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把这些信抄走了?还是上海的红卫兵抄走了这些信后,再转给北京的红卫兵?但从赵清阁写给韩秀的信来看,她似乎十分清楚是什么人弄走了这些信。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猜测。据史承钧和洪钤所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的那百多封信,至今依然沉入历史的黑幕里,而她珍藏在手里的部分,又在逝世前亲手毁掉了。(待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