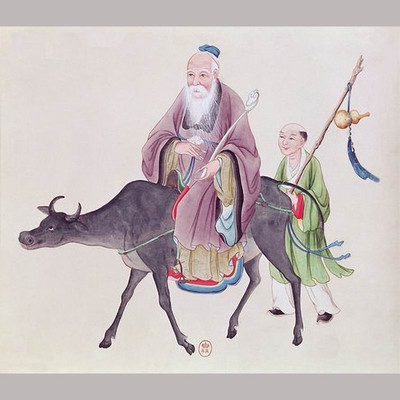前两天受重庆交通大学外语学院的邀请给他们作了两个讲座,一个谈莱辛与她的《金色笔记》,另一个漫谈文学翻译。答应过要将讲座内容挂出来,现在就履行承诺。(图为重庆交通大学新校区)
多丽丝·莱辛与《金色笔记》
《金色笔记》是一部不好读的书。作为译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读者说说我对这部书的认识;我还见过莱辛本人,也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她的一些情况向读者说说,以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和她的作品。下面就这两点与大家交流。 《金色笔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从小说的结构谈起。
《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公是安娜·沃尔夫。故事是连贯的,但作者把它分割成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两部分之间出现构成书名的金色笔记。它的位置在四本笔记之后,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网,罩在内容上。通过这张网,莱辛想表达点什么意思呢?
《自由女性》六万字左右,讲的是女主人公安娜与她的女友摩莉的感情生活。她们标榜自己是自由女性,喜欢在一起说一些关于男人的坏话。她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像女权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主线,那么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不是女权呢?
再看五个笔记本: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和她的左翼组织的同伴们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着女主人公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一些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时事新闻报道。最后是内置的金色笔记,它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
一部小说,吸引读者眼球的是生动的叙事,紧凑的、精彩的情节。但五本笔记所记录的东西都是生活中的琐事,故事并不精彩、情节也谈不上生动有趣;每本笔记记录了安娜生活的某一部分,相互间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这样安排情节,布局谋篇,岂不是有意破坏叙事的完整性,与读者过不去,也与自己过不去么?
五本笔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自由女性》则用了第三人称。黄色笔记的主人公变成了爱拉,她是安娜的影子。这样一部小说,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吗?叙事的连贯性完全没有了,小说的规范彻底被颠覆了。乍看之下,它就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标新立异的莱辛为什么要这样做小说呢?
然而,这种古怪的布局却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这种“混乱不堪”的表象是作者刻意制造的。这样头绪纷繁的叙事是为表现宏大的主题服务的。
三个主题
《金色笔记》有三个主题:一是反映意识形态上四分五裂的世界;二是描写女主人公四分五裂的人格;三是借小说表达作者的文学观。
第一个主题:反映意识形态上四分五裂的世界
莱辛是一个有极大的文学野心的人,她想用一部小说写出一个多元的世界的精神风貌。在一九七一年写的那篇《前言》中,作者曾坦诚地交待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鉴于此,她有意要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为英国文学弥补这一缺憾。(见《阅读提示》p.156)《金色笔记》就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写的。在写作实践中,她还比她的榜样走得更远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司汤达所关注的也只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法国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意识。多丽丝·莱辛却试图描写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政治风云与精神气象!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膊”(见《前言》)。
莱辛将小说的语境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时候的世界正是各种主义分割世界版图、各种意识形态各行其是、各领风骚的时代:以英国、美国、法国为首,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前苏联、中国为首是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最突出的矛盾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莱辛想用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对这个多元的世界进行是非的追问和道德的判断。她自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前言》)她因此用《黑色笔记》来表达她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认识;用《红色笔记》和《蓝色笔记》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用《自由女性》与《黄色笔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这种对整个世界作全方位的描写,究竟能达到多大程度的可信性与准确性,我们姑且不论,但光这个宏大的规划,这个空前绝后的伟大的文学命题,尝试如此宏大叙事的文学家的勇气,都是值得我们赞赏的,钦佩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莱辛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学习司汤达、托尔斯泰,就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论,她不仅做到了,而且超越了;司汤达、托尔斯泰等人只写了某个民族,某个国家,莱辛却用她的《金色笔记》写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诸多民族、诸多国家的社会现实!构成世界多样化的文明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都成了她拷问、质疑、探究的对象。可以说,《金色笔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第二个主题: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的人格分裂。用莱辛自己的话说,就是描写个体的“主观性”,审察一个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小宇宙”。
安娜是一个灵魂的漂泊者,她不满意资本主义,向往共产主义;但苏共二十大所揭示的事实真相使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最后她成了一个精神无所寄托的人,一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的人。作为作家,她再也不能重复以前说过的话;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甚至想到自杀。
《自由女性》中有一个情节是执着于共产主义信念的汤姆的自杀。汤姆是摩莉和前夫理查生的儿子。在安娜和摩莉的影响下信仰起共产主义,但由于看不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患上了意志麻痹症,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最后他朝自己开了一枪。经过抢救,性命保住了,但成了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汤姆的自杀折射的其实是安娜自己的死亡意志。小说中的汤姆被描写成一个能洞察安娜灵魂的人,这是因为,汤姆本来就是安娜灵魂的一部分。《自由女性》最后一节有那么一句话:“如果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的笔记了――当然,汤姆是个例外。”(自p.688)为什么汤姆应该是个例外呢?就因为汤姆本来就是安娜灵魂的折射,是她的另一个自我。
为了克服死亡的意志,安娜才想到用四本笔记本来记录自己迷乱的精神状态。她当时已经陷入极端混乱的情感之中,若要活下去,她得将这混乱如麻的情感进行一番梳理。她的人格就像一台机器,内部的零部体都烧坏了,她得将这台不能继续运行的机器折下来重新组装。那部内置的《金色笔记》,就是经拆分后重新组装的新机器,意味着安娜的新生。
理解了这两个主题,我们就不难理解莱辛在小说形式上的良苦用心:她想用四本笔记来寓指两个四分五裂:一个是世界的四分五裂,另一个是安娜人格的四分五裂。说到两个分裂的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她将小说的结构也进行条块分割,意在让形式与内容在指归上保持一致。她要让小说的形式也透露出她的写作的宗旨。我为《金色笔记》的汉译本写的那篇序言,题目就叫“形式也是内容”,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红黑黄蓝四本笔记与内置的《金色笔记》的关系
从四本笔记本记事到只用一本笔记,那是说安娜经过人格的拆分,终于认识了自己,知道自己今后应该如何活,也就是说,她已经完成了自我拯救,四分五裂的人格得到了整合,获得了统一。必须看到:这个完整的人格的回归是以放弃理想主义,与现实达成妥协为代价的。安娜已经不是以前的安娜,无情的现实已经摧毁了她心中的乌托邦,从困惑中走出的安娜有了新的历史观的人生观。这就是内置《金色笔记》所表达的意思。
读者也许会说质疑说,内置《金色笔记》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那里只有关于推石上山的描写。其实,安娜新的历史观的人生观都是寄寓在这个寓言里的。
推石说源于古希腊神话:科林斯国王Sisyphus是个狡猾、恶劣、贪财的人,死后受到惩罚:在地狱推一巨石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就滚落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永无止息。莱辛用这个神话比喻了人类追求真理,向着更高层次的文明艰难前行的步伐。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同于Sisyphus推石上山:所推的圆石会滚下来,推石者得重新再推;但也有别于西绪弗斯:因为所推的石块没有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这就是莱辛的历史观:人类前进的脚步是沉重的,艰难的,更多时候是劳而无功的;但毕竟在一寸寸地向前蠕动,尽管到达山顶遥遥无期,但毕竟在蠕动着。
同是这个西绪弗斯寓言,莱辛还借以表达了她的另一层意思:作为个体的人在缓慢而痛苦的历史进程中应该做点什么?是扮演伟人的角色悠闲地站在高山之巅向下张望,或干脆走在他们前头一万年,在他们还在低坡上做苦力时就为他们筹划向金星移民呢(这里其实是在讽刺革命导师),还是进入推石者的行列,不怀奢望地做一点成效甚微、甚至可能毫无成效的工作?理想幻灭后的安娜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是莱辛的人生观:与现实妥协,做自己能做的事。作为作家的安娜,应该继续她的文学写作。就像伏尔泰所说:还是种地要紧。
《自由女性》与四本笔记的关系
《自由女性》这一部分的文字的关键词确实就是“女权”。安娜和摩莉在厨房里唠唠叨叨,说了男人许多的坏话。有读者凭此认为《金色笔记》是一部写女权的作品。有人甚至称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是“女权主义的老祖母”。这是对《金色笔记》的误读。
其实,《自由女性》中的“女权”只是一个陪衬,一个次要的话题,它与四本笔记的关系是小主题与大主题的关系,决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
莱辛不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更不是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性与荒谬性。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
在莱辛看来,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世界,当务之急是意识形态的纷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这些主义才是影响人类生存的关键。女权主义与这些主义相比较,已经不那么重要,至少还排不上议事日程。
双性同体:莱辛的两性观
内置《金色笔记》除了表述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死观外,还表现了莱辛的两性观,即双性同体的思想。这是她为结束“性战争”,实现男女和谐相处的美好前景开出的药方。
双性同体,又称雌雄同体,英语androgyny,是由希腊文andro(男性)与gyny(女性)两词相加而成的新词。生物学上可用来指同一个体身上雌雄性器官并存;心理学上指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统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律勒治认为一个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自己的房间》的作者)把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批评中,提出人的大脑只有将两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富有创造力的。双性同体被认为是艺术创造的最佳状态,是消除性别二元对立的理想模式。
莱辛写作《金色笔记》时显然接受了双性同体的理念,只是在表述上没有直接用这个词。她巧妙地构想了一个情节,让这一象征性的情节来传达她的理念。这个寄寓了双性同体思想的情节就是安娜和索尔互为对方的小说写开头:索尔为安娜写的一句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是《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开头,由此我们知道,这部中篇小说是安娜克服了写作障碍症,学会与现实妥协以后写出的。安娜给索尔写的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索尔用这个开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故事的梗概就附在那本金色笔记本里。
这个情节给我们的启示是:女性的安娜身上有了男性的特质,男性的索尔身上有了女性的特质,他们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安娜自己的话说是:“我感觉与他很亲近,仿佛他就是我的弟弟。仿佛,作为弟弟,我们再怎么分开,相隔无论多么遥远,都算不了什么了,我们永远血肉相连,心心相印。”(金p.678)
有论者认为,索尔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安娜的另一个自我。这种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对双性同体的判断也是有力的论证,说明安娜本来就是一个同时具备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作家,按柯律勒治的说法,她具有一个“伟大的大脑”;按沃尔夫的说法,她的大脑是“完整的,有创造力的”。
这里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小说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AnnaWoolf)这个名字。多丽丝•莱辛给《金色笔记》女主人公的取名为“安娜•沃尔夫”,一方面表现了她对托尔斯泰的推崇,另一方面就是与弗吉尼亚•沃尔夫出站在一起,在文学话语中进一步阐发双性同体的思想。只可惜后一点被许多读者忽视了,偏要将一部主张两性和谐相处的作品当作一件宣传性战争的武器。
第三个主题:借小说阐述作者的文学观
在我们谈论《金色笔记》迷宫般的结构,包罗万象的思想内容的时候,不应忘记作者借小说文本还表达了丰富的文学思想(p.160)。这构成了小说的第三个主题。
多丽丝•莱辛不是职业的文论家,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但《金色笔记》中的一部分内容确实属于文学理论,其中一些观点还十分新颖、独到,值得职业的批评家认真思考、借鉴。用小说写文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家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很稀罕的事。有了作者自己的说法,理解《金色笔记》和莱辛复杂的内心世界将变得容易许多,判断她的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将少一点盲目性和主观性。需要说明的是:《金色笔记》的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固然是莱辛虚构的文学形象,但借安娜之口阐述的文论话语,则代表莱辛本人。
《金色笔记》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文学命题:
1,关于文学与真实
安娜认为:小说的真实难以反映经验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是相对的。小说中提到《自由女性》这篇故事是根据四本笔记的资料创作出来的,但安娜对《自由女性》的写作很不满意,原因在于:四种笔记所记录的材料是那么的丰富而庞杂,根据这些原始材料创作出的《自由女性》与之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由此她不得不质疑:根据生活经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能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经验本身是那么“粗厉”,“无序无形”,经作家“提炼”后产生的文学文本究竟残留多大的真实性?
她(指安娜,笔者注)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如果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的笔记了(自p.688)
在小说中的小说《第三者的影子》中,安娜探讨了文学不能反映真实的一个原因:文学描写是事后的分析。(黄p.240)
这篇故事(指《第三者的影子》,笔者注)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是以分析保罗和爱拉之间的关系如何解体写出的。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写它。一个人一旦经历了某件事,这事就定了型。某件定了型的事件,即使它持续了五年,当事人差不多快要结婚,描述时总是以最后的结局为视点。这样,所有的描写其实就不真实了,因为当初经历这件事时,当事人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黄p.240)
2,关于情感与现实的关系
安娜认为,现实不仅仅是经济和战争,不仅仅代表物理领域,现实还包括心理领域,即人的情感世界。因此,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同样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安娜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有什么价值,那就应该说,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情感是社会的一种功能和产物……(自p.46-47)
在《黄色笔记》中,作者还用了“物理质量”这个概念,认为文学应表现物理质量,而不是物理本身。她所谓的“物理质量”,可以理解为从物质产生的情感效应。比如一个人剥桔子,另一个人皱眉头;文学应描写皱眉头背后的内容。
我(安娜)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一概出之于深沉的、赤裸的、毫不掩饰的内心情感。(蓝p.369)
但情感本身又有区别。安娜把情感分成“真情实感”和“虚伪的情结”两种。前者是文学家应该竭力表现的,后者则应扬弃。反思她自己的创作,安娜觉得《蓝色笔记》中记录的就是她的真情实感,而她以前创作的那部小说《战争边缘》所流露的情结就“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黑p.70)她因此断定那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黑p.80)
3,关于小说的功能
安娜认为:小说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十九世纪以前,它的功能是哲学性,也就是说,那时的小说是向读者传播某种理念的,这理念能指导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但现在的小说,“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黑p.67)哲学性成了稀有之物,新闻性取而代之,成了小说的基质。
托马斯·曼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社区,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黑p.67)
造成哲学性缺失,新闻性泛滥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于人类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黑p.68)
莱辛写作《金色笔记》,就是要将新旧小说的特质融为一体,具体地说,是以新闻之形表现哲学之质,或者说从新闻报道中写出哲学性。
4,关于典型人物与个性化
现代文论中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个性化已经不复存在。安娜不认同这种说法,觉得个性毁灭之说是无稽之谈。
前人所写的小说有一半将个性作为主题,而我们却经常被告知:人的个性已化为乌有。然而,当我回首往事,想起紫花树下那一班人并让他们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突然恍然大悟,那一套言论全都是无稽之谈。——当我心血来潮,让记忆重塑我曾经结识过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切关于人性毁灭的言论,这种违反人性的强词夺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黑p.118)
但是,承认个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安娜接受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文论。在《黑色笔记》中,她对《苏维埃文学》所提倡的文学主张大不以为然。早期的安娜相信过别林斯基式的文学观,她为此进行了反思。
加入共产党以来,我在党内的工作主要是给某些小团体作有关文学的讲座。我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的文学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的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之一边。 而西方艺术已经逐渐变成了发自灵魂的呻吟。痛苦已经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大约在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未能把这种话继续说下去。(蓝p.370)
安娜在文学讲座中至所以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对别林斯基式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她觉得,提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将导致人物性格的类型化,集体性取代了个性化,从而使文学回到中世纪的老路上去。
他们的文学(指苏维埃文学,笔者注)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叙述调子总是出奇的欢快,甚至在处理战争和苦难的题材时也是如此。这种风格来自那个神话。但是,这种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方法也正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面镜子,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的思想倾向而深感惭愧。如果这种情感一直影响我的创作,我决定从此搁笔。(蓝p.369)
5,关于作家与批评家
关于作家,安娜是这样定位的:
作家是世界的良心。为了献身艺术,一个作家有责任背叛自己的妻子,国家和朋友。还有他的情人。(黑p.461)
这几句话记在《黑色笔记》的右侧,小标题是“钱”。这“钱”是反语,作者意在讽刺艺术的商品化。
对于批评家,安娜对他们的定位是:“知识界的娼妓。”
她(一位名叫到玛丽的批评家,笔者注)很忙,但她还是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我。我的天,一想起这事我就热泪盈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个妓女为了爱跟我度过一个晚上。对我的恭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恭维我的不是杂志的编辑,而是知识界的娼妓――批评家。(黑p.462)
莱辛对批评家的反感是一贯的。她的作品经常被误读,这使她对批评家有了很深的成见。在71年写的那篇《前言》中,就以较大的篇幅谈论了批评家:
我所见过的作家,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稀有生物时,无不显现偏执狂的迹象,摆出毕恭毕敬、感激涕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他何必期待那个非同凡响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评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评家确实偶而存在着,但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对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编织那个特殊的茧状物的人毕竟只有一位,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编织那个茧。(前p.14)
莱辛的意思是,作家是编织那个茧状物(即作品,笔者注)惟一的人,只有他或她自己最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批评家或评论家拿这样那样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作品,但他们不了解作家的良苦,他们的评判也就不得要领。
为什么批评家不能成为作家的知音呢?因为他们缺乏作家所具备的修养,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与作家相背的[28](p.14)。莱辛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只知服从权威,只向学生教授如何引用或遵循他人观点和论断的现行的教育体制: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评家和评论家,就不可能为那些痴心追求创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出富有想象力与创造精神的判断。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做得好的,只是告诉作家:他的小说或剧本如何写才能与当前的情感与思维模式,即观念的风尚保持一致。他们就像石蕊试纸。他们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他们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前p.6)
6,关于浪漫派风格
在《金色笔记》中,有两篇模仿浪漫派风格写成的文字,一篇是借托一位叫詹姆斯•雪佛的作家写的《香蕉林的血迹》的复印件,用大头针别在《黑色笔记》里,故事叙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仇恨:
我绝望地走着,在时间的织机中,那大地的回音含混不清。我走过那棵香蕉树,那些忠诚的仇恨的红蛇在我身后吟唱:去吧,伙计,进城复仇去吧!香蕉林上的月亮一片猩红,它匆匆歌唱着,尖叫着,哭泣着,呻吟着。哦,红色是我的痛苦,猩红是我的痛苦,哦,红色和猩红正使仇恨所滋养的,受月光映衬的香蕉叶一片片掉落。(黑p.470)
另一篇以《写作的浪漫派》为题,出现在《黄色笔记》中,谈异性之爱和同性之爱孰轻孰重的问题:
神奇的时光之翼拍打我们的心,雪花飞旋,漫天皆白,时光将卷着我们大家,尾随我们的罗茜们,直到生命的终点,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看到我们的巴迪向前走去,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看雪花在他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那感觉真是既悲哀又美丽。(黄p.575)
这两篇文字似乎都很美,很抒情,但矫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安娜为什么要模仿浪漫派的写作风格,要在以平实明快为基调的《金色笔记》中夹杂进这种华而不实的文字呢?答案她自己已经给出:
如果我的写作又回到拙劣的模仿中,那么该是搁笔的时候了。(黄p.575)
原来,莱辛的代言人安娜是借模仿否定浪漫派的文风。通过这种否定,对于她所肯定的,也就不言自明。
 爱华网
爱华网